古琴
“琴趣”二字的来历“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是借用古人口吻说出的,大意便是说:“只要能体会到琴本身的乐趣就行了,至于要用琴弹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也就没有必要了。”
说这句话的人是谁呢?他便是“五柳师长西席”陶渊明,原来陶渊明有一张没有弦的琴,作为自己的文房玩物。人家问他:“无弦之琴,有何用途?”陶渊明答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
陶渊明绘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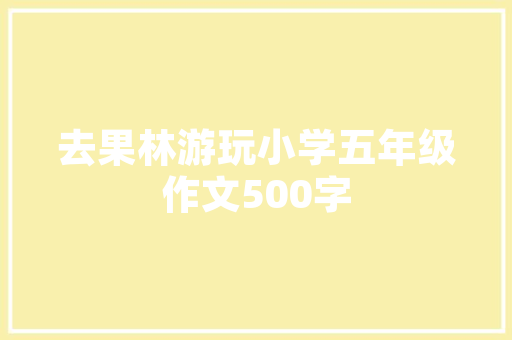
这是“琴趣”二字的来历,从陶渊明的话语中可知:琴的乐趣不在于音声,实在这只是陶渊明卓尔不群、任性率真、清高自大的性情使然。
可是后人却把“琴趣”二字用为词的别称,可以说是一种认识上的谬误。为什么这么说呢?由于把“琴趣”作为词的别称,在两个方面涌现了谬误:
一是把“琴曲”当成“琴趣”,是在“曲”字和“趣”字的字音层面上涌现的谬误,这是第一点。二是词自觉生以来,因此音乐的形式存在的,是合营谱子歌唱的,也叫歌词,以是有些词人就把词比之为“琴曲”,因而就将“琴趣”当成词的别称。这第二点,也便是是在认知层面涌现的谬误。宋代传世名画《听琴图》·局部
“琴趣外篇”的含义和来历本日所能见到的以《琴趣外篇》为名的宋代词集统共有五部,分别是五位宋代词人的作品,这五位词人和他们的词集分别是:
欧阳修的《醉翁琴趣外篇》、黄庭坚的《山谷琴趣外篇》、晁补之的《晁氏琴趣外篇》、晁端礼《闲斋琴趣外篇》、赵彦端《介庵琴趣外篇》。
古琴
此外,根据《宋史·艺文志》的记载,南宋词人叶梦得的词集也取名为《琴趣外篇》,可是叶梦得的这部《琴趣外篇》的词集在历史的长河中散迭遗失落,并没有流传下来。
所有的“琴趣外篇”,都不是词人(原创作者)自己选定的书名,而是南宋期间的出版商的“精品”,为什么这么说呢?
由于进入宋代后,造纸和印刷技能日趋成熟,以是书本印刷逐渐走向繁盛,在这种情形下涌现了以成都、开封、杭州和建阳、麻沙为中央的四大刊印中央,其刻印能力之强、刻印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唐、五代。图书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数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文本流利范围较之以前有很大的扩展。
苏轼也无不自满地说道:“余犹及见夙儒师长西席,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 …今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
宋代印刷术
宋词的传播和盛行也有印刷的一份“功劳”。由于印刷技能的推广及其在其他领域的运用逐渐冲破了宋词以演唱为主的的传播办法,通过雕板或刻石拓印的文本受到了普遍民众的欢迎。
得益于印刷技能的成熟,也随着歌词在宋代越来越风靡,刊印一些名家词人的词集既可以为书商带来丰硕的收入,也进一步遍及了词的传播和盛行,可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以是书商在汇刻诸名家词集时,为了编成一套丛书,便一本一本地将词人的词集题为某氏《琴趣外篇》,或者在“琴趣外篇”的前面加上词人的名号。
如欧阳修自号“醉翁。书商在刊印出版的时候,就将欧阳修的词集命名为《醉翁琴趣外篇》,于是词集也就成为了当时的“脱销书”,在这种传播办法下“琴趣外篇”就自然而然的成为词的别称了。
晁补之《晁氏琴趣外篇》·书影
琴曲本是古乐、雅乐,在音乐中霸占很高的地位。而词本是民间俗曲,它们是若何联系到一起的呢?
原来,宋代词人为了提高词的地位,最初称之为“雅词”,后来更尊之为琴操。这可以说是对词曲的莫大推崇。然而这个比拟却是不伦不类的,由于词的曲子与琴曲是完备不同的。
宋代书商
“琴曲”和“词曲”的差异对付这点,宋代词人实在是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异的,苏轼有一首《醉翁操》,在这篇文章自序中,苏轼是这样写的:
琅琊深谷,山水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既去十余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
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词》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约,非天成也。后三十余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于东坡居士以补之云。
董其昌书法·苏轼《醉翁操》
苏轼《醉翁操》译文的大意是说:欧阳修在滁州游琅琊深谷,飞瀑鸣泉,声若环佩。美妙动人,乐而忘归,写了一篇《醉翁亭记》,文章随处颂扬,流传千古。当时人们就刻石立了碑。
沈遵特意跑到滁州探访,见那琅琊山水确如醉翁妙笔所绘,就动了兴致,以琴寄趣,创作了一支宫声三叠的琴曲《醉翁吟》也便是《醉翁操琅然》。
后来沈遵寻了个机会为欧阳修亲自弹奏此曲,欧阳修听了很高兴。并应沈遵的要求为该曲作了词。欧阳修是填词高手,“然调不主声,为知琴者所惜。”调不主声便是唱不出来。可见欧阳修精通词律,到时对琴曲不是很精通。
沈遵的《醉翁吟》传开之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人们不但争传《醉翁吟》琴曲,连欧阳修所作《醉翁吟》歌词,也有好事者纷纭为其谱琴曲,但都不理想,就这样一晃三十多年过去,欧阳修、沈遵相继去世,庐山玉涧道人崔闲还惦记着这件事。
崔闲精通琴曲,曾拜沈遵为师。他非常喜好此曲,“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于东坡居士。”苏轼贬谪黄州期间,崔闲多次从庐山前往拜访。一次他揣着《醉翁吟》的曲谱登门,请东坡填词。苏轼不但诗文高妙,而且精通音律,听明来意,欣然应允。
于是,两人互助起来,崔闲操琴,东坡一边听着琴声一边谱词,不大一下子就完成了。
苏轼塑像
这是琴曲,属正宫。苏轼词集原不载。同时郭祥玉效作一首,序中写道:“予甥以子瞻所作《醉翁操》见寄,未以为工也。倚其声作之。”此后,辛弃疾作一首,始编入集中,即正式沿用为词调,宋代词人的《醉翁操》共有五首。《醉翁操》双凋,全词共九十一字,上片十句十平韵,下片十句八平韵。
苏轼这首词便是专门为琴曲《醉翁操》这一天生绝妙之曲而谱写的。由于时期变迁,琴曲《醉翁操》原来是有其声而无其辞,此后乐谱失落传,却变成有其辞而无其声。流传至今的苏轼的这首词作,是否真的有天籁之音,由于词谱唱法的失落传,这个我们本日已经无法听闻了,我们也只能从苏轼留下的笔墨中加以品味了。
苏轼这一段话,也解释了琴曲节奏疏宕,不与词同。“醉翁”欧阳修用楚辞体作《醉翁引》,有人为他作曲,在演奏时,曲子虽然有了节奏,而琴声已失落去其古音之自然。
由此可见,苏轼也知道词与琴曲是完备不同的。苏轼的这一首《醉翁操》,本来不收在东坡词集中,由于它是琴操而不是词。南宋时,辛弃疾模拟苏轼,也作了一首,编入了他的词集,于是后人在编东坡词集时,也把《醉翁操》编了进去。从此,琴曲《醉翁操》成了词调名。
苏轼绘像
“琴趣外篇”这个名词在宋代后的变革宋代词人赵令畤著有《侯鲭录》一书,是一本记载宋代文人轶事的小说。现存八卷。《侯鲭录》记载了这样一段词话:
东坡云,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季常云:此曲奇妙,勿妄与人。
这段话是引用了苏轼瑶池燕词的自序,便是有名句“飞花成阵春心困”的这一首词。由此也可知为琴曲而作的歌词,不协于词的音律,如果要以琴曲谱词,就非变不可。
以上二件事,都可以证明琴曲不能移于词曲。因此以“琴趣”为琴曲的代用词,这是第一个谬误;以“琴趣”为词的别名,这是第二个谬误。
不过,宋代人还没有把“琴趣”直接用作词的别名,他们用的是“琴趣外篇”。所谓“外篇”,也便是意味着,词的地位虽然提高了,但只能算是琴曲的支流,还不即是真正的琴曲,只是“外篇”而已。这样标名是可以的,在“琴趣外篇”与词的认知上,只犯了一个谬误。
元、明两代以来,许多词家都不明白“琴趣外篇”这个名词的意义,他们以为“琴趣”是词的别名,而对“外篇”的意义,则不去研究,于是非但把自己的词集标名为“琴趣”,乃至把宋代词人词集中“外篇”二字也删掉了。
《传是楼书目》著录秦不雅观词集为《淮海琴趣》,欧阳修词集为《醉翁琴趣》,汲古阁本赵彦端词集称《介庵琴趣》,《赵定宇书目》称晁补之词集为《晁氏琴趣》,都是犯了同样的认知上的谬误。
黄庭坚《山谷琴趣外篇》·宋版
小结清代以来,词家以“琴趣”为词的别名,因而用作词集名者很多,例如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张奕枢的《月在轩琴趣》,吴泰来的《昙花阁琴趣》,姚梅伯的《画边琴趣》,况周颐的《蕙风琴趣》,邵伯褧的《云淙琴趣》,都因此误传误,是失落于讲求的,更是认识上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