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诗词须要“回到现场”,古典诗词的“现场”便是作者描述的当时情境。只有回到那种情境,才能进行高质量的鉴赏,否则要么纯属凿空,要么流于肤浅。
如何回到古典诗词的“现场”?一是还原法,一是代入法。
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孟子云:“易地则皆然。”可见,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是按照韶光的箭头永一直歇,但是这无休止的变革之中蕴含着一些永恒、重复的周期性片段。比如,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仲春东风似剪刀。”如果让一个从小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鉴赏这首诗,很可能“鲜能知味也”。想办法略这首诗的好处,只有来到有柳树的地方,亲眼看看那“碧玉一树、万条丝绦”的景象。再看看那些光滑平整的柳叶,不就像剪刀剪出来的吗?于是,顿悟该诗末句以“剪刀”喻“东风”的神来之笔。
又如,杜牧的名诗《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仲春花。”读到这首诗,大脑内会迅速构建画面,一种安谧的美感油然而生,不“还原”现场彷佛无碍鉴赏。但是,之以是能构建这种画面,那是基于日常的履历。倘若让一个生活在极地的人去鉴赏,恐怕便是“夏虫不可以语冰”了。而且,就算想象成功,仍旧不如现场鉴赏所带来的深层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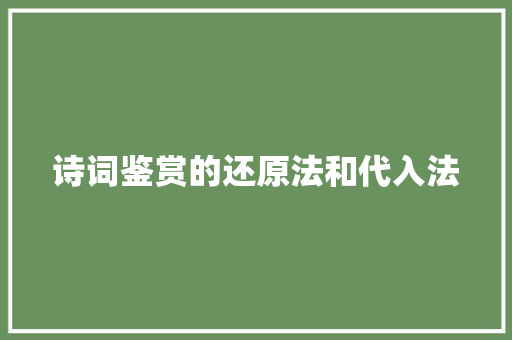
对付《山行》,古今的诗歌评论家一贯在辩论——究竟是“生处”还是“深处”?抛开啰嗦的版本学与训诂学不谈,不妨去看看秋日的枫林。我曾在江南某处领略过这种景致——在山下仰望,看着半山腰的白云旋起旋没,人家若隐若现,乃顿悟“生”字之妙。就算有别的文本支持“深”字,我也甘心相信自己的感想熏染。再欣赏那成片如火的枫林,就会由衷以为“霜叶红于仲春花”实在是“嚷出来”的诗句,绝不造作而一语中的,未加雕琢而自然合范。
古人写诗讲究炼字,对炼字的鉴赏也是诗词鉴赏的主要部分。高明的炼字不在于求新求奇,而在于求当求准。恰当地利用还原法,会增加对炼字的理解,从而让鉴赏更深一层。比如,王维的《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传颂千古的名句,并配有教科书般的解读——“直”“圆”两字是诗眼,是炼字的典范。但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个字,恐怕也有不少“人云亦云”的嫌疑。
我曾经深入戈壁滩数百公里,傍晚站在碎石丘上举目四望。戈壁滩的夏日薄暮干燥而宁静,牧民的炊烟在不远处袅袅升起,没有受到任何扰动,自然笔直而上,这不便是“大漠孤烟直”(原诗中的“孤烟”是指烽烟,但与炊烟属于同一性子)吗?再向远看,引水渠蜿蜒不断,太阳垂垂落下,由于空气纯净,落日看起来比平常更大更圆,这不便是“长河落日圆”吗?霎光阴,我以为王维这句诗被真切地“还原”了,对“直”和“圆”二字也有了更直不雅观更深刻的体悟。墨客用“直”、用“圆”,字面虽然普通,但移之他景不得,何等精准。
用还原法鉴赏诗词炼字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王安石的“东风又绿江南岸”,与其从语法角度剖析“绿”字的活用,不如到春天的“江南岸”走一走、看一看,还原一下这句诗的情境,便会以为“绿”字似虚而实、似巧而质;又如,宋祁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在书斋里是无法鉴赏“闹”字的,只有在春日外出不雅观察,还原蜂舞蝶绕的枝头景象,才能体会墨客的用字之妙。
还原法对付诗词鉴赏极具效力,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古人写诗词,讲究情景交融,“统统景语皆情语”。对付以“情语”为主的诗句,还原法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须要利用代入法鉴赏。所谓代入法,实在便是“角色置换”,鉴赏者将自己想象为作者本人,代入到当时的情境之中,体会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比如,在欣赏杜甫的“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一联时,许多人将视野局限在名物考证与句法剖析上。不可否认,此联的句法是很奇特,值得仔细剖析探究,但弄清句法倒装彷佛并无助于欣赏诗句之美。因此,不妨试一下代入法,假若“我”便是杜甫,回到千年前的大唐某个初夏时节,与朋友在园林嬉戏。忽然,“我”看到一大片绿色和赤色,便想一探究竟,于是走近这色彩,定睛细看,才创造原来绿的是笋、红的是梅。经由这样的代入,将“我”在日常游园中的感官履历置换给杜甫,便有恍然大悟之感。杜甫之以是舍弃常日的句法,将“绿”“红”二字放在句首,与其说他是故意出奇求变,不如说他是在忠实地记录自己游园的感想熏染:游园一开始瞥见的正是颜色,然后才会分辨颜色属于笋还是梅。用代入法鉴赏这句诗,比那些啰嗦的句法剖析得更直不雅观、更深入。
读者与作者心灵的默契程度越深,鉴赏也会更加深入。比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算作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孔,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林寺在史上是一方名刹,苏轼题壁于兹,其旨恐怕不大略,他该当不会像导游一样教游客如何欣赏庐山,而是另有深意。我想,在写罢一二句时,苏轼可能想到了《长阿含经》里盲人摸象的故事。庐山横算作岭、侧算作峰,在庐山面前,谁敢说自己不是盲人?之以是“不识庐山真面孔”,是由于游客将“横岭侧峰”当成庐山的真实情形,才会困惑于面孔的不同。如果沉浸在对表象的不雅观察中,就犹如身在庐山深处,永久不能看清庐山真面。
撤除还原法和代入法,诗词鉴赏还须要“厨师”的本事。《列子·说符》记载:“淄渑之合,易牙尝而知之。”易牙能够用嘴巴分辨出淄水和渑水的味道,我们在鉴赏诗词时,也要像易牙一样辨别诗词的味道。诗词之味,实在便是诗词的风格呈现、意境营造和措辞技巧。随着鉴赏的深入,该当对诗词的大致风格有所把握。比如,杜甫的七律、李白的乐府、王维的五律、李贺的歌行,都极具自家面孔,辨识度很高,在鉴赏中该当尽可能熟习它们,以便汲取更多养分。
鉴赏和创作就像诗词的两翼,分开创作的鉴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鉴赏到创作可以先从模拟做起。模拟是诗词创作的第一步,有如书法临帖。鉴赏阅读了许多名篇,该当有一种模拟的冲动,这是见贤思齐,也是由“赏”入“鉴”的一定。比如,看到韩愈的《南山》,以为此诗风格与古人迥异,体会到“以文为诗”的手腕,往后再读李商隐的《韩碑》,就会创造李商隐明显模拟借鉴了韩愈,于是技痒,就可以考试测验以这种“以文为诗”的写法创作一首长诗,在创作的过程中匆匆进对诗词的理解和感悟。
诗词鉴赏的方法难以逐一概括,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便是深入文本,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墨客的创作手腕,终极落实到体悟如何用笔墨营造意境、寄托情绪。
(作者单位系杭州出版集团)
《中国西席报》2018年04月25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