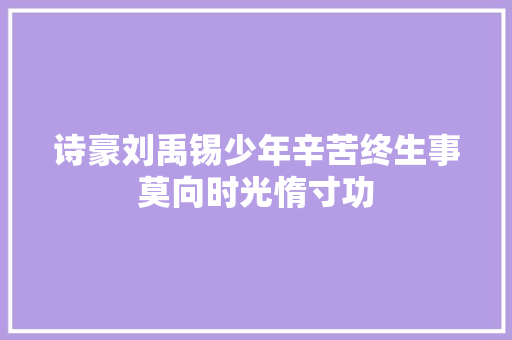体弱多病,熬炼意志
公元七七二年的某一天,刘绪和夫人卢氏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刘禹锡。夫妻二人老来得子自是十分高兴,但不幸的是刘禹锡生下来就十分瘦弱,体虚多病。
后来,刘禹锡也在《答道州薛侍郎论方书书》一文中讲述了他被病痛折磨的经历:
愚少多病,犹省为童儿时,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医巫家。针烙灌饵,咺然啼号。巫妪辄阳阳满志,引手直求,竟未知何等方何等药饵。及壮,见里中儿年齿比者,必睨然武健可爱,羞已之不如。
刘禹锡年幼多病,家人常常要抱着他四处求医问巫,考试测验各种治疗办法。大夫会用烧红的刀针,扎入他身上的疮处,将脓毒从疮口排出,而刘禹锡常常在这个过程被吓得哇哇大哭。针烙之后,还有巫婆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苦口的药汤等着他服用。终年夜一些后,刘禹锡看到那些康健强壮的同龄人,心里常常生出一种倾慕之情。
病痛的折磨没有将刘禹锡塑造成悲观懦弱的懦夫,反而熬炼了他的意志和毅力,造就了他身上独占的一份乐不雅观豁达与坚韧不屈。
少时的刘禹锡没有因疾病而困于病榻,而是更加珍惜学习的光阴,其勤奋于学的态度远非同龄人可比。
在别的孩子玩乐嬉戏的时候,刘禹锡则沉迷于舞文弄墨,他后来在《刘氏集略说》中也提到:
始馀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父老所行止,必操觚从之。
刘禹锡从小就喜好诗词,以是喜好与善于诗词的文人交游。他手里常常拿着觚(一种木质的写字板),跟在文人墨客后面请教,这些人见他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向学的恒心,都很乐意传授他知识。
惜寸阴者,乃有凌铄千古之志。对付刘禹锡这样饱受病痛折磨的人来说,能在这世上活上一天,便已经是上天的赠送。以是,他才格外地想把握住读书的光阴,把握住自己生命的代价,把握住能在这有限的韶光里实现青云之志的机会。
我想,也正是这段少年期间的独特经历,授予了刘禹锡作为一代“诗豪”的刚毅秉性与豪情壮志。
家学渊源,家教严格
刘禹锡成长于一个深受儒学熏陶的士大夫家庭,他的祖辈“世为儒而仕”,但大多是普通官员,社会地位不高,以是他的身上也自然被家人授予了入仕为官的重望。父亲刘绪坚持儒家教诲,对刘禹锡的家教十分家心和严格,权德舆还曾用“万石之训”来比喻刘绪的家庭教诲。
所谓“万石”,本名石奋,是汉代初年的一位官吏。他学问不深,但其谨慎的行事风格无人能及,后来他凭借着谨慎踏实的作风逐步升迁至上大夫,月薪两千石。他教诲四个儿子品行端正,孝敬父母,严守规矩。后来,他的儿子们也都成为两千石级官员,父子五人合起来为一万石,天子尊称他为“万石君”。权德舆以此赞誉刘绪,夸奖其教子有方。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儒家经典和诗文辞赋成为刘禹锡发展的教科书。权德舆就曾见证过少时刘禹锡苦读《诗经》、《尚书》的环境,他在《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中记录到:
始予见其丱,已习诗书,佩觿韘,恭敬详雅,异乎其伦。
在这样的悉心教导下发展起来的刘禹锡,身上呈现出一种文静端庄的气质,他待人谦善恭敬,有着深到骨子里的教养。
刘禹锡在《自传》中曾几次再三声称“家本儒素,业在艺文”,“明净祖传遗,诗书志所敦。”他深知自己的发展和造诣离不开家庭的儒学教诲和文化氛围,因此他始终器重这份家族传统,心怀“兼济”之志,看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期造诣一番奇迹。
而他的儒家精神与兼济之志也表示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如公元八二二年创作的《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九曲黄河裹挟万粒沙,经波涛的冲洗和狂风的簸荡,自天边奔跑,直上银河。
那时的刘禹锡虽然被贬,却仍怀着为济世救民的伟大空想,他相信有朝一日能施展才华,纵然经受波击浪打,也不改初心,他这种毫不服从的坚韧精神与博大肚量胸襟实在令人钦佩。
儒家的教诲理念和文化氛围为刘禹锡供应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和人文素养,也为他的诗歌作品注入了豪迈之气和人文关怀,展现了他作为一代“诗豪”的非凡气度和才华。
少遇良师,初修禅心
刘禹锡的少年期间正值中唐大历期间,这是一个诗僧浩瀚且在文学史上产生主要影响的期间。那时,号称“唐代第一诗僧”的释皎然和深得他看重的诗僧释灵澈就居住在吴兴境内。当时刘禹锡所在的嘉兴离吴兴很近,以是刘禹锡常常跑去拜访这两位著名的诗僧。
《澈上人文集纪》中就曾记载了刘禹锡拜两位诗僧为师的故事:
初,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时予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童子可教。
皎然与灵澈两位高僧墨客,见一少年郎如此好学不倦,心中甚喜,并因此更加存心地为刘禹锡传授诗道。
而对刘禹锡来说,皎然、灵澈就犹如残酷的星辰,在他的少年期间引领他步入诗歌的殿堂,成为他学诗的启蒙老师。
皎然将自己的诗歌理论凝集在了《诗式》一书中,他将禅学与诗学联系起来,认为诗学与禅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通性,两者的最高境界是超越措辞笔墨,靠民气领神会,由此方能体悟其深远意境。在皎然的影响下,刘禹锡也用“悟不因人,在心而已”的理念来沟通禅学与诗学。
灵澈虽然没有诗论传世,但是从权德舆作的《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中也能窥见灵澈的诗学理论:
心冥空无而迹寄笔墨,故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考终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
灵澈的诗学理论强调主体在静默中的不雅观照,以此达到意境的空灵与深邃,措辞讲究清新自然。
刘禹锡也在之后悟出了“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的作诗之道,形成凝练而不凝重,通达而不通俗的诗风。
他认为,诗僧之以是能够创作出清新脱俗的诗句,是由于他们摒弃了世俗的功利心态,投身于自然的怀抱,与自然和谐共生。他们用宽广的肚量胸襟容纳万物,从内心深处感想熏染到大自然的俏丽和灵气。因此,诗僧们常常能从禅林中的花草中汲取灵感,创作出如珠玉般残酷的诗歌。
在禅学的熏陶下,刘禹锡身上多了一份通达与豁然,这也表示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如《秋斋独坐寄乐天兼呈吴方之大夫》:
空斋寂寂不生尘,药物方书绕病身。
纤草数茎胜静地,幽禽忽至似佳宾。
世间忧喜虽无定,释氏销磨尽有因。
同向洛阳闲度日,莫教风景属他人。
独坐寂寂空斋之中,身侧只有药物方书为伴,在这般静默之境墨客的禅心也逐渐沉淀。心与自然相感应,一花一草、一禽一鸟全部都带上了一抹禅味。人间间的忧伤与喜悦虽然没有天命,但佛教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有因果报应和循环的规律,保持一颗沉着纯净之心,便能度过劫难。因此,墨客劝朋侪保持一颗平常心,享受在洛阳的这段清闲光阴,莫教美景都独被他人欣赏去了。
禅宗的精神在刘禹锡心中内化成一种通透豁然的处世态度,以是他才能在被贬朗州司马时写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样的千古名句;以是他才能对着奔波坎坷的二十三年贬谪生涯吟上一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能成为一代“诗豪”并非有时,而是源于少时病痛缠身熬炼出来的刚毅不屈与保持不懈,严格家教和以儒为本的家学氛围培养出来的济世胸襟与人文关怀,良师言传身教下禅理的精神渗透,以及他自身自律勤奋与好学不倦的向学态度。
少年辛劳终生事,莫向光阴惰寸功。若是成为一代“诗豪”的刘禹锡再回看自己的少年时期,想必也会感谢那个冒死努力的自己吧。
-作者-
禾雨,喜好诗词的女子,在四季中探求一个个俏丽的细节,愿光阴留下温暖的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