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来读江西师大刘世南师长西席的《在学术殿堂外》(九州出版社2018年)一书,收成很大。由于孤陋寡闻,以前只知道吴小如师长西席常常帮助别人纠谬,可见坚持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为原则、容不得错谬的人,在老辈中并不少见。个中有一篇《若何培养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人才》一文,谈到这样一件事:
一次,一位文科副教授问我“闇汤”怎么解。我要他拿原书来,一看,原来是把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一文中的“闇沕”。这位副教授竟把“沕”算作简化字“汤”。他竟不想想四库的誊录员,写的都是繁体字,怎么会把“湯”简化为“汤”呢?就这么一种水平!
克罗齐说得好:“你要理解但丁,就要达到但丁的水平。”中国古代文人都是饱读诗书的,你连看都没有看过他们熟读的书,就想去标点、注释他们的诗文,行吗?
这里的“沕”读音有两个读音,一是mi第四声,阐明为潜藏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沕深潜以自珍”;其余一个即读wu,也是第四声,阐明深微貌。同样引自《屈贾列传》:“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不管哪一个读音,加一个“闇”字,大体意思该当可以猜到。读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落笑。这种由于简体字和繁体字关系弄错的事,近年来我常常遇见,乃至深受其害。四年前,我母亲去世,做一块墓碑,母亲姓郁,我哀求他们做成繁体字,结果碑做好往后,我母亲的姓变成了“欎”,我问他们怎么一回事,他们说:“你哀求做繁体字呀?”原来他们碰着繁体字不会写的时候,就从电脑上查。我说:“姓氏的‘郁’和郁郁葱葱的‘郁’字,还有‘忧郁’的‘郁’字,在过去是两种写法。”当然,用三言两语是无法和他们讲清楚的,只好再花几千块钱重新做。既摧残浪费蹂躏钱,又延误了韶光,为此我“忧郁”了好永劫光。今年为纪念我的中学老师杨匡海师长西席去世一周年,亲友、学生为他出一本字画集,我受师母之命,去校正释文,结果松树之“松”全误成“鬆”,子曰诗云之“云”误成了“雲”。这样的舛讹所在皆是。
做这些事情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情有可原。问题是有些当代有名的书法家写的书法作品也出这样的笑话。九十年代,笔者所在学校的中文系主任张撝之师长西席送我一本《全国书法家作品选》,他见告我:“里面一些字写得不错,可惜不少人文化太差,写自己做的诗的一个也没有,只有唐宋诗一首而已,而且还常常要写错别字。”我翻开看了一下,凡写错的,先生长西席都用铅笔把那些字圈了出来,有一位全国有名的书法家写的是陆游的《沈园》两首,他把沈园写成了“瀋园”,我记得张师长西席在书的边页上写了一行字:“沈周之沈非瀋阳之瀋”;有个书法家写于谦的《咏煤炭》。题名时,把“于谦”写成“於谦”,他还以为是繁体字总是比较雅;还有把杜甫“独耻事干谒”写成“乾谒”的。我前后数一数,这样的缺点大约有十来处。前一段韶光,网络盛传某书法名家的作品有许多错字大多属于这类性子,可见这种征象实在是很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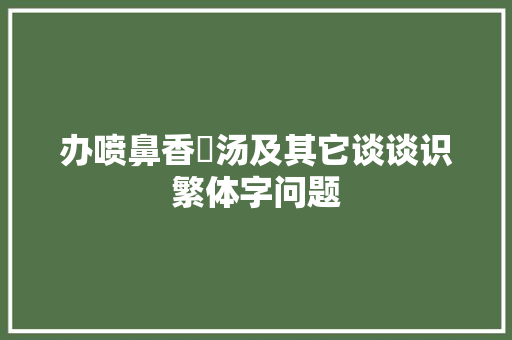
虽然写一些错别字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对书法家和语文西席来说,是不应该的,由于他们会影响不少人。白纸黑字印出来的东西影响的人更多,以是更要谨慎,以免以讹传讹。可惜现在草率下笔的人还不少。受朋友委托,恰好我手头在审阅一本普通读物。这本书讲的都是古代名人的故事,个中有一则“苏武牧羊”的,文中有一句说:“过来五六年单于的弟弟于轩王下海打猎”。什么人是“于轩王”?我读过《苏武传》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原来是“於靬王”,这个“於”字不是简化字的“于”,而是另一个字,精确的读音也不是“yu”,而是“wu”,“靬”和“轩”就更不同了。
不足为奇,在这本书里还有一篇是先容蔡文姬《悲愤诗》的,里面在说到清代诗论家张玉谷有一首评论蔡的诗,同时说到杜甫:“文姬才欲压文君,《悲愤》长篇洵大文。老杜固宗曹七步,瓣喷鼻香也可及釵裙。”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蔡文姬的才华要超过卓文君,《悲愤》诗确实是一篇精彩的诗篇;杜甫固然因此曹植为学习的榜样,也该当把敬仰的目光投向一个才女。这里的关键是一个词语“瓣喷鼻香”,引这首诗的作者把“瓣喷鼻香”误成了“办喷鼻香”——“办喷鼻香也可及釵裙”,“办喷鼻香”是什么意思?读了一辈子书,我彷佛没有见到过“办喷鼻香”这个词语。于是从网络上找张玉谷的这首诗,谁知道,网络上引的诗都作“办喷鼻香”。我知道,前面提到的那位作者可能是从网络高下载了蔡文姬的故事及其评论,于是连带着把舛讹一起下载了。问题也是出在那个繁体字上,“办”字的繁体是“辦”,和“花瓣”之“瓣”,音同形也附近,确实很随意马虎稠浊。这种稠浊在现在的刊物上是可以常常见到的。我想到吕思勉师长西席1957年写的一篇文章《论笔墨之改革》,吕师长西席对笔墨改革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对“汉字要走拼音话道路”则武断反对。在谈到简化字和繁体字时,他说:“新字之增,历来有之,然无大批呈现者,垂垂而来,众自不惮增识之劳,而旧字自亦能随之而废。一朝更迭数百字,则势必弗成矣。”为什么?由于新字出来了,旧字却不能废,“则新旧并行,而所须识之字反增矣。”以是他认为,将来的青年要读古书,就要识两套笔墨。现在看起来,不幸而言中了。
几年以前,我创造我们语文传授教化专业的研究生,国外的理论学得不少,一些语文界名人的书也读得不少,新名词讲起来一套套,传统文化的基本功却不踏实,鉴于此,我对自己的研究生提出四个哀求:一要识繁体字,不要不辨鲁鱼亥豕;二要记二百本书名和两百个人名,不要把鎏金铜当宝贝;三要背诵默写两百首古诗词,不要瞠目结舌,缺了课件连课都不会上;四要写好硬笔字,最好能写羊毫字,不要信笔涂鸦,连板书也写不好。多少年过去了,有的已经在中学小有名气,但是能够做到在四条的实在不多。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我的哀求是有道理的。
今年,我又参加我们语文传授教化专业的研究生的口试,多数是其他专业转过来的,在基本的措辞、笔墨、文学等一些中文系根本专业方面的知识与能力非常欠缺,有的达到惊人的地步。但是提及理论和传授教化方法来却又是一套套。问他们识不识繁体字,那更是天方夜谭。交上来的表格,填的字都不成样子。给他们提出一点建议,要他们去看一些什么书。他们的口头禅是“好的,我去网上查一查。”我们几个老西席对他们说:“你们要读纸本书,不要只是网上查,有些东西网上查到的未必可靠。”
确实是这样,网络这个东西有时不可靠。再以前面提到的为例,我在查蔡文姬条款时,顺便看了一些关于蔡邕的行状,谁知里面的评价和传统历史书的评价相差实在太大了,充满溢美之词,再细读,原来是根据电视剧编写的东西,许多属于“戏说”。如果一个语文西席据此先容蔡邕的话,就会出笑话。有一次一位语文老师在备课的课件里,有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里的一句话:“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他把他说成是王羲之和孔融 。我说:“此是李北海非那孔北海”,唐代书法家李邕做过北海太守,以是世称“李北海”。他见告我也是从网络上查来的。不过比来彷佛网络我在百度上查到的是精确的。去年我去一个中学听一位年轻西席上苏东坡的《赤壁赋》,她在课件中涌现了:“苏轼出身于四川眉山的穷汉之家”,“苏轼像罪犯一样被发配到黄州”我问她,你是从哪里看到这些材料的?她笑一笑,说:“我是从网络高下载下来的。”我对她说这些东西不可靠,你备课不能只靠网上查。现在年轻西席常常依赖网络查资料,这个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能够分辨知识的真伪,在用材料之前最好要核对原文、原书。
从“闇沕”谈到“瓣喷鼻香”再说得网络,无非是想强调,我们现在年轻的语文西席该当在自己专业上多用点功夫,彷佛比一些空头的理论更有用。不是说理论不要,而是要摆正位置,不要舍本逐末。【原载《语文培植》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