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它为惠州培养了大批人才,造就了其文化基因,造就了惠州岭南文化互换中央的历史地位。但是鲜少人知晓的是,康熙为丰湖书院题了墨宝,足见丰湖书院的地位,但它又何以得此机会?
近日,惠州市博物馆经研究,创造了《丰湖书院书本碑记》,不但佐证了《惠州府志》有关文献记载,而且对付见证惠州丰湖书院发展历史,有着非常主要的文物收藏及研究代价,进一步丰富了丰湖书院的历史人文内涵。
康熙天子“御书”内容。
赐墨宝勉励惠州人“争当第一元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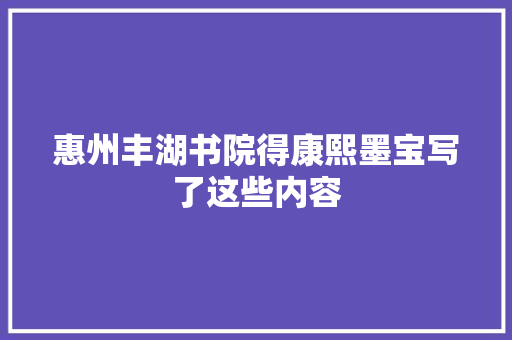
丰湖书院始建于南宋,是广东四大书院之一,近千年来多次重修。自明洪武十七年(1384)丰湖书院废弃300多年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广东提督王文雄、惠州知府李士瑜、连平州知州徐旭旦于西湖黄塘寺之左、览胜亭之右,捐俸共建丰湖书院。
书院建成后不久,提督王文雄(号毅庵,浙江人,文章人品、政事清操,历宦皆然,提粤尤著。)在书院西侧营建“御书楼”,并把康熙天子御赐诗章摹题于石,供奉楼上。
为何称“御书楼”?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小组办公室、惠州市文化局主编的《惠州史稿》(1982年版本)第五章西湖古迹考记载,御书楼在丰湖书院,清提督王文雄请康熙天子写了杜诗四句,刻在石头上,藏之以楼,故名。
丰湖书院图 惠州市博物馆供图
为何惠州还能获康熙御书?
根据康熙年间专门进呈给天子御览的《惠州西湖志》,康熙五十三年(1714),朝廷有体例《皇舆全览图》(即当今的全国舆图)的操持,为此康熙特差钦天监、理藩院、养心殿的官员苗寿、朝尔代及武英殿监造布尔赛,这些卖力不雅观察天象、颁布历法及文书官员会同泰西人麦大成、汤尚贤二位共同来惠州绘图,实地丈量西湖。
钦差大臣来惠数旬日,极为郑重。时任职广东提督的王文雄按理也会陪同到惠州。上述《惠州西湖志》卷之一丰湖书院条款亦有记载:“……公(王文雄)以是娇众议,更捐俸恭建御书楼,敬摹御赐诗章匾额以上,俾边海编氓咸得仰瞻宸翰……”
考虑到王文雄对惠州丰湖书院的感情,可合理推测他不会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借此特请康熙天子御赐墨宝,在其捐俸共建惠州丰湖书院时,有感于丰湖书院的历史及影响,便与知州徐旭启旦建御书楼以书院之后,并专门将康熙天子亲笔所题书法勒石制作成御碑,镇立御书楼二楼,用天子御书来表达培植御书楼的主要意义:除了能让平民瞻仰天子墨宝,从康熙天子所题内容所蕴含的意义来看,作为一国之君,或是希望在惠州府建成后的御书楼能跟汉代麒麟阁比较,寓意天子表彰对惠州有贡献的元勋,同时也鼓励士民要同心共同为惠州的培植多作贡献,争当第一元勋。
“御书楼”内天子的墨宝究竟写了什么内容?御书楼建好6年后,涂吴骞以中宪大夫知惠州事守惠,当他专门游览并目睹到这座建筑时,随手写下《御书楼》诗一首,该诗有序曰:……自提臣王文雄邀赐御书杜甫诗为:“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提督文雄摹于石,供奉丰湖书院之上……
桐阴论画(左)和陶渊明文集 丰湖书藏印
逢月朔十五登御书楼遥报君泽
御书楼建成后,为使临海的一样平常平民都可以在丰湖书院瞻仰帝王的墨迹,特意摹刻康熙天子的书法,供奉在御书楼上。另这本《惠州西湖志》卷之八事实还记载一则事例,时康熙五十五年,任职广东提督的王文雄在惠州丰湖书院后盖一楼,楼上供奉着天子的御书,在每月的农历月朔和十五,即百官朝参加朔望的日子,都会穿上朝服登楼,朝北叩首,以报君泽,以请圣安。
当时在文教培植中能实实在在得到天子的恩宠并御赐墨宝,无疑是这个城市的一件盛大喜事,因此书院落成之时,军民杂沓,肩摩背负,塞满湖堤,歌颂之声响遏流云。
根据成书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世经堂藏版《惠州西湖志》(卷二)的十七胜迹图之丰湖书院图中,可以清楚看到当年“御书楼”大概样式,该楼平面呈六角形,为三开间、悬山顶、中间有一正脊的二层楼阁式古典建筑,位于丰湖书院正后方,周边有文昌阁、黄塘寺等。
御书楼建成6年后,时任惠州府太守吴骞在其编著的《惠阳山水纪胜》(西湖纪胜)对御书楼位置仍有专门描述,但15年后的清雍正九年(1731),另一位惠州知府吴简民在永福寺右建惠阳书院,估计此时丰湖书院再次停用,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惠州人黄安澜绘西湖全图仍可见御书楼。
20多年后的清嘉庆五年(1800),惠州知府伊秉绶大规模重修丰湖书院时,史料记载刻石立碑者多,但唯独未见有描述或记载该御碑,估计已楼塌碑倒。因此,此时诗碑亦可能已经损毁,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梁鼎芬“夜阅课卷一百本”
提及丰湖书院,势必绕不过梁鼎芬,历史上因其掌教丰湖,创设“书藏”在广东乃至全首都尤为有名。但实际上,这位曾名震朝野的晚清重臣,对惠州及丰湖书院的感情十分深厚。
“夜阅课卷一百本。”这是梁鼎芬《节庵师长西席遗稿》卷三,至丰湖书院日记中的一句话。光绪十二年(1886),梁鼎芬赴惠州执教,到惠州第二天,他便与惠州府事夏献铭详细谈了书院有关事情,并敲定开课日期,随即在讲堂贴示书院条规,发出甄别榜,决定院内住院去留人数;开课前一天,梁鼎芬便一早到书院讲堂,备课桌,准备就绪后出书院登稌山惠州府衙答拜夏公,同时也理解一下丰湖书院之前情形。
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九日,丰湖书院重新开课,梁鼎芬在日记中记录了生员首题“吾事君以忠”,文童题“尚志”,诗题“孤月此心明”等环境,同时接见学生一百人,又欲托人寻觅好的《五经》善本读物,以供诸生阅读,课后老例在院前院后巡视一周;开课第二天,梁鼎芬陆续接见七十人后开始定日记程序,缮写朱子《白鹿洞教备》,操持托人拿去刻印,夜阅课卷一百本,至凌晨。
“夜阅课卷一百本”表示了当时梁鼎芬初至惠州丰湖书院即全力以赴,齐心专心投入教诲,为培养好惠州士子的莫大决心。
千里摹石入惠州。这是梁鼎芬在其一通书信中表达的意思,该书信题为“奉讬二事”,书信中有一段话:处州有黄山谷书范滂传石刻,务欲借不雅观,重暮上石,惠州有范祠也……梁在惠州丰湖书院期间,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十三日写下了《祭范孟博师长西席文》。
据民国《惠州西胡志》记载:“范孟博祠在丰湖书院东,记东汉党人范滂,知府夏献铭奉命筑。”范滂(字孟博)为人正派清高、有气节,后被举荐为孝廉、光禄四行而一贯受众人钦佩,同时,他也是中国读书人的榜样,为苏轼自幼所崇拜。另一则史料也表明:“光绪丙戍春,梁节庵(梁鼎芬)师长西席主讲丰湖,因集郡人士,建后汉范孟博师长西席祠于书院东。”范滂高尚刚毅的风骨气节和整肃政治,打消奸佞的品质,正是当时封建士大夫要学习的标准,也成为惠州知府夏献铭和梁鼎芬决心在丰湖书院兴建范孟博祠的紧张缘故原由。
悠悠古树,拥簇着丰湖书院 制图/杜卉
“丰湖书藏”创建初心有迹可循
2010年,惠州重修惠州丰湖书院时,出土一通石碑,残高104厘米,宽53厘米,厚约7厘米,墨石质地,字体为楷书,繁体阴刻,从右至左竖排,显得端庄厚重,但因表面磨损严重,碑上笔墨难以辨认,后陈设在丰湖书院图书馆。
近期,经仔细辨认表面残余的笔墨,创造这通石碑实为《丰湖书院书本碑记》,为清道光十三年(1833)七月题记立碑,距今约190年历史。从这通碑记题字内容可知,作者顾椿,为广西林桂县人,累官桂林知府。清道光二年(1822)进士,道光十二年(1832)应惠州知府杨希铨之邀,任惠州丰湖书院山长。据清代光绪《惠州府志》卷二十四艺文记载,该碑记全文原有500多字,目前这通出土石碑残余可辨认笔墨约50字。
透过史料记载的碑记内容可获悉,时任惠州太守杨希铨见诸生家少藏书,丰湖书院又尚无书本,志愿捐出自己的年薪和养廉金,购买了《御籑七经》《子史精华》《渊鉴类函》《康熙字典》《钦定四书文》及《四书汇参》等经史诸书合计589本,是为书院“藏书之先声”。这些书本后来都悉数藏入丰湖书院澄不雅观楼内,足足放满两个橱柜,以便给更多的学子翻阅查询。
正由于有这些藏书,50多年后,梁鼎芬踏足并主讲惠州丰湖书院,为其创设当代图书馆管理模式——“丰湖书藏”打下了根本。而丰湖书藏可谓耗尽了梁鼎芬的心血,甚至其离开惠州后,还放话说:数百年后,搜聚文献,必有到我丰湖者也。可见当时丰湖书院藏书数量非同一般。
为何要在丰湖书院立此碑记?碑记后面也做了相应补充并解释,作者在碑记中云:囊者伊墨卿师长西席典斯郡,倡建书院……今太守之志,将以追踪先哲,启兹后学。椿即为多士庆,且恐后之人忘所自来,而乐为之记云。因此,顾椿认为,伊秉绶倡建惠州丰湖书院后,聘请岭南才子宋湘来书院主讲,致使惠州文士翁然从学,大大振发了社会上的读书风气。为此,他便在其任职丰湖书院的一年间,便写下了这500多字的《丰湖书院书本碑记》并勒石以书院内,供人敬仰,以励后人,铭记先哲,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统筹策划/羊城 马勇 陈骁鹏
文/图 钟雪平 林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