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墨客蒋捷写过一首词《听雨》,词中写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墨客用短短54个字,借景生情,将少年的浮滑,中年的惆怅,老年的淡泊生动呈现出来,读后让人唏嘘不已。
借景生情手腕为什么随意马虎引起共鸣,其背后有一定的哲学思想支撑。“景”是指外部天下,“情”反响的是内心天下,要想借景生情,必须要有一个根本,即人的意识是社会塑造的。人来到这个天下,在发展过程中,社会即以“言传身教”塑造着人的意识。其结果是我们被授予了不雅观念,据此对表面天下作出判断,自身由此有了偏好并产生相应的情绪。这持续串的想法和行为,都是由社会环境带来的。比如大多数中国人都形成了这样的历史不雅观。人类的历史都须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成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等阶段。教科书即以这一不雅观念来划分中国各朝代,商、周为奴隶社会,秦至清朝为封建社会,再便是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如此划分之后,我们也同时被授予了喜恶和情绪,每当提到奴隶社会或封建各朝代,总会有讨厌之感伴随而生。这种历史不雅观来源于西方,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商、周朝按定义视作封建社会更妥;而从秦朝到清朝,实则是专制统治王朝社会。但在社会环境影响下不妨碍我们大部分人接管它,形本钱身的历史不雅观,并产生相应情绪。
从不同期间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同一事物不同的态度和情绪表达也能看到人的意识的被决定性。对中国人来说,有国家这一不雅观念是民国往后特殊是抗日战役往后的事,清朝以前老百姓是没有国家这一不雅观念的。历史上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某一姓氏的天下,古代的“国”是某一家族的国,和普通老百姓的权利没有直接关系。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满盈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以是说中国古人的国家不雅观念并非民族或政治共同体,而只是王朝或文化意义下的不雅观念。没有国家不雅观念,古代中国老百姓的爱国情绪便无从提及。对照当下中国人显示出来的强烈的爱国感情,可以说爱国情绪也不是天生就有的。
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国家的不雅观念和情绪也存在很大差异。2013年,苏格兰在英国政府的赞许下举行独立公投,虽然末了这一公投未通过,但英国人镇静处理国家分裂的做法对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人来说还是难以理解和接管的。这一事宜表明人的意识在相称程度被他所处的文化环境所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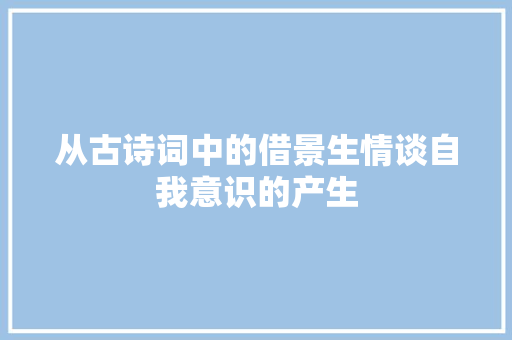
虽然人的意识被社会环境所决定,但人的意识却有它自我演化自我发展的一壁。苏轼有一首诗《不雅观潮》,诗中写到“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虽然“庐山烟雨浙江潮”在看前看后完备一样,但人的内心却起了变革,心境已全然不同。人的意识在不知不觉中起的变革,苏轼作了最好的描述。
人的意识还有其自主性的一壁,表现在人可以将意义或情绪赋于指定的外部事物上,在诗词中即“寓情于景”的手腕。从苏轼的《定风坡·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可看到这一写法的妙处。词中写道:“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使女。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作者将给自已心灵带来沉着之地视作故乡来表达自己的意识和情绪,将情寓于景上,展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
人的意识被社会塑造,但人却有将自已的情绪赋于外部天下的能力,这也是自我差异于他人,差异于社会的能力,也是人生活的意义所在。如果在当今这个社会,一个人只会“借景生情”而不会“寓情于景”,很随意马虎成为作家王朔眼中的“肉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