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中文俚语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对从小讲汉语终年夜的人来说,该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吧。可是,对日本人来说,并不如此。在日文里,跟朋友相关的俚语中,最常听见的是“類は友を呼ぶ”,跟中文“物以类聚”差不多,贬多于褒,印象很悲观,犹如“朱に交われば赤くなる”,即中文“近墨者黑”。以是,当第一次听到“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之际,我以为非常新鲜,彷佛视界一下子扩大了很多。原来,朋友不仅会把我们引上邪路,也会帮我们往外发展。这跟日本人最怕“给人家添麻烦”的心态实在很不同。
又例如,中文俚语“有得必有失落”,在日文里也没故意思相同的说法。这句话反之像英文的“You cannot have a cake and eat it too”(不能保留蛋糕的同时把它吃掉)。我之以是喜好它,由于个中的道理有物理学的根据。好比“物极必反”这句话,也叫人遐想到物理学家摆坠子的实验,合理得显然没有回嘴的余地,跟日本俚语常见的精神主义呈现明显的比拟。
自从开始学汉语,我从中文俚语学到了不少人生真理。例如“豪杰不吃面前亏,好马不吃转头草”。那是我看老舍原作的话剧《茶馆》演出时记住的。一种很合理、很康健的处世方法,在日本文化里却没有类似的说法。大概是武士道影响所致吧,日本人有甩不掉的自灭方向,犹如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吉田松阴所言:虽知如此定失落败,情不得已大和魂哉(かくすれば、かくなるものと知りながら、止むに止まれぬ大和魂)。哎!
于是,日本荣格生理学第一把交椅,已故河合隼大军长西席在《心的处方笺》一本书里,要提倡合理性处世方法时,说的是一句“既然要跑,该放下统统”。意思很清楚,便是劝你不要依依不舍地吃着“转头草”。可惜,还是没有马转头那样视觉化的效果。“很详细”而“视觉化”是中文俚语的强势。像“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句话,每次听到,在我面前就涌现一个人穿着本来白色的一套亵服,不知为何糊里糊涂地跳进黄河,出来的时候全身呈现黄色的尴尬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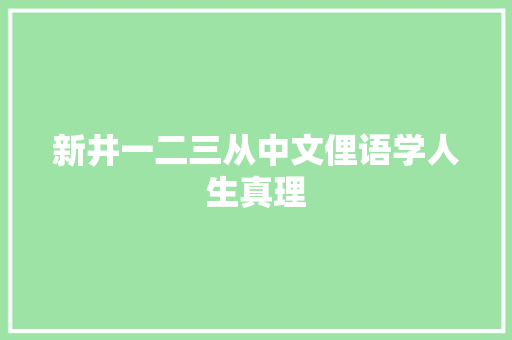
我总以为中文俚语的天下不雅观比日文俚语的乐不雅观、诙谐,例如“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非常喜好个中的乐不雅观心态。辞典说,这句话翻成日文便会是“穷则变,变则通”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出自《易经》的这句话,当代日本人一样平常都不明白。反之,生活中,更多人用的是美国式的假西班牙语句子“Que Sera Sera”。这是一九五六年的希区柯克电影《擒凶记》的主题曲,歌词重复地唱“Que sera sera,whatever will be will be”。记得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我已故的姥姥一贯将这句话挂在嘴边。我这次查询才得知西班牙语的造句有问题,但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不知道。总之,意思靠近“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便是了。
有趣的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中国刚开始做生意的一九八二年,就打了广告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好诙谐的一句文案,确信不这天本人想到的。如今上中国网络征采“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后句,未料涌现的答案竟是“有路必有丰田车”!
在中文互联网搜索“车到山前必有路”,总能引出丰田车。
说到诙谐的俚语,我就喜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相称于日文的“手前味噌”(自我吹嘘,说自己家做的味噌特殊好吃),但是画面详细得多了,切实其实那老王的表情和堆得高高的西瓜都想象得出来。
听起来不大文雅的俗话,表达出来的人生哲理,有时会给人活下去的勇气,例如“好去世不如赖活着”。这么说,活下去不再须要什么正当的情由了,多么好。
我以往事业不快意的时候,常见告自己李白说的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反之,出了点名气却立时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只好说着“人怕出名猪怕肥”来安慰自己。有这一句话比没有强不知多少。当家人亲戚带来麻烦的事情,则在嘴里喃喃自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会以为自己并不孤独。是的,只要能觉得到自己不孤独,人生就可以活下去了。
中文俚语和日文俚语的差距,有时来自环境之不同。比如说,中文讲的“瘦去世的骆驼比马大”,翻成日文便是“腐っても鯛”(腐败了还是鲷鱼)了。果真是大陆环境和岛国环境之不同产生了两个乍看很不一样的俚语。
1984年的北京,图为结冰的昆明湖。久保田博二 摄
想起来都很不可思议,一九八○年代初,我去北京留学的时候,郊区黄沙飞扬的马路上,还偶尔看得到关外农人拉着骆驼进城的画面,由于骆驼能载的货色比马多很多。近间隔看了几次骆驼往后,就自然晓得“瘦去世的骆驼比马大”指的是什么意思。同一条路(也便是如今的北京西三环路)上,当时也看得到毛驴。近间隔看了几次后,对当地点心“驴打滚”的取名要“拍大腿”了。奇怪的是,“拍大腿”翻成日文是“膝を打つ”(打膝盖)。这句话说得太奇怪了,由于打了膝盖,手肯定会疼!
《我和中文谈恋爱》;[日]新井一二三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