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丑,是史籍上都有过记载的,说他长得长身耸目、面色铁青;他的“温顺”,是写在词作里的,他的情词之美令人惊叹。他便是贺铸。
由于丑他得了个外号叫“贺鬼头”;由于情词,特殊是那首《青玉案》写得牛,他得了个外号叫“贺梅子”。两个外号,一个接地气,一个文雅得弗成,都让人记住了这个多情的词人。
提到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个人以为它是千年词坛中唯一能跟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相媲美的《青玉案》了。不过,关于这首词到底是写什么,真的是写爱情吗?在诗词大会上,导师王立群却提出了质疑。
当时诗词大会考的是一个连字题,在9个字里找出“梅子黄时雨”这一句。这题出得很大略,毕竟这是贺铸最有名的诗句,答错的选手也比较少。但这句词却引起了现场两位导师王立群和郦波的谈论。我们先来读一下这首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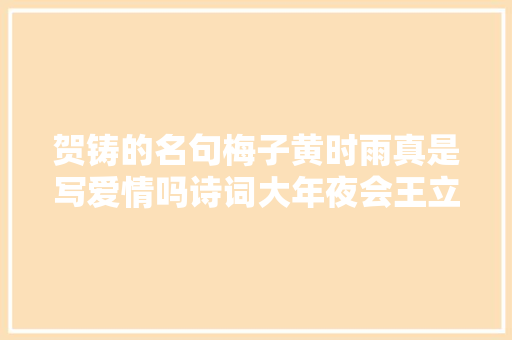
《青玉案》(贺铸)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对这首词,王立群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不雅观点:这首词可能不是爱情词,该当是喻有所指的,有可能词人在仕途不顺时写的怀才不遇之作。
他自己表示,之以是这样认为是由于从字面上来看,这首词写的是一场暗恋。词人在街上偶见了一位姑娘,回家后就魂牵梦萦。他不知道这位姑娘叫什么,住在哪里,乃至不知她是否有过婚配,但却仍旧对她朝思暮想、刻骨铭心。这在王立群老师看来,是不太可能的,按他的话来说“这也有点太过了”。
对付他这一不雅观点,一旁的郦波老师也加入了谈论。他指出:很多人由于这首词,认为贺铸跟他的妻子感情不好。但事实上,贺铸是非常爱她的妻子的,他那个千古名句“梧桐半去世清霜后,头白鸳鸯失落伴飞”,便是为妻子写的悼亡词。
郦波老师提出这个问题时,虽然没有否定这是一首爱情词,但是否也能作为佐证:贺铸如此爱妻子的人,不可能写这样的情词?
难道以前我们都理解错了,这首词真的跟爱情没有关系吗?王立群老师的不雅观点,也惹来了不少不雅观众的质疑。支持这是一首爱情词的不雅观众给出了不少情由,概括起来有3个:
首先,大家看词的内容和语句。如果是怀才不遇的作品,多少会透露一丝丝干系的字眼。屈原以喷鼻香草美人喻心中的空想,已经够隐晦了,还是被后世创造了。而贺铸这首词,是一个字眼咱们都没有创造。总不能说“梅子”、“月桥”有特殊的寓意吧!
那难免不免也太牵强了。
其次,谁说文人写爱情诗词,都是抒写自己的感情呢?李商隐并不多情,但却成了唐代的情诗圣手;晏殊一代宰相,哪来的韶光谈感情,但人家最拿手的却是婉约情词。对很多文人来说,作品里记录的经历有可能是他听来的,乃至还有可能是完备靠想象写出来的。唐代那么多墨客写边塞诗,但事实上去过边塞的没几人。
再次,这首词每一句都在写爱情。词中塑造了一个引人怜的女子形象,一个痴情的男子形象,如此光鲜而又跃然纸上。硬要说它不是爱情词,确实让人难以接管。
郦波和王立群老师是笔者非常喜好的诗词高手。但这一次,我赞许不雅观众们的见地。当代人读古典诗词作品时,都随意马虎有两个很大的误区:
其一,便是盲目地“代入感”。虽然《说文解字》中对诗的定义是言志,也便是抒写自己的感想熏染。但事实上,让我们有感触的事并非一定是自己亲自经历的事。以是希望通过诗词这种文学性很强的作品,去理解作者的平生、经历等,多少是会有一些偏差的,
其二,过度的标签化。比如杜甫的标签是“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大墨客”,以是哪怕人家明明只是给妻子写了一首情诗,很多人也爱给诗句扣上一个“忧国忧民”的标签,一定要在诗中找到一点这个痕迹才满意 。同理,陆游、辛弃疾等人,也是属于长期被过度标签化的文人。
当然,还是那句话: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贺铸这首《青玉案》到底是情词,还是怀才不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雅观点。不雅观点可以不同,但该当许可不同见地的存在。对此事,大家怎么看?欢迎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