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经典没有不引起争议的,只管争议的在少数,以是,个别学者也对毛主席的这首词提出了一些见地,而在这些人里,对这首词评价最差确当属与毛主席十分熟习的胡适。
彼时,身在台湾的胡适读着报纸上刊登的毛主席的诗词,频频摇头,当晚,他就在日记上写下了自己的评价:“没有一句通的!
”
我们知道胡适是民国的一位文学大家,抛开其政治方向不谈,他的治学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那他为什么给这首全球公认的佳作如此低的评价呢?
是眼力过高?还是故意贬低?这统统还要从两人的关系开始讲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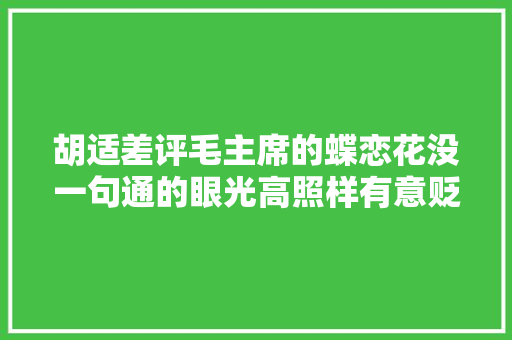
“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36年夏,毛主席在接管美国斯诺的采访时,回顾起曾经学习的经历,感慨地说出了这番话。由此可见,当年胡适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1918年8月,彼时,青年毛泽东为筹集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学费来到了北京,在北大当了图书管理员,而胡适就在北大任文科教授。
早在毛泽东在湖南师范读书的时候,他就从《新青年》上读到了胡适的文章,对里面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思想非常感兴趣,可以说,当时他把胡适当成了学习的榜样。
这次来北京,毛泽东自然想见胡适一壁,于是,便常常趁着安歇的韶光跑到北大的大教室旁听胡适的课程,对付讲台上侃侃而谈的胡适,毛泽东心里更加佩服。
几天后,他就在恩师杨昌济的先容下,专门到了胡适家中拜访,两人从文学到哲学、从政治到思想无所不谈,毛泽东感到受益匪浅。
在当时,有很多青年学生都选择了留学,到国外寻求救国的道路,但毛泽东末了却选择留在了海内探索,这个中同样离不开胡适的支持。
原来,毛泽东非常喜好胡适的文章,有一次,他读到了胡适于1914年揭橥的《非留学篇》,个中提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大学,不是非要去国外留学”,这给了毛主席很大的启示。
在京期间,他又专门就此事征询了胡适的见地,胡适同样对他留在海内的想法很是支持,以是,毛泽东终极才在临出发前下定决心不去法国了。
他说:“我以为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也要有人留在海内,求学不一定非得‘放洋’不可,把韶光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有利……我曾以此事问过胡适和黎邵西(胡适的朋友)两位,他们都以我的见地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海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不久,毛泽东回到了湖南,但只要一听说胡适有新文章揭橥,他都第一韶光负责阅读,而胡适也对毛泽东很是欣赏。
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报刊《湘江评论》,并且时常在上面揭橥一些具有革命气息的文章,不过碍于名气所限,一开始传播范围十分有限。
胡适得知后,便利用自己的名气在著名的《每周评论》上向国人隆重地先容了毛泽东创办的报刊,他说:“《湘江评论》是我们新添的小兄弟,长于议论,尤其是《民众大联合》的文章,眼力很远大,议论也很高兴,确是现今一篇主要笔墨。”
毛泽东听到胡适的讴歌,非常高兴,而有了胡适的宣扬,《湘江评论》逐渐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除了在舆论上支持毛泽东,在实际行动方面,胡适也对他供应了很多很有助益的支持。
1920年,毛泽东打算在湖南成立一个工读互助团,以便实现一种“新的生活”,只是在一些详细的细节上还有些准备不敷,为了寻求支持,他再次当面向胡适求教。
胡适对付有想法的青年人一向很是支持,于是,他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的建议,并且还主动帮他将工读互助团取名为自修大学,此外,还帮他修正了自修大学的章程,对付这件事,毛泽东也一贯记在心里。
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两人亦师亦友,交往十分密切,毛泽东从胡适那里学到了很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由于崇奉的不同,两人终极还是分道扬镳……
“可以让他当个图书馆长”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一贯坚持自由主义思想,对共产主义很是排斥,这就与崇奉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背道而驰,自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之后,两人便再也没有直接的往来,乃至走到了敌对的地步。
不过,即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毛主席也一贯没有忘却这位当年的朋友,以是,当斯诺来陕北访问时,毛主席还专门提到了他。
1946年7月,国民参政会的民主人士傅斯年来到了延安与我党洽谈关于“和平建国”的问题,傅斯年是当年胡适在北大的学生,也是胡适的好友,毛主席激情亲切地招待了他。
期间,两人聊起了胡适,毛主席朴拙地让傅斯年代自己向远在美国的胡适问好,并且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希望同胡适这一派知识分子在抗战和建国中建立互助的意向。
傅斯年回去后急速给老师胡适写了文章,胡适受到毛主席的问候,很是高兴,他激动地说道:“感念旧好,不胜驰念”,然而,由于他骨子里还是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导致两人始终没有见面的机会。
对付胡适的固执,毛主席没有多说什么,可以说,他对胡适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始终是寄予期望的。
1948年末,中国公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北平解放指日可待,此时,胡适正在城内担当北大校长,仍旧武断地反对共产主义理论。
毛主席不计前嫌,专门让我党的广播电台揭橥了声明,希望胡适能够留下来,北平和平解放后,仍连续担当北大校长,还可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一职。
只是,对付毛主席的积极争取,胡适还是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只留下了一句“他们还信赖我吗”,就乘坐飞机匆匆飞往了南京,随后,又逃到了台湾,一贯在国民党政府就职。
见到胡适这般,毛主席意识到只有绝不避讳地批驳胡适,才能使他幡然悔悟,于是,几个月后,他专门针对胡适这类人揭橥了一篇名为《放弃抱负,准备斗争》的文章,在个中直接点名批评了胡适。
不过,毛主席并非一味地批驳他,批驳的目的也是为了能让他回到公民的怀抱,毛主席说:“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抱负,因此应该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诲和联络的事情,使他们站在公民的一方来,不上帝国主义确当。”
毛主席对胡适是有着很大的原谅性的,纵然在后来批驳胡适思想的运动进行得风起云涌的时候,毛主席仍旧十分客不雅观地说道:“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该实事求是。”
还说:“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浸染,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规复名誉吧。”由此可见,毛主席一贯没有忘却当初的情意。
可胡适却齐心专心肠站在国民党的一方,始终不肯听取我党的见地,不仅如此,他乃至还对毛主席所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给予了差评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景致长宜放眼量”
韶光来到1957年春节,正在办公的毛主席收到了好友李淑一的来信,信中提到了她思念捐躯的丈夫柳直荀的经历,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词,希望毛主席能给些建议。
三言两语引起了毛主席对杨开慧的怀念,于是,他提笔写下了《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落骄杨君失落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李淑一收到毛主席的复书后,连读了多次,久久不能释怀,后来当地学校的学生们读到了这首词,他们以为像这般情真意切的诗词,应该被全国公民熟知,于是便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公开拓表。
毛主席看到来信后,随即表示了赞许,还叮嘱学生们好好学习。
1958年元旦,这首词改名为《蝶恋花·答李淑一》,被揭橥在了湖南师范的院刊上,事实证明,经典便是经典,很快,这首词就经各大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大部分文人学者也对这首词推崇备至。
然而,就在1959年3月11日,远在台湾的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这首词后,却给出了和大部分人截然不同的态度。
他在当晚的日记里这样写道:“瞥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
个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没有一句通的!
”这是极大的否定,而且乃至已经不能算得上是纯挚的文学评价了,由于看过这首词的学者们都知道词的艺术代价所在,那他为何会这么说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批驳的重心是基于词的格律而言的,他之以是给到差评,是缘于他认为这首词不合格律,而如果严格按照格律的规则来看,他的评价彷佛有一定的合理身分所在。
通读整首词,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创造词的上阙和下阙明显押得不是一个韵,而蝶恋花这一词牌却哀求同调同韵,很显然,文学功底深厚的胡适创造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在治学方面的确是有其严谨性在的,他在考证这首词韵脚的时候,考虑到了湖南方言对押韵产生的影响,为此,他专门找到了湘籍措辞学大师赵元任进行请教。
结果,赵元任也表示纵然按照湖南方言来读,毛主席所写的高下两阙也不押韵,以是,这就给了胡适批驳毛主席这首词的机会,至于他说“没有一句通的”则是由于政治不雅观念不同而进行的夸年夜式的诋毁。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偏偏只有胡适一个学者进行了如此差评呢?难道其他人就没有创造押韵上的问题?
原来,关于押韵的问题,毛主席早在写完词的时候,就不才面做了批注,精通格律的他自然不会平白无端地这样用韵,他说:“高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古人讲写诗贵在天成,不能因韵害意,毛主席显然把稳到了这一点,这首蝶恋花虽然高下两阙不合韵,但通篇读下来,丝毫没有由于韵的不同危害词的整体美感,反而更加具有韵味了。
毛主席常常提到旧体诗要发展,要改造,这首词便充分表示了他的艺术考试测验,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看,倒是胡适显得有些守旧、呆板了,这也是他的诗词境界远远不如毛主席作品的缘故原由之一。
诗品如人品,胡适琐屑较量的心态决定了他的格局,加上文人相轻和政见不同,他才会锱铢必较,忽略整体,故意贬低,专门从毛主席已经批注过的格律入手进行所谓的刁难。
相反,毛主席宽广博大的肚量胸襟让他才思泉涌,写下了一首首的传世佳作。
值得一提的是,纵然胡适给毛主席的词作了如此的差评,毛主席仍旧没有放在心上,他总是在很多场合给予了胡适客不雅观公道的评价。
1964年8月18日,在一次与哲学事情者的漫谈中,毛主席与众人提到了对红学的研究,他还负责地说道:“比较于蔡元培的不雅观点,胡适的不雅观点比较对一点。”伟人的胸襟气度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