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之一,《尚书》不仅在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层面有主要代价,其在东亚文化圈的主要浸染亦不容忽略。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互换碰撞,《尚书》流入西方天下,成为西方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管道。
《尚书》东传与东亚文化圈的建构
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的《四书》《五经》形塑着中华民族的代价体系,也塑造着一个民族的影响力。蕴含着丰富治国理政思想的《尚书》及由其阐释史建构起来的理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文化、教诲等,其早期传播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具有主要意义。《尚书》东传由百济入日本,汉籍传入朝鲜半岛约在汉代,而由半岛传入日本约在公元6世纪初。秦代南传入南越,作为其文化载体的文籍与内地相同。
韩国成均馆大学编纂的《韩国经学资料集成》是理解中国经典对朝鲜半岛文化影响的主要史料,该丛书搜集了14世纪至19世纪中期朝鲜半岛的经学文献,《尚书》文献有22册,与中国同期《尚书》学同调异趣,朝鲜半岛《尚书》学思想上宗蔡沈《书集传》,承宋明理学理路,谈论天理人欲之辨、心性论、道统等问题。方法上,承宋以来辨伪路径,重视《尚书》辨伪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内容上,多《洪范》著述、科举用《尚书》义拟题著作及《尧典》“期三百”的天算著作,这与箕子入朝的古史、科举取士及西方天算知识传入干系。近当代以来,以经典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遭受质疑否定,半岛专门研究《尚书》的学者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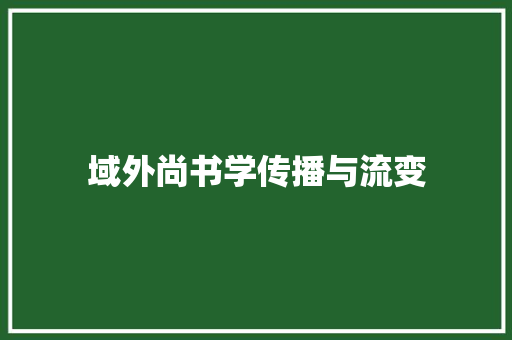
《尚书》在日本的传播,文本上最早是郑玄注本,由百济传入,今已不存。安然时期以来,日本以习伪孔安国《尚书传》为主,亦有很多唐隶古定写本,对《尚书》笔墨研究有主要代价。14世纪,清原良贤引入蔡沈《书集传》。研究方法上,日本早期接管《尚书》的办法紧张是传抄、训点、授读,至安然至室町期间逐渐形成中原氏家、藤原氏家、清原氏家等传经世家,各有秘说,主汉学训诂章句路径。十四世纪,《书集传》引入,开汉宋兼采新风。十七世纪,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渐重汉唐经学,考辨之学兴起,山井鼎《尚书古文考》校勘了《尚书》误字误句,伊藤仁斋有《古文尚书》疑辨之伪等。19世纪,西学涌入,日本《尚书》经学性子逐渐淡化,而成为了历史学、哲学、措辞学、文史考辨、文献书志等人文学科研究的史料,林泰辅《周公及其年代》开启《尚书》为史料的先河,平岗武夫《经书的成立》阐述了《尚书》作为中国文化枢纽的地位,松本雅明《春秋战国期间〈尚书〉之展开》谈论了《尚书》学变迁,加藤虎之亮《皇道所见之书经》、中江丑吉《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等借《尚书》寻绎中国古代思想。但对《尚书》经文的表明和译读仍这天本学界研究重点。在传播上,《尚书》在日本有由宫廷、寺院垄断走向民间的进程。
儒家文籍公元前3世纪传入南越,赵佗“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东汉末年,交趾太守士燮通《尚书》大义。六朝时,南下交州避难士人许慈、程秉皆通《尚书》。仿唐宋科举,李朝于1075年开科取士,其后陈朝取士大略与宋元经义取士同。黎朝于1467年设五经博士,国子监生“专治《诗》《书》者多”。阮朝时,《四书》《五经》成为了士人的基本读物。今存有黎贵惇著《书经衍义》,摘《尚书》各篇关键处略加讲授。以《尚书》为代表的《五经》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影响尚待深入研究。
东亚文化圈王朝时期,《尚书》是国家教诲的核心内容,人才选拔的依托,主流意识的主要构成,其学术流变与作为东亚核心的中国基本同等。在阐释路径上,由汉学、宋学到考据之学,经典的阐释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建构、代价塑造的资源,由此形成共同文化认同。西方学术方法融入的近代,作为经学文献的《尚书》成了中国历史、文化、措辞学等人文学科研究的史料,传播办法上由国家教诲转为个人研究爱好,影响力急剧低落。
《尚书》西传与中西方文化的互换
经典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文化的互换须要借助其传译和阐释。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开启了中国文化西传的历史,作为承载中国文化精神的《五经》开始与西方文化碰撞互换。
法国传教士在《尚书》西传中用功颇多,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刊于杭州,成为中国最早刊印的西文译本。康熙朝,传教士马若瑟著《经传议论》,个中选译有《尚书》。1770年法国汉学家宋君荣据满文《尚书正义》翻译成法文,又著《〈书经〉中的天文学》,开启《尚书》专题研究。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译《尚书》为拉丁文,传教士顾赛芬译《书经》为拉丁语和法语。
英语天下,1840年,以美国传教士文惠廉选译《尚书》为开端,1846年,英国学者梅赫斯特翻译《书经》,提出了富商遗民东逃美洲建立了墨西哥的不雅观点。1846年麦都思以汉英混排、直译加注办法完成了第一个全译本《书经》,1849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又英译《尚书》,最有影响的是1865年王韬帮助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完成的《书经》译作,中英学者的互助使传译质量有了很好保障。理雅各英译了儒道主要文籍,为将中国文化系统通报到西方作出主要贡献。1904年英国汉学家欧德有《尚书》译本,195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有《书经译注》。
俄罗斯汉学家西韦洛夫分别于1822年和1841年推出了《尚书》俄语译本。201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推出《尚书》俄文全译本,接管了不少《尚书》研究的当代成果。
《尚书》在西方传播由文本译介到思想文化研究,经书成为西方理解研究中国文化的主要管道。中国文化在西方的收受接管有一个变革过程,17、18世纪的欧洲对刚传入的中国文化充满热爱,卷起过一场中国热。但在应对西方工业文明失落败的19世纪,中国文化代价在西方受到批驳,二战之后西方又重新核阅中国文化的代价。汉籍在西方的传译,内容上由经、子转向史、集,并向现当代作品拓展;思想上由基督教经院哲学阐释的误解到对中国文化的真切理解;传译军队上,由以传教士、外交官为主体逐渐转向汉学家、外洋华人、职业翻译家。
《尚书》作为中国上古史和治道之书,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东亚文化。在东学西传过程中,是西方理解研究中国的主要文献。本日,这些民族元典有效的传播和对其代价的深度发掘,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构大国气候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办法,推进以文化代价多元化为根柢的天下多极化建构。故意识地选择构成中国文化核心代价的经典系统、组织专家学者加以传译,应该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手段。翻译界与经典研究专家、经典研究专家与汉学家应该很好互助,推介高质量成果,在世界格局中建构中国文化话语。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20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