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生卒年月不详,仅后人考证就有多种说法,闻一多师长西席说,张旭生于658年,卒于747年;熊秉明师长西席认为其生年不迟于657年,卒年不迟于746年;朱关田则认为,生年约为675年,卒于759年。反正众说纷纭,我们不做历史研究,也就不考证这位狂草祖师到底几时生,几时卒,知道他属于唐朝也就行了。
本日我们研讨的《古诗四帖》,相传为张旭书,由五色笺四幅构成一卷,共四十行,188字,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全卷保存完全,现藏辽宁博物馆。书写内容为四首古诗,前两首分别是南北朝梁庾信《步虚词》之六和之八(五代杨凝式也有《步虚词》刻本流传),后两首是南朝宋谢灵运《王子晋赞》和《岩下一老翁四五少年赞》,个中,“北阙临丹水”的“丹”应为“玄”,为避讳而改;“谢灵运”三字后面的字原为“王”,作伪者把首横去掉了。
这卷书法流传下来,真伪难辨,曾藏于宋宣和内府时是以为谢灵运所书;明代的丰坊首先对作品真伪提出质疑,否定为谢灵运所书;董其昌判为张旭作品;近当代,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等学者经由严谨考证,确定此作为张旭的代表作。
以上是关于《古诗四帖》的一些问题的表述,接下来我们对这作品的前三行进行一番过度的剖析,不喜者可以不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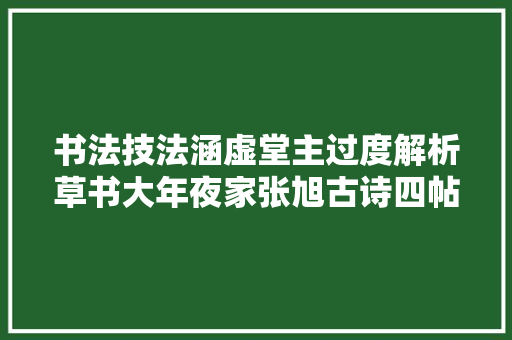
释文: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飘飖入倒影,出没
一、从看“东明”二字看点画的外部形态。
“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这是孙过庭的《书谱》中表述的,这话中“形质”指的是详细的点画形态,“情性”指的是线条中呈现出来的感情。而形质霸占物质性的根本地位,有了形质,情性的表现才会有载体。而草书中,由于使转、牵连,“使转”霸占紧张地位,也便是说,草书以圆笔为主,方笔为辅。这实在说的是点画的外部形态。圆笔的来源是篆籀,相对付方笔来说,圆笔在书写时随意马虎节制提按使转,但诸事都要克制,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一味调皮,就会肥软流俗,以是才须要方笔为辅。
“东明”两字是开篇,调度笔锋之后,以圆笔中锋写出,在“明”字收笔之处以圆点稍作停顿。在这两个字中,“东”略收,由于是收紧的关系,涌现了两个墨团,这是用笔使转时的笔道粘连,险些纯用圆转之法,只有在收笔迁移转变处才略带折法。而“明”字相对付“东”来说,呈放势,其外廓是圆转的弧线,有张力。两个字已经呈现出一种收放的比拟关系。
二、看前三行的节奏变革。
在书法章法的构思上,我们总结出一种组式的构造模式,在前三行中,东明两字连写,九字独立,这个“九”字成为第一行中的节奏迁移转变点,上面是两字实连,下面的“芝盖北”三字连续虚连,以是说,这一行中“九”的书写起到了调度书写速率,调度节奏的浸染。但要把稳的是,书写“九”这个字得顾及到整体的问题,以是这个字的笔势要与下面三字呼应,否则就不是迁移转变点,而是跳脱出去的扎眼之处了。有了“九”的过渡,下面三字就有了一个连续使转的笔势。
第二行在书写之初就得考虑到前一行的问题和效果。因首行中“九”的断点,使得高下有了一个段楷的空间,以是,第二行就涌现了四字相连的使转线条,加上一个独立的“飘”字。“烛五云车”的四字相连与首行中“九”字形成的高下断开之势有了一个比拟。
前两行中连续使转的线条过多,特殊是第二行中险些可以说是一向而下的连续使转所形成连绵之势拉开间隔,扩大比拟,第三行的组别办法险些是字字断开,除了末了的“出没”二字相连,不过这两个字墨色枯,形成一组虚的线条,以是并不抢眼,这两字的的连与第二行的尾部的断开有形成一个对应关系了。
三、看前三行的笔势变革
相对付后来的草书大家怀素、黄庭坚、王铎等来说,张旭这个狂草的祖师级人物,在笔势的变革上并不过分,在第一行总体上来说,呈现出一种直向的平正之势每个字的中轴线险些可以连接成一条直线,而在第二行,行轴线有渐次左移之势,到第三行又复归到一种直向的平正。由此可见,张旭这三行行间分布是较为均匀的,没有太过的偏侧变革,也没有后人书写狂草的那种激越的轴线交叉、挪移、交叠。
四、从“芝盖”两字看体势变革。
前文对“东明”的收放比拟关系稍作剖析,现在说一说“芝盖”二字。从整体上来说,自上而下呈一种左开右合的趋势。这个左开右合之势详细表现为左边的笔画张口大,右边的笔画呈虚线远交于一点的虚交之势。“芝”字草字头的弧线和横画左高右低幅度较大,接下来一组连续使转,至“盖”字的大部分逐渐转为平势。单看“盖”这个字,在前三行中,其下部左合右开的发射状的体势还是很抢眼的变革。
五、从“云车”两字看绞转笔法的书写动作。
绞转是草书笔法的根本。姜白石说“真多用折,草多用转”,提要挈领正草两体在笔法上的根本差异。对付迁移转变的不同,姜白石在《续书谱》中详细写道:迁移转变者,周遭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转。折欲少驻,驻则有力;转不欲滞,滞则不遒。然而真以转而后遒,草以折而后劲,不可不知也。草书用圆转之法其目的是想写的快,只有在一些迁移转变处变方为圆,才能做到利于提按抑扬,又利于中锋用笔。
在“芝盖”两字书写时,就有多条横向延展的笔画,这就牵扯到一个同样线形的方向问题。而“云车”二字与“芝盖”二字连续使转时有相似之处,也便是线条方向的变革问题。而绞转笔法在堂主前文(参看下部链接)中有过论述(环转法),即在转指、转腕的同时施以提按抑扬之法。在“云车”二字中,“s”形曲线的处理,故意识的分成两个小段,即两个“s”形曲线,中间用一个小小的连接线相连。
至于墨色的变革,斜与正的剖析,险中求稳的构造,疏密有致的章法等等,在此就不再做解读。张旭写这长卷的时候未必就有那么多的思考,如果从全体长卷来说,稍显平正了些。但不可否认这一卷书法的技法丰富性是绝无仅有的。仅仅前三行,最让人感到佩服的是从第一笔落下,那种艺术创作的稳定性,各种技能元素的娴熟利用,意境精神的高兴倾泻,都已经显露无疑。他没有给人一种感情的渐变,而是一开始便是高潮,这也就有别于后来的很多书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