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网络。
《食遇》亲笔书法,低廉甜头印章,各种小吃水彩绘穿插,三十三首竹枝词到位,媒介标配,作者心思,一应纸上。
《食遇》的首签会,是在也闲书局举行的。我从网上看到首签场面。
书局卖力人写道:周之江自带羊毫、砚台、印泥,拿着笔的右手如电熨斗把书碾平,正经坐着,拿羊毫为每一位读者题写打油诗,写上文绉绉的“辛丑仲春”,盖上钤印,在一旁看着他的我,竟然有些冲动。书全部售罄,一些人在犹豫,另一些人抱了一摞。卖书的人却忧郁了——书卖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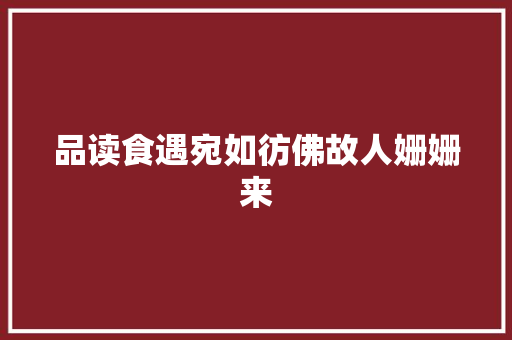
书价不菲,一举告罄,实属少见。
我看到的是,一个诚挚的作者,尊重诚挚的读者。不忽悠,今日已属大德。
十多年前,看到周之江开始在写贵阳百年底层的小吃,牛肉粉、豆腐果、丝娃娃、油炸粑、碗饵糕、破酥包……以遇书房笔名见诸博客。一幅幅人间烟火图,一卷卷浓郁书卷气,一篇篇贵阳浮世绘。写食更写世,隐喻在纸背。
我与他偶有互动。
一本近二十万字的书,称不上鸿篇巨制,之江费时如此绵长,不急不徐,十多个春秋,自然有所寄寓,也可谓精雕细刻之范。
之江也年轻,也激情,也旷达,时有呼朋引类,突袭小吃夜摊,一家家吃将过来,端粉递汤撒葱花,笑颜可掬。他非嘴馋,更非吃货,而是一种经历,一份体验。看他镜片后的沉静便知。如燕达在序中所说,“他笔下的美食天下,更像是对这片地皮的记录与抒怀”。
他的心不在热闹的去处,他的心容不下鼓噪。常日,他在世界迢遥的另一壁,笔墨金石,精雕细刻,如琢如磨,元气淋漓,当然,更有《元史纪事本末》《清史稿》《燕行录》《辰子说林》《分甘余话》《出埃及记》《文明与野蛮》以及“饮冰室”“苦雨斋”相伴相随……享受着他独自的精神夜宴。
滚滚尘凡,万丈鼓噪,同为70后,有人以150迈的速率飙车,有人夜夜笙歌,哪有“但见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落“?
当代主义画家高更,穿着文明人风雅的外套,却痴迷于简陋、闭塞的塔希提岛,痴迷于那里土著的原始生命形态。
周之江系了围腰,厨房细作。这是一种脾气、一种怡悦、一种享受、一种境界。不褪了火气,止了沸扬,是进不了这种格局的。
之江气定神闲,居于一隅,犹如入定,顾盼有情,得意其乐。
《食遇——贵阳小吃竹枝词杂咏纪事》,通篇笔墨,之江石友杨早看得明白:以食见事,由忆及史,小而能大,放亦可收。
概括很准。
这随意马虎么?
《好吃不康健》《花生佐酒慰平生》《惟羊肉和老友最值得涮》《难言正宗 作甚传统》《隔锅何以喷鼻香》……这些篇目,谁一口气厘清微言大意?更不必细究那些不便言说之隐了。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多方位趋同时期,物质的、文化的趋同,作为个体的生命,我们的行踪可能流落很远,我们可能生活在别处,而我们精神、文化的认同,特殊是这饮食文化,这口舌之欲,无法因地域的迁徙而轻易挪位。这或许是尚未破译的生命密码?影象了的,储存了的,再也无法删除,无法清空。
之江的《家宴的风雅与风骨》,意味深长。我的一个朋友看了说,家宴是个性的,自由的,独立的。作者借此表达一种风雅与风骨。
说得够明快了。
吃,不但是吃食品本事,更多是吃人物,吃地方,吃时节,吃氛围,吃心情。杨早如是说。
酒店的宴请多了去了。
酒店里,厚重的窗幔直直地垂下。洁白的餐布、雪亮的杯具明哲保身,做事员个个挂着职业的微笑,一招一式都规格化、程式化,碗筷羽觞调羹有序排列,温热的擦手毛巾叠出花样,上菜井井有条,还闇练地报出菜名,虽然普通话带有浓厚的乡音。拼盘的凉菜是摆成图案的,汤是每人一盅,自酌自饮,井水不犯河水。餐桌内里的转盘缓缓迁徙改变,不用相互劝菜。全体,文质彬彬,温良恭敬。
这哪来之江笔下家宴之乐呢?“早早拟就了食单,毕恭毕敬地誊录好——凉菜:野薄荷拌韭菜、烧椒擂皮蛋、怪噜花生、炸小茨菇;热菜:煎松板肉片、爆炒猪肝、素卷回锅肉、喷鼻香辣铁板米豆腐、炒萝卜缨缨、糍粑豆干;汤菜:筒子骨汤焗萝卜;主食:砂锅饭、鸡汤炒米。不待开吃,看上去便已诱人无比。”
更紧要的是之江写道“家则不同,拖鞋一换,人便放松了一大半。”
神来之笔!
《罗马假日》安妮公主作为王位继续人,在落地长裙掩蔽下,不是悄悄腿去那双束脚的鞋,赤脚站立,然后随了派克兜风罗马?
之江又说:话说回来,以“家宴”为招徕的做法倒还真是古已有之,最近读到《一氓书缘》,里面引用明伦哲如咏“谭家菜”的诗云:玉生俪体荔村落诗,最後谭三擅小词。家有籝金
之江的风格,受到杨早调侃:“作者还多爱掉书袋的,隔两段就撞见书名号,统计一下,七八万字的内容,引书与文,将近200种!
个中:《黔语》《武林往事》《清稗类钞》就算了,跟内容还贴切,《中国饮食文化史》《欧洲文化饮食史》《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也还沾边,梁实秋周作人汪曾祺流沙河不在话下,《文明与野蛮》《查令街八十四号》《燕行录》会不会扯太远了?你是在写食话还是书话?”
侃。一个嗜书成瘾者,各种文籍会排着队为他的食话作注、求证。而且,岂止食话?之江的天下里,书与人一体,水乳交融,他注定冥顽地用笔墨笼罩市井,为美食发声。
《食遇》中,文学呼吸之气浓郁,学识灵性气息可辨。美食弥漫的喷鼻香味中,处处是生命的脉动。投箸举杯,是生命自带的一种原来,一种落定。
气韵何来?
之江祖籍钱塘江畔,母亲祖籍宁波,他气接明代山阴(今绍兴)张岱、绍兴知堂、高邮汪曾祺……偕老一代下江人之韵。
张岱,甲申之变命运迁移转变,逸民张岱看破繁华,隐迹于会稽山,看葛岭峰上的初月,钱塘江下的新潮,才有凄凉沉重、冷隽超然。穿过“鹿鹿风尘”,伤泪滴过,透出的还是清新优雅,时杂诙谐,真切至极。
张岱的笔墨属明末的古文,文短意赅,字字珠玑,句句生辉。之江写景写事用词讲求简练,与张岱一样兼引诗词典故,有“尺牍体”味道。
知堂的散文为散文之极致,耐读而难学。他闲散的姿态,夷易的笔调,背后却蕴藏着虔诚、真纯和理智。粗砺而细致,俗陋而精美,散漫而流畅,随意而深刻。前期舒徐清闲、信笔所至,后期枯涩苍老、出神入化,归入古雅遒劲—途。他的《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意见意义平淡兼有涩味。他写的故乡的野菜、苦雨、鸟声、篷船、金鱼、两株树,做到平淡极境。他晚期的条记体篇幅很短,三五百字,浅近的文言,融贯古今、凝涩简朴,寥寥数语,蕴藏着丰富内涵。
之江清音独远,此《食遇》缘起,也与知堂老《老虎桥杂诗序》关联。知堂老说,我就有一点散文的资料,却用限字用韵的形式,写了出来,这东西以前称之为打油诗。之江践行“平生易近故事岂容嗤”,故作《食遇》,“略记过往及当下的食事,抒发少许隐蔽在一饮一啄背后的感慨,聊且博人一乐或一叹”。
《食遇》的贵阳方言,我们心中有,我们笔下无。读来妙趣横生,妙意难言。
他写素粉:“素粉偏搁油辣角,芽菜过水一小撮。人言此物丰滋味,中有乡思不可说。”
写肠旺面:“肠糯旺嫩面要脆,平民所爱是杂碎。免青红重今不闻,打杯散酒容小醉。”
写豆沙窝:“糯米捶面握粑粑,馅子要用咸豆沙。铁镌滚油炸黄脆,与糖麻圆作一家。”
套用杨早的话说,这是写给贵阳饮食文化的情书。小吃背后折射的,不仅是人类对世间滋味的挖掘与追寻,更是一方水土对食俗风味的塑形与细刻,是口腹之欲背后的人生与民气。
至于竹枝词,之江说,是“韵用吾乡土话,平仄亦未尽和于律”。但它是之江的独门武器,竹枝词生发出的描述、考证与感慨,才是将小吃写成“大事”的触碰开关。
有幸品读《食遇》,对付在贵阳生活六七十年的我,宛如彷佛故人姗姗来。
文/卢惠龙
视觉/赵珊珊
编辑/赵相康
二审/曹雯
三审/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