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默写古诗,唐代墨客李益的《夜上受降城上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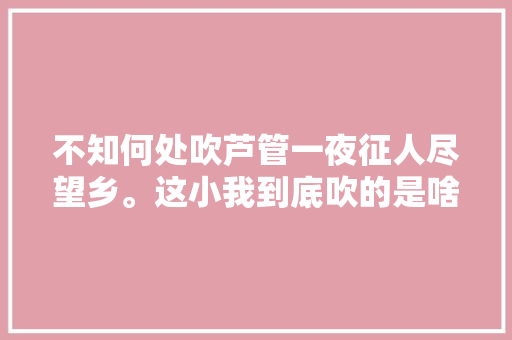
一夜征人尽望乡。
“不知何处吹芦管”中的“芦”被相称一部分学生写成了竹字头。
这个怎么办?我不习气罚抄,由于以为那样做太low,缺少聪慧含量。还是要想办法要让学生既知其然,又知其以是然,把来龙去脉讲清楚。于是,动手查阅干系资料。
芦管:乐器名。以芦苇的茎部制成的乐器,是胡人吹奏乐器的一种。
“汉典网”中关于“芦管”的这个阐明和我原有的认知不谋而合,而且,恰好便是举的“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于是,我开讲了。
很多同学把“芦管”的“芦”写成了竹字头,显然,是对这个词语不理解。所谓芦管该当因此芦苇的茎为原材料制成的大略乐器。我老家在北方,那个地方少有芦苇,但春天到来时,小孩子会把刚萌芽的杨柳的枝条里面的芯抽出来,留下外皮做成大略的哨子,可以吹出声音来。
我们看“芦”和“苇”都是草字头,由于芦苇是草本植物,以是用草字头。
在我们曾经学过的,或者一些比较熟习的诗歌中,也有“芦”这个字,比如:
苏轼的《惠崇春江晓景》中的“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里的芦芽便是芦苇的新苗。
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个中的黄芦便是一种芦苇。
司空曙的《江村落即事》中有:“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胡令能的《喜韩少府见访》中有“儿童不惯见车马,走出芦花深处藏。”
芦苇是比较常见的植物,以是在很多古诗中都有涌现。须要把稳的是,我们很多人误以为芦苇花下所丛生的白毛是芦苇的花,古人也这么认为,实在它只是外不雅观似花,并不是真正的芦花。
讲完这些,我有一点儿小小的得意,乃至以为挺完美。由于这个讲法坚持了我在讲解错别字时一以贯之的原则,坚持从字源动手,从语境动手,尽力给学陌生解白,而且还要做到温故而知新。
但是,得意没多久,事情就发生了翻转。在批改学生交上来的错别字诊断书时,创造有一个学生在剖析“芦管”中的这个错别字时,引用了这样一段资料。
芦管,起源于古代波斯(今伊朗),是古代西域各国通用的乐器筚篥,东晋之时传入中原,南北朝至唐代极为盛行。
这个资料哪里来?上网查一下,原来是“百度百科”中有专门的词条。我由于先入为主的缘故原由,认定“汉典网”中关于芦管的阐明可以接管,就没再关注其他资源中关于该词的阐明。
顺着这个百科词条看下去,冷汗就要快下来了。
芦管管身竹或铜制,竹芦管用当地“菁竹”制作,长约19厘米旁边,开七孔,上端装一芦苇制簧哨。
这个简介颠覆了我原有的认知,芦管这个乐器虽然利用了芦苇作为原材料,但显然芦苇不是主体,而主体是竹子所做。而且,简介中特殊说“芦管擅于演奏速率较慢、缠绵悱恻、哀伤动人的乐曲。”
末了,该词条还补充了白居易的《听芦管》一诗,作为证据。“幽咽新芦管,悲惨古竹枝。似临猿峡唱,疑在雁门吹。……”
这么说,难道是我讲错了?细细琢磨一下,还真有可能。
情由有二:
一、如果仅仅是芦苇的茎部制成的大略乐器,可能发出的声音不会很大,不会传播得很远,可能不会“不知何处吹芦管”,就造成“一夜征人尽望乡”的效果。纵然“尽望乡”有一些夸年夜的成分,但总得相称数量的人能听到吧。
二、以履历来说,用芦苇的茎部制成的大略乐器,一样平常音调比较轻快单一,不可能演奏出缠绵悱恻、哀伤动人的乐曲。
然后,再细琢磨,创造问题越来越多。
题目是《夜上受降城闻笛》,为什么诗句中却说“不知何处吹芦管”了,这个“笛”和“管”什么关系?
是像教材下面对该诗阐明的那样,“芦管”便是“芦笛”吗?两者是同一种东西吗?那诸如芦笳、胡笳、羌笛、羌管等在诗词中常常涌现的乐器名称,它们各自又是什么样的乐器呢。
既然芦管是竹子所制,为什么偏偏又叫芦管,难不成是故意难堪我,让我在字源上不给学生阐明还好,一阐明学生会反而更含糊。
……
带着这些问题再研究,查阅各种资料,又和语文组新来的研究生毕业的小马老师谈论,她又非常热心地给我供应了很多资料,于是又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原来在我提出这些问题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对此做了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和考证。
大致梳理一下,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1.历史发展过程中,乐器名称同质化的方向越来明显。墨客在诗作中这些乐器的名称常常可以通用。诗歌中常常涌现两种乐器名称指代同一件乐器的征象。大约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把什么吹长号,吹短号,吹圆号,乃至吹喇叭,吹唢呐之类的统统称之为吹号是一样的。
2.如果细致区分,芦管,芦笳,芦笛等等,又有不同材质制作的差异,有不同工艺的差异,而且不同时期又各有发展变革。以是从名物学的角度来说,教材年夜将“芦管”阐明为“芦笛”实际上并不确切。还不如不阐明,直接就说“芦管”就好。
3.古人“芦”和“竹”可以互称。“芦”和“竹”在形态上附近,大约古人认为它们属于同一种类,而且,现在也有芦竹这样一栽种物。
当然,在所查阅的各种资料之中,也有很多相互抵牾的地方,只能依据个人的判断择善而从。
实在,在更深入探究“芦管”是什么乐器之前,我在查资料时,就有很多新的收成,新的创造。
比如:
“芦芽”到底是芦苇的新苗,还是像某些工具书或者网上资料中说的便是“芦笋”。虽然时常吃芦笋这种蔬菜,但是真的还是只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不知道它是怎么样一栽种物。
“黄芦”是一种芦苇,还是一种类似于本日说的“黄栌树”这样一种木本植物,“地低湿”和“黄芦苦竹绕宅生”有若何的物候上的关联。
“枫叶荻花秋瑟瑟”中很多注释将“荻花”直接阐明为“芦花”,那“荻”和“芦”又有若何的异同呢,再进一步说,“蒹葭苍苍”中的“蒹葭”又和芦苇有什么关系呢。
“芦”本来是形声字,声旁是“卢”,但为什么现在写成了“户”,类似的还有驴、炉、庐等,真正以“卢”为声旁的诸如栌、鲈、泸、胪、垆、鸬等,两者之间的差异何在,汉字简化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
“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作者依据若何的履历做出的判断,这句话和前一句“蒌蒿满地芦芽短”存在若何的内在联系呢?
如果我们常日理解的芦苇的白毛不是真正的“芦花”,那真正的芦花又是什么样的。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更进一步明确了不同的乐器有不同的音色特质,能够演绎不同风格的乐曲,由此更深刻地理解了干系诗词中的音乐与诗词主旨的关系。
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连累累连,枝枝节节,就像是鲁迅在百草园中拔何首乌的根一样,虽然没有找到一块像“人样儿”的,但这个过程就足够好玩儿,足够不亦乐乎。
如果不是为了想办法给学生讲得更清楚,我自己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可能就滑过去了,不会深入琢磨思考。为了这一个字,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还乞助大学同学,乞助生物老师,乞助同事,花费了十几小时的韶光。正是这个过程,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传授教化相长”。
我所查阅的这些资料,收成的这些内容,都要讲给学生吗?
当然要讲,但不是全部都讲,不是事无年夜小地讲,而是要有选择地讲。既然之前关于“芦管”的问题讲错了,就要纠正过来。
我先带着学生回顾上一节课怎么讲的“芦管”,为什么“芦”必须写成草字头,而不是竹字头。大多数学生都记住了。我话锋一转,见告他们这个情由虽然看似完美,但是我讲错了。听我这么一说,学生都大吃一惊。
接下来我大略地给他们梳理了一下我最近在查找资料过程中的各类收成,并由此着重分享了我的一些心得。
我是想让他们把我所理解到的这些知识都记住吗?不,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拿这个举一个例子,见告他们如何创造(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办理问题。不要知足于回答老师的提问,回答试卷的提问,真正有代价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彻底办理的,要学会和问题和平共处,要学会带着问题提高。
很多时候,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并不最主要,提出一个有代价的问题更主要,在这个思考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快乐更主要,唯其如此,才能够将学习引向深入,这是有内驱力的主动的学,而不是依赖外力的被动的学。
然后,我又给他们分享了一首诗。
彩蝶双起舞,
蝉虫树上鸣。
明月当空叫,
黄犬卧花心。
传说这首诗是一个秀才所作。当年王安石看到之后,读了前两句以为不错,但读了后两句,不禁哑然失落笑。怎么回事?明月怎么能会叫,黄犬那么大的动物怎么能躺卧在花心之中,显然狗屁不通嘛。
于是,王安石大笔一挥,将后两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荫”。这样一来,文意就彻底理顺了,明确了。修正之后,王安石也以为很得意。
然而,事情又发生了反转。
良久之后,王安石去了秀才所在的地区,有光阴创造,原来,当地有一种名为“明月鸟”的小鸟,叫声很清脆,还有一种名为“黄犬虫”的小虫子,常常伏在花蕊之中。
原来不是秀才错了,而是王安石错了。王安石在这件事上由于先入为主,也由于见识有限而犯了错。
末了,我见告学生两个道理:
1.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
当我们创造一个问题,考试测验着去办理一个问题时,要故意识地查阅各种资料。但又不能查到了资料就轻易地相信,要多个不同的资料比拟确认,要择善而从。
2.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韩愈《师说》
不要老师说什么便是什么,说什么都当成对的,老师也有错的时候。老师能教给学生的绝对不但是知识,更主要的是学习的态度,学习的方法。只有这样,才会“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