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并不大却很热闹好玩,尤其四合院的犄角旮旯太适宜小孩子们捉迷藏了,每次都弄得全身的麦秸秆和杂草灰尘,却玩的很愉快,小饭桌和椅子、床单都能派上用场,用小板凳搭火车,玩过家家的游戏等等,四合院里切实其实便是儿童乐园、快乐的老家。
记得那时北厦(老家那里的土话把屋子叫做“厦”)邻家的房顶上,常有鸽子咕咕、咕咕吹着鸽哨,然后又扑棱棱展翅飞向天空。姑姑家的厅堂里,则有个燕窝,燕子每天都飞进飞出的,有几只刚出生的小燕子从窝里伸出小脑袋,张着尖尖的小嘴正嗷嗷待哺呢,样子挺可爱,引人怜惜和喜好。院子里常常有几只母鸡带领着各自的一群小鸡仔,喔喔喔、啾啾啾清闲地到处觅小虫子吃。每天,天不亮各家养的大公鸡就扯着嗓子定时打鸣,此起彼伏的叫着,有时竟连起来,仿佛在比赛谁的嗓门亮,声声唤醒人们快点起床。清晨,屋檐下的小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一直,一下子在院子里飞,一下子又在晾衣绳上荡秋千。总之,四合院里热闹非凡。姑姑家那时还养了一只猫,那只猫白天在院子里乱窜逮老鼠,到晚上便回屋了,一到冬天总爱赖在热炕头上打盹睡觉打呼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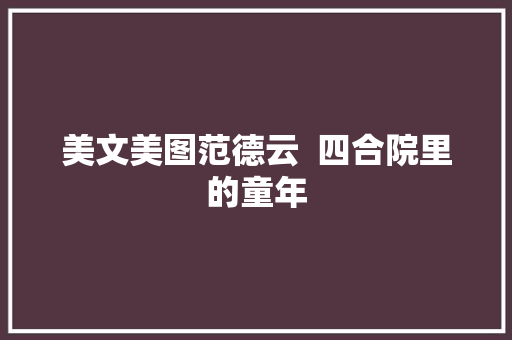
四合院里,谁家做了好吃的饭菜,都少不了孩子们的一份。记得有一次北厦姐家(实在这个姐姐比我大好多岁,只是她的辈分小,她的六个孩子中有四个年事都比我大)做了焖面,就端给我一小碗吃,当时以为特殊好吃。谁家做了特殊的吃食,都要分给邻居们吃。姑姑那时会做黒面酱,便是用发了霉的干馍馍做的,详细怎么做,因我当时太小没把稳过(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操作步骤,也从没留神过),脑筋里模糊的印象便是把那个发霉长了毛的馍块掰碎,放到缸里,加入适量的盐和水搅和均匀,头几天要反复搅拌几次直到变成糊状,然后彷佛还要抹上泥巴把盖密封好,再放置在北屋邻居家的窗台下面晒(期间当然还要防止雨淋的),大约要暴晒一个月就成了,打开盖子就能闻到诱人的酱喷鼻香味了。当时,院子里还有一个小风景,便是糊在墙上的袼褙,所谓的“袼褙”,便是把不用的碎布头用面糊糊(用面粉熬制的浆糊)一层层裱糊在墙上抹平整,晾晒干透,成为布板,碎布片大小形状不一,颜色互异,只要适当裁剪对接好就行,粘贴至1.5毫米旁边,俗称“打袼褙”。那年月,家家户户经济条件有限,屯子人很少买鞋,穿的都是自家做的千层底布鞋。现在想一下,那一张张贴在墙上的袼褙,多像是一幅幅的抽象画呢。还有用剩布头做的花色小书包、门帘,切实其实便是手工制作的民间工艺品。那时的屯子人,除了很少买鞋,其余便是为了省钱很少买洋布,床单、被里(或被面)、棉衣棉裤的里布等大都是用自家织的粗土布做的,经济实用又舒畅,可便是织布的工艺流程太繁芜。依稀记得个中有一道刷线工序,每次刷线时姑姑一大早就得忙活着做准备事情,然后和几个邻居们要把一大盆一把一把的线抻开,再框在撑子上,两头固定好,记得线从院子的南头一贯拉到北头,像一条长长的传送带,一人拿把刷子,一节一节的逐步移动撑子,一点一点的往前刷线,将那些一绺一绺的线刷开、刷直、捋顺,就像梳理头发似的,之前把颜色都搭配好,其间还要仔细的接线头等等,这是一项非常细致繁琐的工序,也是织布前的主要一环。纵然火辣辣的日头晒着也不能停下手中的活,中午大家吃完饭再接着干,常常要干到太阳快落山,也便是险些要忙活一天的韶光才能完成此项活。由于年代的久远,好多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楚,只能凭印象记个大概,大概有些地方影象有偏差说的并不准确,但记得当时大人们忙得不可开交,院里的小孩子们却老想跑到跟前凑热闹。
四合院里谁家有困难碰着难事大家都相互帮衬,平时说话和和气气的,邻里和蔼相处,其乐融融,就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那时候,姑姑家在村落外的沟梁上种了两棵柿子树,以是每年秋日都可以吃上甜甜的柿子,晒在姑姑家窗台和阁楼天窗上火红的柿子,吃一口最是甜在我的心窝里,还有那用柿子做的醋,抿一口就能酸到骨子里。
夏天的夜晚各家就在院子里铺上凉席乘凉谈天,这时,姑姑总是手拿一把蒲扇,一边一直地给我扇风驱赶蚊子;一边给我讲好听的神话故事,每当此时,我便好奇的瞪大眼睛,凝望着夜空的满天星星,发呆愣神,并一直地缠着姑姑追问。冬世界学回来,坐在热热的炕头上闻着饭喷鼻香和姑父旱烟的喷鼻香,身上立马感到暖和,一点儿都不冷了。犹记得,在隆冬夜晚灰暗的石油灯下,姑姑一针一线为我们缝制过冬棉衣棉裤的身影... ...
四合院里我的童年,蓝蓝的天空,残酷的阳光,天真天真,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儿,更有姑姑百口对我浓浓的爱!
想起来,便觉一股暖流流遍全身。
哦,那高枕而卧的快乐光阴!
那天真烂漫的孩提时期!
童年的光阴,是一首姑姑家四合院里的歌谣。
童年远逝,仿佛做了一个俏丽的梦,梦醒时分,变成甜美的回顾。这回顾,一半留给自己来珍藏,一半用来怀念故去的亲人。
作者简介
范德云,生于1965年,山西省临汾市人,1985年毕业于山西太原电子技能学校,1997年得到山西师范大学汉措辞文学专业自学考试毕业证书,爱好文学字画。就职于中国铝业山西分公司热电分厂,2015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