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里最吉庆的节日,是要想法子给新的一年,讨个辞旧迎新的好彩头的,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中国人过年,春联是必不可少之物。而写春联则是传承千年的宝藏,是红红火火的年味。
年终将至,如果您今年相应号召,决定“就地过年”,那也千万不要以为孤单,由于从小年直到除夕,我们都会陪着您一起,回味那些小时候过年的影象。
当然,过年自然少不了礼物,我们的礼物藏在文尾,请您查收!
写春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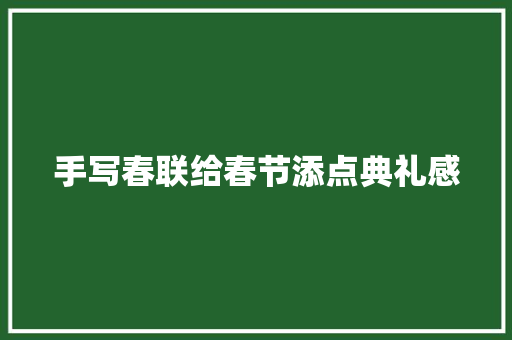
过年写春联、贴春联,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习俗,已有悠久的历史。
宋代大墨客陆游曾专门作过一首写春联的诗——《大年夜雪》:
北风吹雪四更初,
嘉瑞天教及岁除。
半盏屠苏犹未举,
灯前小草写桃符。
“桃符”便是春联。
听说,春联最早是由桃木板演化来的。相传,桃树下面有两个神,这两个神专门管理各路鬼魔,哪个鬼魔如果不诚笃,做出孽事,他们就把哪个鬼魔拿下,然后扔给猛兽,让其成为猛兽的美餐。因此,秦汉以前,每逢过年,人们为了驱鬼避邪,吉祥安然,就找两块桃木板,分别描上两个神的像,工工致整地挂在大门的两边,叫“桃符”。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元日》一诗中曾写道:
炮竹声中一岁除,
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两块桃木板多大呢?《后汉书·礼仪志》中有记载:六寸长、三寸宽。到五代十国时,有一年过年,
后蜀主孟昶以为,年年在桃木板上描神像太乏味,没多大意思,便别出心裁,让一个大学士把“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两个句子分别写在两块桃木板上,中国第一副春联,就这么出身了。
后来,经由逐步的发展和演化,纸张涌现了,由于桃木是赤色的,用红纸替代,“桃符”也改称“春联”了。
小时候过年,买不起春联,村落里识字的又少,能写春联的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每到过年,能写春联的那几户人家,便去了好多求写春联的人。有的人由于忙,没顾上去求人写,或年年求人家写觉得不好意思再去了,过年就把红纸裁裁,直接在门上贴红纸。
爹说,他小时候过年我爷爷就常常这么贴。
记得那时,爹去求人家写春联,都是提前买上盒烟揣兜里,到人家家里,摸出来放桌上,然后小心着见告人家裁好的红纸中,哪副是大门上的,哪副是上房门上的,哪副是灶房门上的,等等。
人家暂时愣住羊毫,拿着墨块,边在石砚上不紧不慢地研着,边看着爹一副副揭给人家看,然后见告爹,放箱子顶上吧,年三十上午再来取,接着低头连续写。
有“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啦,“虔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啦,“旭日门第春常在,勤俭人家庆有余”啦,“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啦,等等,基本都是固定的老词。
现琢磨延误工夫,来不及。
每年临过年的时候,村落街上便时时有拿着红纸到能写春联的人家去,或从能写春联的人家拿着写好的春联出来的人。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了羊毫字课,每周一节,叫“写仿”,先把字帖垫在能透过字来的那种专门的大方格本下,按照老师讲的握羊毫的办法和点、撇、捺、勾的运笔技巧,一笔笔随着描,老师认为描得好的,批作业时,会在这个字的阁下用红笔圈个圈。描得差不多后,老师不叫垫字帖了,而是在黑板上用粉笔写几个字,叫直接在方格本上写,先大略的字,然后繁芜的字。
到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临过年时,爹说,你都在学校练羊毫字这么永劫光了,今年过年写春联,咱不求人家了,自己写。
我挺忐忑的,从来没写过,怕写不好。
爹说,别写错就行,好点孬点不要紧,字不都是练的吗,逐步就好了。爹提前买了红纸,怕我写错,还多买了一张作为预备。那时,我们家已买了一台木壳收音机,“红灯”牌,就在我们上房那张老式桌子的左后角放着,上面盖块花毛巾,有一天晚饭后,收音机里说要以记录速率播送新春联,我赶紧拿出本子,就着油灯记录了一些。
春联纸爹已提前裁好,我写时他在阁下给我研墨,让我别紧张,我琢磨了琢磨,决定还是先写横批试试。横批是四张正方形的红纸,一个字一张,对角写,如果写坏一张,不影响别的。
为了把字写正,避免东倒西歪,我把四张纸摞在一起,叠上了方格印,然后拿过一张,蘸蘸爹研的墨,写下了“五”字,旁边瞅瞅,又写了“谷”,接下来是“丰”和“登”。爹说:“这不挺好吗?”说着,拿到了炕上,晾。我又取过与这副横批一组的那副春联纸,轻轻展开叠上方格印,写上联、下联。每写完一张,爹拿走一张。不到一个半小时,我们家所有的春联全都写完了。
那年,我十四岁。
贴出来后,正楷的羊毫字一笔一画,黑黑的,衬在鲜红鲜红的大红纸上,特殊鲜艳。出来进去,往门框上瞅一瞅,就像小说处女作得以在有名杂志上揭橥一样平常愉快。
爹从此对我说话,也不再是命令一样,而是像对成人似的以商量的口气,我觉得自己忽然间终年夜了不少。那时我还没有钢笔,舍不得买,过年走亲戚,竟悄悄在左上衣口袋别了一支圆珠笔。
从那往后,我们家写春联,再没求过人。而且,第二年,村落里还有人拿着红纸到我们家,叫我给写春联,记得我写了五家。每来一个,爹都笑哈哈地接待,还给人家泡上茶,陪着坐在炉子旁烤着火拉呱。
此后,直到十八岁我坐火车离开家,才换成了弟弟。
以上内容来自于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