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
《秋》
丰子恺
我的年纪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两年了。不解达不雅观的我,从这两个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与影响。虽然明明以为自己的体格与精力比二十九岁时全然没有什么差异,但“三十”这一个不雅观念笼在头上,犹之张了一顶阳伞,使我的全身蒙了一个暗淡色的阴影,又仿佛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往后,虽然太阳的炎威依然没有减却,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没有降落,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驱,大地的节候已从今移交于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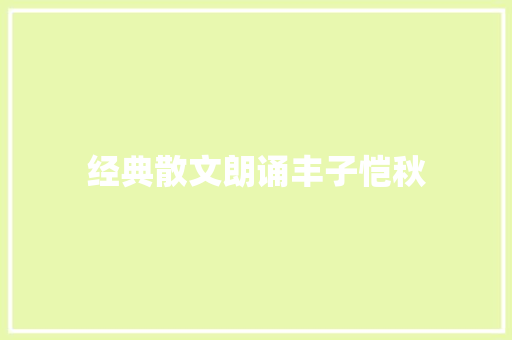
实际,我两年来的心情与秋最随意马虎调和而领悟。这环境与从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欢畅杨柳与燕子。尤其欢畅初染鹅黄的嫩柳。我曾经名自己的寓居为“小杨柳屋”,曾经画了许多杨柳燕子的画,又曾经摘取秀长的杨柳,在厚纸上裱成各种风调的眉,想象这等眉的所有者的颜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与口。那时候我每逢早春时节,正月仲春之交,瞥见杨柳枝的线条上挂了细珠,带了模糊的青色而“遥看近却无”的时候,我心中便充满了一种狂喜,这狂喜又急速变成焦虑,彷佛常常在说:“春来了!
不要放过!
赶紧设法招待它,享乐它,永久留住它。”我读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经至心肠冲动。以为古人都嗟叹一春的虚度,前车可鉴!
到我手里决不放它空过了。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清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愈甚。那一天我总想有一种足以充分酬偿这佳节的举行。我准拟作诗,作画,或痛饮,漫游。虽然大多不被实施;或实施而全无效果,反而中了酒,闹了事,换得了烦懑的回顾;但我总不灰心,总以为春的可恋。我心中彷佛只有知道春,别的三季在我都当作春的预备,或待春的安歇韶光,全然未曾把稳到它们的存在与意义。而对付秋,尤无觉得:由于夏连续在春的后面,在我可当作春的过剩;冬先行在春的前面,在我可当作春的准备;独占与春全无关联的秋,在我心中一向没有它的位置。
自从我的年事告了立秋往后,两年来的心境完备转了一个方向,也变成秋日了。然而环境与前不同:并不是在秋日感到象昔日的狂喜与焦灼。我只以为一到秋日,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且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暂时失落却了自己的所在。而对付春,又并非象昔日对付秋的无觉得。我现在对付春非常厌恶。每当万象回春的时候,看到群花的斗艳,蜂蝶的扰攘,以及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地滋长繁殖的状态,我以为天地间的凡庸、贪婪、无耻、与愚痴,无过于此了!
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看到柳条上挂了模糊的绿珠,桃枝上着了点点的红斑,最使我以为可笑又可怜。我想唤醒一个花蕊来对它说:“啊!
你也来反复这老调了!
我眼瞥见你的无数先人,个个同你一样地出世,个个努力发展,争荣竞秀;不久没有一个不干瘪而化泥尘。你何苦也来反复这老调呢?如今你已长了这孽根,将来看你弄娇弄艳,装笑装颦,招致了蹂躏、摧残、攀折之苦,而步你先人们的后尘!
”
实际,迎送了三十几次的春来春去的人,对付花事早已看得厌倦,觉得已经麻木,激情亲切已经冷却,决不会再象初见世面的青年少女似地为花的幻姿所诱惑而赞之、叹之、怜之、惜之了。况且天地万物,没有一件逃得出兴废、盛衰、生夭、有无之理。过去的历史昭然地证明着这一点,无须我们再说。古来无数的墨客千篇一律地为伤春惜花费词,这种效颦也以为可厌。如果要我对付世间的生荣去世夭费一点词,我以为生荣不敷道,而甘心欢畅惊叹统统的去世灭。对付前者的贪婪、愚蠢、与胆小、后者的态度何等谦善、悟达,而伟大!
我对付春与秋的取舍,也是为了这一点。
夏目漱石三十岁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处必有暗;至于三十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处暗也多,欢浓之时愁也重。”我现在对付这话也深抱同感;同时又以为三十的特色不止这一端,其更分外的是对付去世的体感。青年们恋爱不遂的时候惯说存亡活去世,然而这不过是知有“去世”的一回事而已,不是体感。犹之在饮冰挥扇的夏日,不能体感到围炉拥衾的冬夜的滋味。便是我们阅历了三十几度寒暑的人,在前几天的炎阳之下也无论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围炉、拥衾、浴日等事,在夏天的人的心中只是一种空虚的知识,不过晓得将来须有这些事而已,但是不可能体感它们的滋味。须得入了秋日,炎阳逞尽了威势而逐渐退却,汗水浸胖了的肌肤逐渐紧缩,身穿单衣彷佛要打寒战,而手触法兰绒以为快适的时候,于是围炉、拥衾、浴日等知识方能逐渐融入体验界中而化为体感。我的年事告了立秋往后,心境中所起的最分外的状态便是这对付“去世”的体感。以前我的思考真疏浅!
以为春可以常在人间,人可以永在青年,竟完备没有想到去世。又以为人生的意义只在于生,而我的生平最故意义,彷佛我是不会去世的。直到现在,仗了秋的慈光的鉴照,去世的灵气钟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欢,是天地间反复过亿万次的老调,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的安然的度送与脱出而已,犹之罹了猖獗的人,病中的颠倒迷离何足计较?但求其去病而已。
我正要搁笔,忽然西窗外黑云弥漫,天涯闪出一道电光,发出模糊的雷声,骤然洒下一阵夹着冰雹的秋雨。啊!
原来立秋过得不多天,秋心稚嫩而未曾老练,不免还有这种不调和的征象,恐怖哉!
1929年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