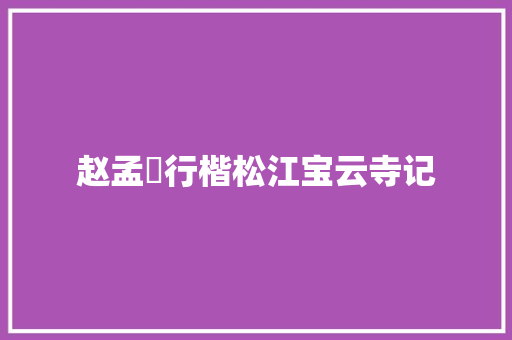
松江宝云寺建成于唐大中十三年(859年),位于今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原属松江县)。相传“宝云寺”曾有1048间,梵宇轩昂,绵延数华里,号称“江南名刹之五,华亭之最”。由于饱经自然磨难及战火沧桑,“宝云寺”屡修屡毁。元代重修时方丈净月立碑,牟巘撰文,廉密知儿海牙(汉名廉恂)篆额“重修宝云寺记”,碑文《松江宝云寺记》由中国古代大书法家赵孟頫书。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当地人均将此碑称“子昂碑”。光绪版《重修华亭县志》载“咸丰十一年毁于兵”,仅存山门及“子昂碑”。1966年,山门及“子昂碑”均被人为毁坏。碑额及不敷原碑十分之一的残碑(共70余字)现存于亭林镇政府内。
赵孟頫所书《松江宝云寺记》有两个版本。
一是墨迹本。赵孟頫书《松江宝云寺记》时年五十有四,正值书法艺术出神入化、渐入化境,可称为极品。故有真迹影印多见于各种出版物,也有少量影印单行本在民间流传。其真迹是否已由博物馆收藏还是仍留存民间,目前尚无资料稽核。近当代字画家徐宗浩(1880-1957)对赵体有深入研究,模拟其作品可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1928年,徐宗浩根据成氏“物色得之”的影印本“亟付影印,以广其传”。1995年上海公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赵孟頫墨迹大不雅观》、1997年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书法教程·赵孟頫行书》、200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赵孟頫书法》、2002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赵孟頫名帖今写示范》等都收录《松江宝云寺记》。墨迹本上有“项子京家收藏”等39枚收藏章,解释《松江宝云寺记》真迹曾被来岁夜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明代人,字子京,号墨林隐士、墨林居士、喷鼻香严居士、退密斋主人等等,浙江嘉兴人)收藏。《松江宝云寺记》也曾被清陕甘总督富呢扬阿(满人,曾任浙江巡抚)收藏。据记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月朔,林则徐应富呢扬阿之邀赴午宴,共同玩赏富氏珍藏的赵孟頫所书《宝云寺碑》真迹。
现在所见的墨迹本并非《松江宝云寺记》全文,有资料说,“该帖充满传奇色彩,曾被当过窗户纸,后被抢救了回来”。徐宗浩在其收藏的影印本中题“晚归陈朝下阙二百二十九字殊为可惜耳”,同时指出“大理大夫”、“集”、“书”等14字“为后人所补,颇失落吴兴笔意”。因此,见于各种出版物的赵氏墨迹,存在诸多遗憾。
另一个版本是碑拓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号称“清代订正第一人”的顾千里(1766~1835)及“清代藏书家”瞿镛(约1800~1864)珍藏的《松江宝云寺记》碑拓。此件或许是现存的最早的拓片。但毕竟石碑历经数百年,损伤很大,拓片中不少笔墨难以辨认。2005年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晚清期间的拓片,比国图藏品要有更多的笔墨丢失。听说建国前后有不少人碑拓,但拓片石沉年夜海,目前还可见到的唯有一亭林人的拓片照片,但显然增加了石碑风化痕迹。
实在,墨迹本与碑拓本源于同宗。笔者将残碑照片与墨迹本通过打算机抠图技能进行逐字比照,字形构造及笔画间距完备同等,解释两者出自赵孟頫同一手稿当属无疑。
奇怪的是,墨迹本与碑拓本除了“阙二百二十九字”外,上题款与题名也不一样。墨迹本上题款为“赵孟頫书并篆额”,个中“赵孟頫”、“篆额”为真迹,“书”与“并”疑后人所补,而碑拓本是“赵孟頫书,资德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廉密知儿海牙篆额”,这显然是由于作为窗户纸抢救不完全,而后人又无法补足所致;墨迹本题名是“大德十一年十有二年”,碑拓本为“至大元年五月望日”,两者相距五个月旁边,或许是由于上石之前变动年号之故,改书题名。
建国往后当地新修地方志、专业志,都收录《松江宝云寺记》碑文,基本上均出自民间流传的碑拓本。由于对拓本辨认及理解的差异,或许是印刷排版之误,诸文不尽同等且有不少不当之处,也在情理之中。
今以墨迹本、碑拓本及光绪版《重修华亭县志》“重修寺记略”一文互为补充,并查阅有关史料,对《松江宝云寺记》碑文重加整理,现将全文960字抄录于下。为免歧义,下文中的通假字、异体字等保持原状,不作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