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鸦的眼睛里,洁白的天鹅是有罪的,就连雪都是有罪的。
《百家讲坛》播出后,文化名人纷纭飞进平凡百姓家,走进大众视野。他们不再囿于三尺讲堂,只是手中拿着粉笔凭借诗人意气,挥斥方遒。
《品三国》的易中天、《明亡清兴六十年》的阎崇年、讲《史记》的王立群。
这些学者都是从三尺讲堂走上百家讲坛,各有各的特色,或诙谐诙谐,或基本管理,或锐利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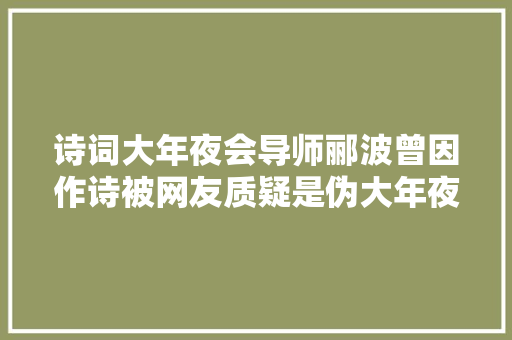
那么郦波呢?这个百家讲坛最年轻学历最高的主讲人,如果没有突出的优点,百家讲坛也不会为之开先例,不是探求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或者人气颇高的新晋教授,而是约请年轻的他成为主讲人之一。
文化类节目在当下快餐时期,就像是一股“清流”,迅速出圈,也将这些文化名人捧红,人红是非多,这些名人没有一个能冲破人设崩塌的魔咒。
这个中,有的人确实才疏学浅,但是也有一些人只是被“碰瓷”。
《中国诗词大会》的导师一个一个火爆出圈之后,又由于各类缘故原由被拉下神坛。
和郦波同为诗词大会导师的蒙曼和康震,都由于解读提出新颖见地不合原句被专家批评,引起网友炮轰。
人红是非多是一回事,技不如人又是一回事;特立独行是一类人,标新创新又是另一种结果。
随着同期两位老师人设崩塌,网友们都纷纭预测剩下的郦波又能苦苦支撑多久。
《中国诗词大会》宣扬片
果不其然,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对郦波提出质疑,一向温文尔雅的他,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整件事情的导火索,是郦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一首诗作《旅夜作书》:永夜永怀难自问,欲笺尺素赏音稀。一身多少江湖事,明月清风弄我衣。
这首诗引起不少人关注,惊叹之声不绝于耳,但逐渐地有人创造端倪,认为郦波抄袭古人诗词,进行修正并二次创作变成自己的诗。
一位自称“民间高手”的网友,认为自己虽然不是是业余的诗词爱好者,但他也能看出郦波的诗抄袭拼凑。
这首《旅夜作书》一共28个字,“有20个字照搬古人,原创度十分低”。
此种辞吐一出,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指出这位网友空口无凭,即便有借鉴古人语句,也不能直接说成抄袭,这是对作者极大的不尊重。
面对这样的质疑,该网友的准备也十分充足,洋洋洒洒一篇文章,总结出原句出处,舆论风向瞬间改变,很多人反叛开始批驳郦波,希望他给出合理解释。
郦波一向比较看重和诗友们进行切磋互换,在十一年写诗的经历中,他真正做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常常会有网友对他的诗重新创作,在他看来都是值得鼓励的行为,这是在鼓吹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乐意研究古诗词。
面对这次风波,郦波一开始也以为只是纯挚的文化互换,但是星星之火尚且燎原,更何况是科技发达的时期,传播迅速,范围无限扩大。
郦波负责地写下关于阐明这次抄袭情形的文章,希望能有效降落这件事情的热度,对所有的回答做出详细解释。
“明月清风弄我衣”,取自阮籍的“余光照我衣”和曹植的“清风飘我衣”,将两人的灵感放在一起,利用到一句诗中。
这样的情形也有很多先例,郦波逐一列举出来,但是并没有起到熄火的浸染,反而越燃越烈。
越来越多的人说郦波冲破他们心中那个“儒雅君子”的形象,垂死挣扎并不能合理解释抄袭的事情。
并且郦波在人设崩塌之后,不是道歉,而是舌战“群众”。
郦波的回应
从《中国诗词大会》开始,郦波谈吐儒雅、风姿翩翩,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学者形象,正如杜公所说“宗之洒脱美少年,皎如玉树临风前”。
不仅会点评还会作诗,让他在一众导师之间显得格外突出。
这些都是网友对付郦波的先前印象,“温文尔雅的诗词鉴赏专家”怎么会如此心急地给出阐明。
他还指出如果按照该网友的理解,那么曹孟德、李白、王昌龄都曾经“抄袭”过古人的诗句。
曹孟德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更是“直接照搬诗经”,但《短歌行》依旧成为千古名篇。
他认为如此行为堪称“十足小人”,中国是诗词大国,主见平等互换相互促进,这样明扬暗贬、挑弄是非的行为都不该被提倡。
郦波的一番回应,被网友认为过于毒辣,并不至此。
这位网友也并不认可郦波的阐明,将在节目中的即兴诗作拿出来说项,那首集句诗的格律利用和意向衔接都有失落专家水准。
郦波当时就作出回应,承认确实有问题,由于是临场发挥的诗作,肯定会有一些难以避免的硬伤。
他将不依不饶的网友比做《逍遥游》中的蜩与学鸠,而自己是鲲鹏,在当时也引起不小的谈论。
因此这位网友提出,郦波写诗从不会标明诗的文体,不指出是五言、五绝还是七言、七绝,这都解释他并不精通古体诗,根本不算是诗词鉴赏专家,愧对他教授的称号。
格律哀求
为此郦波再次在社交平台上发声,写下一首新诗,个中有两句直接表达出自己对付这些行为的不齿:
“庭深刺柏精神在,池浅鼋(yuán)孙怙恶繁。”
刺柏对鼋孙,是郦波忍无可忍的回应。这些回应让网友更加坐不住,进行新一轮的谩骂责怪。
大家都认为他光明正大地骂人,已经失落去文人应有的风姿和斯文。
过于在乎名声与乌鸦争斗,终极只会弄脏珍惜的洁白羽毛。
郦波每一次回应都会带来新一轮谩骂攻击。
成年人的天下和小朋友不一样,小时候可以撒娇耍赖驳回个理,换来一句对不起。
但是成年人的处事规则并不接管这样的处理办法。
被误会时,第一韶光去据理力争,焦急澄清阐明。
但是急于阐明,反而会挑起争端,让氛围更僵。
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利益交手点,更是有不同的生理活动,如若一方得理不饶人,就不会很随意马虎停止。
这也是郦波“抄袭”事宜为什么会酝酿发酵如此剧烈,他一直的阐明,网友一直的质疑。
无法连续阐明就用文学作品进行还击,这一套只适用于同样在文学切磋的人,而不是随意找茬的网友和键盘侠。
大概真的有人在负责磋商学术问题,但肯定有大部分都是见风使舵,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看客们。
他们每每作壁上观,偶尔参与讨伐大军,郦波一个人根本无力回转这样的场合排场,一人何以阻挡千军万马?
而郦波困在文学界诗词中,那种非要寻求一种公正的天下,而忘却社会不是象牙塔,更何况是互联网这个大染缸。
鱼龙殽杂的地方如何哀求每个人都明辨是非,不应该倔强地寻求谁对谁错。
郦波囿于局中,更无法看清事情背后的原形。他的天真在于认为只要阐明就能改变舆论大众的意见。
回归事情本身,很多鞭笞都不合逻辑。从客不雅观角度来看,郦波对付中国古代诗词研究确实做出很大贡献,他的能力是不须要质疑的,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一些诗作原创度的问题。
但是郦波是不是一位合格的诗词研究专家,不应该用写诗水平来衡量。
用一句普通的话来讲便是“吃猪肉的一定要会杀猪吗?”用杀猪水平来判断能不能吃猪肉难道不牵强吗?
郦波是一位汉措辞文学博士后,在学习过程中,他就有“中国古代诗词格律”的专业课程。
一贯到毕业之后,从事干系事情,研究“格律”已经快30年。
根据“一万小时定律”,他就已经成为专家,再打算不可抗拒的成分,天赋缘故原由和个人努力韶光就算不是专家,那也比业余爱好者对格律更加熟习理解。
郦波是国家认可的古代文学方面的专家,这些早在约请他去当《中国诗词大会》导师之前就被节目组评估过,他的学历和从事职业也充分证明他不是名不副实。
更何况,央视非常重视文化类节目的推广和宣扬,因此对付导师的选择是不会放低哀求的,这些都间接证明郦波的实力。
作为诗词研究专家,就一定要成为诗词创作专家吗?这个也没有正规的认证办法,也就无法客不雅观评判他的写诗水平。
提出质疑的那位网友,不是研究格律的专家,也不是墨客,或许他无法对郦波做出一个准确的评判,但是提出质疑未尝不可。
正如阎崇年教授提出的,要与他进行学术互换要符合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是清史专业;
第二,必须在清史研究上有学术专著;
第三,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谈论会的经历。
这三个条件看上去确实门槛过高,但很大一部分能提高互换质量。
毕竟本身不在同一个层次,沟通互换起来会很难,到头来只会平白摧残浪费蹂躏双方韶光。
阎崇年签售会
研究格律的人并不代表能写出好诗,成为好的墨客,就像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一本广受好评的书,离不开一个好编辑的努力,但不是每一个编辑都能写出好书。
蒋方舟考上北大,老师讯问她你来北大是学习什么的,如果是想学习成为一名作家,那很抱歉,北大教不出作家。
从古至今,都没有“教出作家”的观点,大多数作家开设的培训课,都以失落败告终。
创作是灵魂上的共鸣,是一门艺术,不是机器地学习就可以很好地创作,比很多职业都更讲究天赋。
大概日积月累,履历使然,努力可以让你写出令人称道的文章,但和作家比较还是不一样。
因此,郦波身为格律专家,并不代表他一定是诗作大家。
同时根据史实,中国格律形成于中唐,换言之在中唐以前,诗歌创作是不讲究格律的,非要讲究格律,很随意马虎忽略情绪表达。
既然如此在乎传统,那么古人都不严格讲求格律利用,那么今人作古体诗在格律也可以效仿唐人,以诗情表达为主。
关于那首被指摘的《旅夜作书》,一开始认为个中有字句,古人没有写过,被质疑生拉硬拽、强行凑韵。
再到后面创造古人写过,据直接标榜郦波“抄袭”。无论如何在这位和尚的眼中,郦波都有罪。
不管古代还是近当代,很多墨客都会直接引用古人的诗句,他们并没有被责怪“抄袭”,是由于两人表达的思想完备不一样。
比如苏轼借用“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劳为谁甜”;毛主席借用“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果都算抄袭,那么真正的原创墨客又有多少呢?
《旅夜作书》中后两句与宋人黄孝全的“江海一身多少事,月白风清我沾衣”看上去很相似,但表达主旨却完备不同。
郦波表达出自己为俗事所困,但依旧不忘初心,关于是否抄袭,每个人的不雅观点不尽相同。
“世间好措辞,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世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
王安石身为一代文豪,尚且做出如此感叹,更遑论历经千百年来到现在。
凭借机器办法利用当代大数据来鉴定文章是否抄袭,大概这件事情本身就存在一定问题,即便是没有缺点的行为,但也损失本身的创作情绪。
大多数人都认为郦波写诗还击损失文人风骨,但文人风骨是什么?
文人风骨是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不畏强势的气概,是敢于直谏的勇气。
郦波焦急澄清回应是太过爱惜羽毛,但坚持原则正好证明他的傲骨。写诗回应比起那些毫无根据的批评,才是文人该做的事情。
他写诗的水平,身为门外汉的人不多做评价,那些该留着写诗的专家去评判。
他的学历、他的专业这些也不是随便容人质疑的,能做的便是客不雅观看待这件事。
网上看客们无风起浪三尺三,就该像郦波的诗一样平常“他坐在那里,不声不响,不言不语……。于是统统声嘶力竭歇斯底里,都不值一提。”
风骨何在?没有执拗的人谈不上风骨,但有些时候改变不了他人,就去改变自己。
郦波真专家的身份再多的人质疑也不会改变,至于“伪大师”或许是空穴来风。
“不要把真理露出来,他们不配知道;不要争辩一句,他们无心来听。把怜悯给他们,也给被他们弄脏的这个时期。”余秀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