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对仗。古诗除了讲粘,还要讲对。即动词对动词,名词对名词,实词对实词,虚词对虚词。但创造李白的诗有异乎平凡之笔。高下句对应的词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词性,如李白在《古风》一诗中写道:
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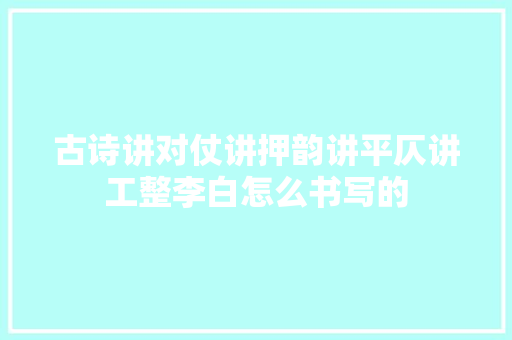
战国名荆榛。
龙虎相啖食,
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
哀怨起骚人。
不必对等。总认为,高下句数相等,彷佛是标配。但在李白的笔下,就有高下句字数不相等,可以是是非句,跟词有点像。当然词也属于诗,是诗的变体。如李白在《远别离》一诗中写道: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
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
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
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
不必偶行。一样平常认为,写诗有上句就有下句,两句成偶。如果两句成行的话,行彷佛也应是偶数。但李白便是李白,不仅浪漫,而且标新创新。如李白在《乌夜啼》一诗中写道:
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
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
停梭痛惜忆远人,独宿空房泪如雨。
只有三行,没了,让你想象去吧。
不必偶句。便是诗句也可以是单数的。你看李白在《乌栖曲》一诗中写道:
苏州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叶欲衔半边日。
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
东方渐高奈乐何!
在句数上,一改偶句收结的常用格式,而变偶为奇,做这种安排,肯定有诗仙的考量和深意,绝不是下一句写不下去了,你说呢?
不必押韵。便是写诗时,一样平常四句中至少要有两句尾字押韵。但在李白的诗中也有意外,如李白在《将进酒》一诗中写道: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
四句尾字确无相同韵角。有人说经由从古到今的变迁,古诗当时是押韵的,不能用当代汉语看待古诗的韵律,既然如此,押不押韵恐怕就没那么主要了。
不必艰深。李白的诗,虽然意境雄伟,变革莫测,缤纷多彩,新奇独到,但措辞朴素,有些并不难懂,如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中,虽说叫诗,但平铺直叙,一看就懂。
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
越人语天姥,云霞闪动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晒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如果这还显得不足,那就看这首措辞直白,朴实易懂,耳熟能详,朗朗上口,老少咸宜的《静夜思》吧。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昂首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实在,越是领袖级的人物,讲话越接地气;越是大师级的人物,文章越讲朴实。就好比,一个好厨师不是依赖名贵食材,而是用普通食材能做出不一般的味道。一篇文章,自己认为好,或少数人认为好,未必好,得到多数人共鸣才是好(当然这与媚俗无关)。一篇文章好就好在写出了别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
厉害吧,诗仙便是诗仙,巨腕便是巨腕,不服弗成,你看是不是完备颠覆了我们的诗界不雅观?
从不拘格式和韵律来看,诗仙李白不仅是古典诗的集大成者,也是当代诗的奠基人和启盟者,为今人写古诗供应了开放性的思维空间。
诗歌离不开小众精英的文化引领,更离不开大众布衣的文化传播,离开了文化传播,古诗的生命就停滞了,就会成为作古的古董而被束之高阁。李白作为唐宋诗歌颠峰时期的俊彦,有浪漫不羁的豪迈,兼具洞悉后世的远见,既信步高坛,把酒言欢,又俯首垂臂,提领大众步入诗坛的阶梯,何其壮哉!
诗歌的上乘佳作当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但现实每每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于是,我们的创作方向该当是形式服从内容,以抒怀表意为主,而不必去钻格式和韵律的“笼子”,更不可本末倒置,堆砌词华,玩笔墨游戏。
任何事情都须要创新,古诗也不例外,也不能成为“八股”式的教条,也要与时俱进,心中有格,而不拘一格,把古诗的“温顺敦厚,哀而不怨”,与当代诗的形式自由,意涵丰富,领悟起来,揉到一块。有的认为,写古诗就要严格按古诗的章法写,不可越雷池半步(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不然,就不要写古诗,写当代诗好了。这里要说的是,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在继续的根本上,没有继续就没有创新,把二者割裂开来是不当的。既然诗仙能把古诗写涌当代诗的味道来,那我们不妨把当代诗的元素钳入古诗的雅趣中,从而走出一条“借壳上市”的新路来,那恐怕又是大众喜闻乐见,一番新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