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作皆署“雅号”,即:“蘅芜君”(宝钗)、“怡红公子”(宝玉)、枕霞故人故友”(湘云)、“潇湘妃子”(黛玉)、“蕉下客”(探春)。
菊花诗十二题分为宝钗的忆菊和画菊;宝玉的访菊和种菊;湘云对菊、供菊和菊影;黛玉的咏菊、问菊和菊梦;探春的簪菊和残菊。
《菊花诗》与《咏白海棠》属同一类型,都在花事吟赏上反响了当时的都城社会习俗和贵族人士的文化生活情趣。
小说中赏桂、赏菊、送海棠以至冬日消寒大嚼鹿肉都写到了。有钱人的各类乐事完备是建筑在财富和地位上,而财富的积攒又大部份来自于房客每年所缴纳的佃租。彼此唱和、斗奇争新的咏物诗风靡一时,正是这种散逸生活的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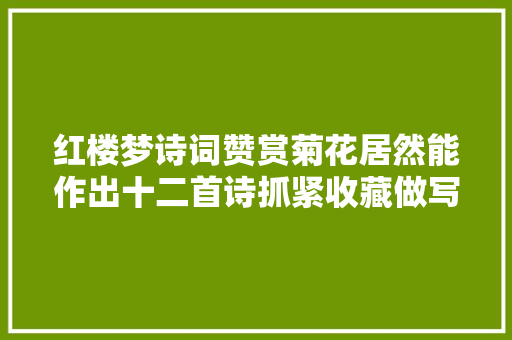
菊诗分咏十二题的形式好象只是宝钗、湘云有时想出来的新鲜玩意儿,实在,也完备是当时现实生活已存在着的一种诗风的艺术概括。与作者同时期人、清宗室、袭封康亲王的爱新觉罗。可见,小说中的情节多有现实生活为依据,并非作者向壁虚构。
和同类内容的大多数诗一样,《菊花诗》寄情寓兴的一壁还是值得把稳的。每首诗依然有选咏者各自的特点:比如薛宝钗的“忆菊”就一味地是寡妇腔;贾宝玉的“种菊”就归结为绝尘离世;史湘云的命运从她的“册子”上看,后来虽一度“来新梦”,但究竟“梦也空”,未能“淹留”于“东风桃李”的美满生活;林黛玉的诗中“孤标傲世”、“幽怨”等等,则更说得明白。
从“残菊”诗看探春,可之她“运偏消”时如菊之“倾欹”、“离披”,情状也大不如前,“万里寒云”、“分离”而去正是她远嫁不归的象征,所谓明岁再见、切莫相思等慰语,其用意也不过犹如元春离去时所说的“见面尽随意马虎,何必过悲?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不可如此奢华糜费了”那番话罢了。
林黛玉所写的三首诗被评为最佳。如果作者只是为了表现她的诗才出众,为什么在前面咏白海棠时要让湘云“压倒群芳”,在后面讽和螃蟹咏时却又称宝钗之作为“绝唱”呢?
原来作者还让所咏之物的“品质”去暗合吟咏它的人物。咏物抒怀,恐怕没有谁能比黛玉的出生和气质更与菊相适宜的了,她比别人能更充分、更真实、更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完备合乎情理的。
黛玉三首诗中“咏菊”又列为第一。由于小说中众人的议论,随意马虎使我们以为这首诗之好就好在“口角噙喷鼻香对月吟”一句上。实在,诗的后半首写得更自然,更有传染力。“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
我们从林黛玉的诗中又听到了曹雪芹的心声,它难道不便是作者题于小说开头的那首“缘起诗”在详细情节中所激起的回响吗?这实在比让林黛玉魁夺菊花诗这件事本身更能解释作者对人物的方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