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向主见稳健、渐变的政治方针,因此与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在政见上多有不合。宋神宗赏识苏轼的才能,由于政见不合,苏轼再三批评新法,这对新党来说不啻为一个不小的威胁。神宗天子逐渐心生不满,朝中小人便见缝插针,诬告苏轼兄弟在居丧期间利用官船贩卖私盐、木材等,虽然末了查无实据,不明晰之。感想熏染到威胁的苏轼为求自保,随即要求外任,以离开政治斗争漩涡。
元丰二年(1079)七月,朝廷的新贵们从苏轼的诗歌和奏章中寻章摘句,罗织莫须有的“包藏祸心”、“指斥乘舆”、“谤讪先帝”等罪名,哀求天子将苏轼处以“大诛”之罪。苏轼被押至御史台,经由两个月的严刑逼供,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终极“罪名”成立,只等天子讯断。御史台又称乌台,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经由多方营救,“乌台诗案”以苏轼免除去世罪、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停止,事实上,苏轼仍被作为犯人,被监管在黄州。在黄州,在好友马梦得的帮助下,苏轼成功申请了城东荒地,他亲手垦殖,并以此地自号“东坡”。
“乌台诗案”对苏轼产生沉痛打击,虽然他还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但他在思想上几次三番“疑惑人生”。对付词的创作,无论是题材还是意境风格都表现出“以诗为词”的特色,逐渐形成“无意不可入”的境界,透露出一种寻求解脱的精神追求,他寄情山水,在对大自然的感悟中淡化和超越人生的苦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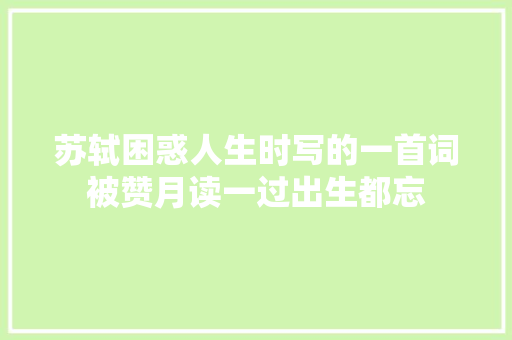
这首《满庭芳》词的详细创作韶光难以确证,但从词中表现的内容和抒发的感情看,该当是苏轼受到重大挫折后,大致可断为写于黄州期间,也有人认为作于元丰五年(1084),也有人认为作于元丰七年(1086)。
满庭芳
蜗角浮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斟酌,能几许?忧闷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去世,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经历人间浮沉的苏轼开头一句“蜗角浮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以唾弃的眼力戳穿追逐名利的虚幻,既是对世俗不雅观念的奚落,也是对人生的困惑和疑惑。紧接着“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名利得失落皆有分缘,但是,胜利者未必是强者,落败者也未必是弱者,万事皆需看开,无需在意那么多。
《老子》云“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倔强者莫之能胜”,那么“谁弱又谁强”呢?想必此时的苏轼,思想上佛老的“清净无为、超然世外”霸占上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不争则无忧,因此便有了“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怎么个疏狂呢?词人豪迈发言“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纵然人生不过百年光阴,我也愿大醉三万六千场,把稳“浑”字用的相称精妙,表示出以沉醉不问世事以阔别祸患的痛楚和悲愤。
下片“斟酌,能几许?忧闷风雨,一半相妨。”承接上文“百年里”,沉思算来,生平百年中,要有一半日子被忧闷风雨滋扰。经历笔墨狱,词人万念俱灰,“又何须抵去世,说短论长。”是经历苦难之后的彻悟,彷佛彻悟,又彷佛我们平日发牢骚,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何必一天到晚说短说长?
“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既然世事难料人生不易,那就忘怀世俗统统烦恼,面对清风皓月,把青苔为褥席铺展,把白云当帐幕高张,末了“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展示了作者人生道路上受到重大挫折之后洒脱旷达的内心转变。
这首词上片由讽世到愤世,下片从自叹到自适,表现了词人宠辱皆忘、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全词以议论为主,夹以抒怀,情理交融,肆意不羁,颇受惊叹。明代李攀龙《新刻题评名贤词话草堂诗余》评价“细嚼此词而绎其义,自然胸次广大,识见高明,居易俟命,而不役于蜗名蝇利间矣。”明代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评正》曾评价“月读一过,出生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