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汉乐府诗中的一首相和歌。这是一首歌唱江南劳动人民采莲时愉快情景的民歌。
相和歌是汉代期间在“街陌谣讴”根本上继续先秦秦声、赵声、齐声、郑声、楚声等传统音调而形成的。相和歌也是极具汉族代表性的传统舞蹈之一。紧张在官宦殷商宴饮、娱乐等场合演奏,也用于宫廷的元旦朝会与宴饮、祀神乃至传统民俗活动等场合。“相和歌”之名最早记载见于《晋书‧乐志》:“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其特点是歌者自击节鼓与伴奏的管弦乐器相应和,并由此而得名。
《江南》是产生于汉代的一首采莲歌。关于此诗的创作背景,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一首情歌,“鱼戏莲叶”有暗喻男女欢爱的意思;也有人说这仅仅是写劳动生活的快乐。
这首采莲曲通过对莲叶和鱼儿的描述,将它们的欢快之情充分透露了出来。诗的前三句是主体,后四句只是敷演第三句“鱼戏莲叶间”,起到渲染、陪衬的浸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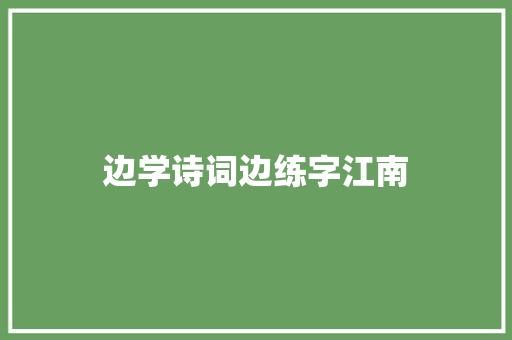
主体部分的三句,描述江南采莲风光,实际着重于表现采莲人的快乐。开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首先把读者引入一个碧叶光辉光耀、小舟穿行的画面。“何田田”流露出感叹、赞颂的语气,本身是带有感情的。虽然没有写人,人已在个中。如此良辰美景,旖旎风光,采莲的人们自然免不了一场嬉闹。何况,采莲的活儿,习气上总是由年轻的女孩子干的,她们平日拘束得紧,如今似鸟出笼,更兼结伴成群,欣喜活泼,自是如水荡漾。然而诗在这里逗了一逗,却不再写下去,转笔落到“鱼戏莲叶间”。开头两句之后,本该有人的“戏”,作者却将它转嫁为鱼的“戏”。这便是移情的表现。但虽是写鱼,“戏”的感情却是从上二句流贯而来的。采莲人的情趣清闲个中。不过,这里也并不是比喻、象征的手腕,“鱼戏”也是实景,是一个完全画面中的一部分。采莲人本是快乐的,看到成群的鱼儿倏忽往来,潜沉浮跃,彷佛自己也同鱼一样,轻松活泼,自由清闲,无挂无碍。
至此,诗意本已完足。后四句只是将“鱼戏莲叶间”逐一铺展为鱼戏莲叶之东、西、南、北。然而缺此四句,全诗即枯燥乏味。由于诗的功效,紧张在于给读者以美的冲动。而“鱼戏莲叶间”一句,阐述的意味重于描写,又是孤零零一句,实在无法造成足以冲动读者的浓郁气氛,必待于后四句的铺排渲染。这四句诗稚拙而又神奇。第一,它就这么简大略单地东、西、南、北一起写下来,却让读者彷佛眼见到一群鱼儿倏忽往来、轻灵巧泼的样子。第二,这种大略的重复,造成了明快的节奏感。因此诗的形象、感情,不仅通过措辞的意义浸染呈现出来,而且在措辞的节奏中流泻出来。第三,一个大略而完全的旋律,经由歌唱、诵咏,会在人的觉得中形成自我重复,长久地萦回不息。以是,有了这四句,鱼群,也是采莲人的活泼轻快,才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墨客把采莲人的快乐转化为“鱼乐”的时候,这种快乐就分开了详细的背景和缘故原由,成为一种纯挚的、空灵的感情,达到浑然忘我的境界。作品本身并没有正面描写过一个人物,但从字里行间以及描述的特定环境,都能引发读者的遐想,也可窥见歌者的心态。这种含而不露的艺术手腕,非常耐人寻味。
这首诗在乐府分类中属《相和歌辞》,“相和歌”本是两人唱和,或一个唱、众人和的歌曲,故“鱼戏莲叶东”四句,可能为和声。故此诗的前两句可能为男歌者领唱;第三句为众男女合唱;后四句当是男女的分组和唱。如此,则采莲时的情景,更加活泼有趣,因而也更能领会到此歌表现手腕的高妙。诗中“东”“西”“南”“北”并列,极易流于呆板,但此歌如此铺排,却显得文情恣肆,极为生动,从而充分表示了歌曲反复咏唱,余味无穷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