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有非常大的情绪涵容力。不管你有多么糟的感情,打开一本中国诗歌集,总能在里面找到对应的诗歌。
当你看到这些经典诗歌的时候,你不仅看到了个中幽约怨悱的部分,还看到了精美绝伦的部分。这两种感想熏染是同时涌现的,以是你悲哀的情绪在一瞬间就被整理成了一个具象且故意义的审美形式,这种审美形式本身就可以带给我们愉悦和代价感。以是,在阅读诗歌的过程中,我们原来那些悲哀的情绪不仅得到了理解,得到了抚慰,还得到了转化,变成了一种更高等的东西。
举个例子。我家在无锡,这里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鼋头渚,是不雅观赏太湖最好的地方。我小时候每年秋游都去鼋头渚。如果去公园看小朋友排着队秋游,每每会看到里面有兴趣勃勃、打打闹闹的小朋友,有捉住统统机会和老师说话的小朋友,还有垂头丧气、松松垮垮背着书包、落在末了的小朋友——我小时候便是这种小朋友。我不是很长于运动,跟小朋友“疯”不起来,而秋游的时候,如果不能跟小朋友“疯”起来的话,实在没有多大的意思,会有一种失落落的觉得。
有一次秋游,不才午自由活动韶光,我非常无聊,以为被老师忽略了。坐在湖边等凑集,要坐一个小时。可是我坐着坐着就看到了在天的尽头,在太湖的水和天交卸之处的小岛,然后就想到了一首刚看过的宋词。这首词是姜夔的:“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薄暮雨。”(《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我当时并不知道这首词详细讲的是什么意思,觉得它便是在讲一个人寂寞离群、不知道何去何从、统统东西都跟他隔着一定的间隔、什么都看似触手可得又什么都触不到。在这首词里,作者一个人在太湖边发呆,燕子和大雁来了又去,薄暮的雨也来了又去,自然界按部就班地运行,自己却彷佛被落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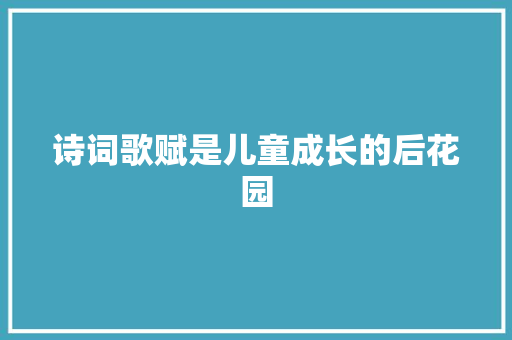
我在湖边,开始的时候怏怏不乐,以为全体天下都欠了我的。可是当把我的处境和这首词联系起来,以为自己彷佛便是词中的这个人,面对的便是词中这个场景的时候,那种孤独无聊的觉得忽然间变成了其余一种东西——变成得意其乐,就彷佛是“哇,这个天下上有这样的美,可是你们这些傻小孩光会打打闹闹,都没有看到”。这种觉得,就彷佛我在秘密花园中挖到了一颗宝石。于是等到凑集时,我也就快快乐乐地回家了。这个秋游我也很有收成,虽然收成的点可能和其他孩子不一样。
这便是诗歌对付人的情绪的涵容和转换。如果我们不把诗词歌赋当作必须学习的包袱、当成炫耀自己有文化的符号,而是把它视为一种资源,把古人视为一些心腹;当我们自己的情绪不被他人理解,或者说也说不清时,就到这些诗词歌赋里去找一找共鸣,让诗歌细腻的情绪来谅解它,用诗歌精美的形式来转化它,我们大概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发展。对我自己来说,我终年夜之后读中文系,一贯和这些诗歌在一起,可能是由于它们比较随意马虎走进我的内心。
有很多次,我都回顾起小时候一个人躺在窗前的床上读《唐宋名家词选》的场景:窗外是满天的晚霞,我读一下子就有一群鸟从晚霞中飞过,读一下子又有一群鸟从晚霞中飞过。自然、诗歌和我三者就构成了一个无比美好的天下,所有的烦恼、忽略或不理解都被抛到了脑后。真幸运能有这样一个秘密花园,能够消化我在发展的过程中碰着的各类压力。
以是,从现在开始,不妨给你的孩子买一本精美的诗集,给他一些韶光,让他去找自己最喜好的那些诗词歌赋,开始建造自己的秘密花园。
须要提醒的一点是,那是孩子自己的天下,爸爸妈妈只要做好守门人,孩子不约请你时,不要随便探头探脑。
(作者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本文摘自《陶渊明也烦恼:给家长的传统文化启蒙课》,有编削)
《中国教诲报》2022年04月06日第9版
作者:黄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