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文明而言,诗是最早的历史,也是最早的艺术。我们的民族当然也大体如此。众所皆知,《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然而未必有更多的人知道 ,它也是一部用于占筮的古诗杂汇,比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还要早五六个世纪。
而《易经》的卦爻辞,当中就有韵文的特色。有学者认为这是先民的古歌,被《易经》的作者援引利用。由于有反复被后人再次加工的过程,以是不易看出这些古诗的原貌来。
那么,《易经》与中国古诗歌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它里面又蕴含着哪些诗歌元素呢?本期“另眼看易经”,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易经》与诗歌的奇妙联系吧!
一、《易经》中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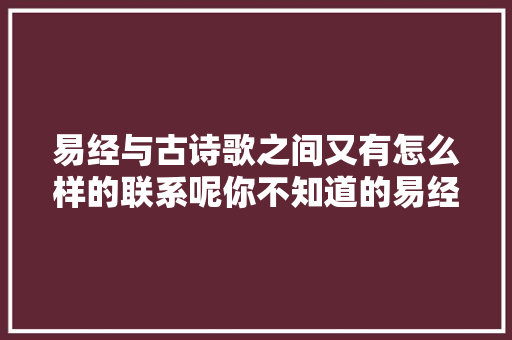
关于《易经》中的诗,古人世有涉及。在近当代,逐渐引起一些易学者的高度重视。例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易学家李镜池的《易经筮辞考》、高亨教授的《易经杂论》等论著中均有所抉发。还有现今四川大学黄玉顺教授的《易经古歌考释》,他认为《易经》六十四卦无不征引古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绝大部分都有古歌。
由此可以说,《易经》不但是中华儒、道等传统文化之元典,同时也是中华诗歌之来源。
研究这些颇带“原生态”意味的古诗“新宇区”,也容许以从中发掘出源远流长的中华诗词的“遗传基因”。
二、易象与易诗
研究易诗,自然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易经》与诗会有什么关联呢?《系辞传》上说:“贤人立象尽意”,“夫象,贤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同时更详细地指明“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于此可见,《易经》是离不开象(即形象)和喻(即相像)的,以象喻理,正是《易经》的基本特点。
而我们知道,诗歌也正好是借助形象思维才能插上它的艺术翅膀的,这就与 《易经》的哀求颇相吻合。并且,由于诗歌笔墨简短,形象生动,富有韵律美和节奏感,因此便于筮人诵读、影象、利用和传播。从此《易经》也就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正如闻一多师长西席所言:“《易》有《诗》的效果,《诗》亦有《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每每不能分别。”
其余,据高亨师长西席的研究,因《易经》的卦爻辞“大抵为简短之韵语,有似歌谣”,故《左传》、《国语》在引用时都称之为“繇(yáo)”,借为歌谣的谣(爻与谣亦读音相谐)。这从笔墨训诂学上也证明了《易经》与诗的自然关联。
《易经》与诗虽然都看重形象思维,但是两者却又有明显的差异。对付这个问题,钱钟书师长西席曾剖析指出:“按《系辞》上:‘贤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故谓之象。’是‘象’也者,大似维果所谓以想像体示观点。盖与诗歌之托物寓旨,理有相通。”
以是,《易经》只不过将诗作为彰明易理的手段而已。但由此却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前《诗经》”,虽然是比较零散和片断的,但这无疑是它另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三、《易经》中的诗大致分为四种
第一类:比兴体诗歌
震·彖辞:“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荡百里,不丧匕鬯。”虩、哑,入声铎部,鬯,阳声阳部,阳入对转通押。
大过·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稊、妻,阴声支部。大过·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华、夫,阴声鱼部。
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左)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翼、食,入声职部。
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和、靡,阴声歌部。
以上四首诗是属于比兴体的诗歌。第一首以雷鸣笑言喻处变不惊,第二首以老树萌芽着花喻老夫少妻和老妇少夫。
值得把稳的是,第三、第四首,其风格已很靠近《诗经》,如与《邶风·雄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等诗相较已难分轩轾。
这是什么缘故原由呢?这就要从两部诗集的成书年代提及。
据学界多数学者的考定,《易经》约成书于西周的初期,即公元前11世纪的中叶。又由于《易经》是对夏、殷连山、归藏二易的摈弃,自然接管了二易的一些卦爻辞,也包括周族先人遗存的一些占筮记录,其上限自当在千年以上。《诗经》的成书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晚于易诗500—600年,其采诗的上限约在殷末周初。
故从韶光跨度上看,显然易诗比《诗经》更为久远、更为古老。但是两诗所收录的年代也有一段重叠交叉,即殷末至西周初期或中在即百年旁边的韶光,因此个中有部份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比较靠近就绝不奇怪了。
第二类:赋体诗歌
丰·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屋、觌,入声屋部,家、户,阴声鱼部。阴入对转通押。
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实、血,入声质部。
睽·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孤、涂、车、弧,阴声鱼部,寇、媾,阴声侯部,邻韵通押。
井·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食、恻、汲、福,入声职部。
第二类诗是属于赋体诗歌。
第一首,大意说高大丰实的房屋却空寂无人,主人已经三年未归。有的释为贩子,“贩子重利轻离去”,爻辞故以“凶”戒之。
第二首,说女方捧着的筐里是空的,男方宰杀的羊也没有带血,是不正常的,故爻辞引以作“无攸利”的占断。这是有关婚礼习俗的风诗。
第三首,有释为夏少康复国过程中一次经历,说在途中开始瞥见一头涂满泥浆的猪,其后又看到一辆车上满载着打扮得像鬼一样的人,本打算开弓射去,随即放下了弓箭,原来是来求婚的。这是用赋法写的一首雅诗。
第四首,说本邑的水井虽然得到疏通却不让饮用。英明的国君第为我们排忧解难,才使大家享受到幸福。这是一首歌颂王侯年夜德的颂诗。
从以上第一和第二两类诗来看,我国传统诗歌风、雅、颂三种写作手腕在《易经》的诗中也都有了。
第三类:谚语、鄙谚微型诗歌
否·九五:“其亡!
其亡!
系于苞桑。”亡、桑,阳声阳部。
中孚·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望、亡,阳声阳部。
第三类为谚语、鄙谚,是句句用韵的短诗,也可谓古代的微型诗。第一、二首大约都是农事谚语,意谓将畜生拴在柔弱的桑树上,或在望月之夜,告诫人们都有亡失落的危险。
第四类:重叠吟诵的组诗
渐卦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衍衍’吉。”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干、磐、衎,阳声元部;陆、复、育,入声觉部;木、桷,入声屋部;陵、孕、胜,阳声蒸部;阿、仪,歌部。
蛊卦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蛊、誉,阴声鱼部;侯、事,分属阴声侯部和之部通押。
第四类是重叠吟诵的组诗。第一首每段都以“鸿渐于”三字作段首,递次换韵,形成渐进式。
第二首前三段以“干(继续)父之蛊(奇迹)”作为段首,末段以句式的溘然变革,凸显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道德情操,至为高妙。
这种反复吟咏、一唱三叹、层层递进、能产生强烈的艺术传染力的组诗形式,在《易经》的卦爻辞中比较多。
在《诗经》中更为普遍。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歌坛亦是常见的的一种咏唱办法,而它却源于三千多年前的易诗,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四、读易诗,话传统
如果单从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来看,根据以上的粗略剖析,《易经》古歌至今给我们留传下来一些什么值得我们很好研究和继续的诗歌传统呢?初步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
1、诗歌表现手腕的比兴传统。我国诗歌最早源于触物起情的兴,而后有借物喻情的比,直陈其事的赋(赋中亦有比兴)。据《兴的源起》一书作者赵沛霖师长西席指出:“就现存的古代文献来看,作为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的兴,最早见于《易经》。”“可以说,兴的涌现是诗歌艺术的巨大飞跃。”
从前节所例举的《易经》的诗中,比拟兴的利用就很普遍、很生动。由此可见,比兴作为形象思维对我国诗歌产生、发展和民族性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有韵而无比兴是不能成其为诗的,如钱钟书师长西席所言,只能叫“押韵的文件” 。
2、诗歌音韵的合辙叶韵传统。上古期间并没有什么韵书,但在《易经》的大多数卦爻辞中,撤除叙辞和占断辞外,险些都可入韵,虽然押韵的韵部较宽,也不大规则。
这当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客不雅观哀求,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紧张是动听、易颂、易记、易于流传。几千年来韵律由宽而严,又由严而宽,终不可废。
3、诗歌音调的高(平)低(仄)音相间传统。从前面所举诗例中就可以看出,这种短练、均齐、具有光鲜节奏感和韵律感的句子,在易诗中为数很多。
对《易经》经文作过大要统计,在约384条四字句里,个中作为音节的第二、四句两个字高低音交替的句子共204句,约占总句数的52%,这是使诗歌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感的必要语音构造。
《文心雕龙·声律》指出:音律本于人声,言语乃文章关键,必须合于“声有飞沉”、“异音相从”和“同声相应”的音律。
《易经》的诗虽未尽合,然已有肇端之功。后来在此根本上逐步创造四声,才自觉地按照“声有飞沉”(平仄)的规律写诗属文。这在先秦以来盛行至今的许多针言里,更加看重前后音节的相互转换。
4、诗歌发展源流的民歌传统。中国历代的诗、词、曲大都起源于民歌。在《易经》的诗中,紧张属于民歌的风诗就占了多数,《诗经》亦如是。
楚辞也多源于江淮流域的歌谣,民歌的句式、用韵、表现手腕(比兴、夸年夜、谐音、章段重叠等),常为历代诗词创作者所沿用。
由此可以看出,民歌在中华诗歌王国中的主体地位。
研究《易经》的诗,初步发掘以上四点有关我国诗学千古不易的古老传统,可以说它已构成中原文化的遗传基因而溶入我们的血液之中了。纵然在“环球化”与时俱进、东西文化相互碰撞和领悟的情形下,大概也不能动摇它的稳固性。
《易经》中的诗歌元素,对付研究我国的诗歌发展史,稽核其相对稳定的要素,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具有主要的认识意义。
那么,这就无怪当今的一些新墨客,也在从西方的引介到寻回自己人文传统的努力中,正积极钻营当代诗在中国的“存在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