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今诗词,凡写游山的,多为登高。
有的是写登山途中的,比如这一首:“横算作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孔,只缘身在此山中。”再比如另一阕:“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仲春花。”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山,在那白云深处,居然还有人家。停下车来,是由于喜好这深秋枫林晚景,那经霜的枫叶,比仲春的春花还要鲜红,这样的情景真美啊!
登巅之后的景致,则更是壮阔。杜甫有《望岳》:“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王之涣登上鹳雀楼后,不禁心潮澎湃:“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还可以列出许多这样的登山感怀,比较之下,下山之作,分明是显得少之又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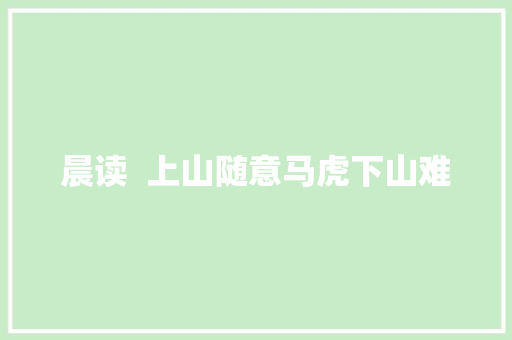
可是,有上必有下,何以下山就不受待见,少被追捧呢?幸好,解铃尚有豁达人,宋代大家杨万里的文笔甚为独到:“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谬爱好。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
原来,不写下山,并非由于上山更具寻衅性,更能激扬笔墨,而是由于下山更难——大概难在过了一山又一山,而大概,下山,总归只是一种回归原点的过程,激情过后,难以免去的,便是换了一副欲说还休的心态——
繁华阅尽多凉薄,落寞吟来甚生僻,宛如彷佛那上山随意马虎下山难。(燃烧的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