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梅江镇迪塘钱村落的乡间小道上,闭眼凝神,我想用自己的鼻子找到唐敦航。他是位酿酒师傅,本日在迪塘钱村落酿酒。
喷鼻香气自东北方向飘来。向前,走过一个路亭,三锅高粱正在露天空地上,接管末了一道催酒工序,梅江烧即将出世。唐敦航像个将军,校阅阅兵着烧着三锅高粱的不锈钢灶的柴木和热度。
“你岳父兼师父让我们来找你的。”我们解释来意,45岁的唐敦航腼腆地笑了笑。若他不笑时,我以为他的气韵酷似功夫明星李小龙,国字脸,方方正正,还留着蘑菇头。
他们一家与酒、与梅江烧有很长的故事,待我们逐步说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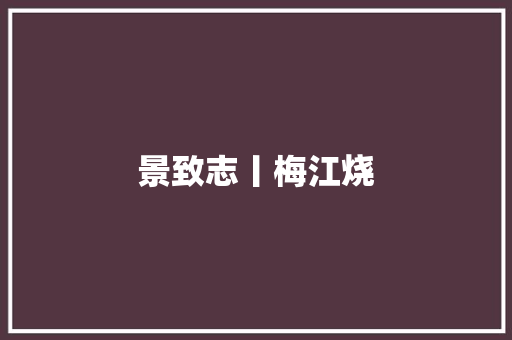
不知其所起
纵然74岁的倪来根——唐敦航的岳父兼师父,这位酿了一辈子酒的老人,也不知梅江烧发起于哪年,梅江镇又是何时开始种高梁的。“上辈人都不讲究起源的,便是代代相传,一贯都这样。”倪师傅说。
梅江烧,顾名思义,梅江人的烧酒。它常日有麦烧、谷烧、米烧、番薯烧、砻糠烧、荞麦烧等多个品种。但在梅江人眼里,纵然是罕有、价高又有保健浸染的荞麦烧也算不得好酒,唯有纯高粱烧才正宗。因此,梅江烧实际上多指梅江高粱烧。
梅江地处兰溪东北部,原属于浦江县域。因历史沿革,自1958年才并入兰溪市。如中国的北方人刚毅豪迈的性情一样,梅江亦是如此。且与兰溪的平原多、适宜水稻栽种不同,梅江山多地少,适宜栽种高粱、玉米等作物。山区气温偏低,酒成了不可少的御寒圣品。
梅江人自己估摸着,梅江烧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这从他们自己栽种的名叫“乌壳糯”的土高粱品种中,可窥见一斑。只管后来政府从四川泸州引进推广了“泸糯8号”,但他们依然以为还是自己的土高粱品种好。
梅江烧的起源,不仅对梅江人是个谜。追溯高粱酿酒的历史,海内许多白酒专家一时也难以破解。大量史料和考古发掘证明,我国白酒起源于金、元期间。而白酒中的佳构高粱酒约涌如今明代。起源地可能在黄河中下贱地区。因当年黄河水泛滥,朝廷命令广种高粱,以高粱秸杆扎成排架添补石灰土加固河堤,高粱籽除部分民食或用作牲口饲料外,还有了大量盈余。因此,高粱白酒应运而生。
倪师傅不知道这些事。陪着雇主,尝了口新出的酒,他怠倦的脸上露出了笑颜。
一往而情深
小雪前两天,我找到了倪师傅。74岁、55年的酿酒史,让他的名望在梅江达到了高峰。那天,他正在他的半子唐敦航的老家唐店村落酿酒。半子在外酿酒的活儿忙不过来,只好把乡里乡亲的事拜托给老丈人了。
“高粱是一茬一茬的,人也是。”那天温度已达23℃,酿酒的不锈钢灶就放在太阳底下,倪师傅依然带着厚厚的鸭舌帽,身上的毛衣没有脱过。他说,他得服老了,如当年他的老丈人一样。
8岁订亲,18岁娶妻,19岁酿酒,而后生养一子三女,到如今依然劳碌在各个村落酿着酒。倪师傅话不多,沉静如未开封的梅江烧,刚烈的性子得经由一番品尝。
“我一辈子都在酿酒。本来,这手艺是传男不传女的。”倪师傅打开了话匣。老丈人是横溪镇胡宅人,那也是后来行政区划的结果,按老梅江人的不雅观念,那还是梅江。老丈人与老父亲是故交好友。倪师傅8岁时,双方父母赞许,把10岁的大女儿胡荷英许配给倪来根,那年新中国还未成立。
19岁时,老丈人病重,两位小舅子还小。出于对手艺的尊重,以及对儿女的疼爱,老丈人冲破常规,把倪师傅叫到身边,手把手地教会了他酿酒手艺,并把制酒娘的配方交给了他。
凭着这手艺,倪师傅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造了新居,养了孩子。而他也不负老丈人的请托,扶持两位小舅子发展,待其成人,教会他们酿酒手艺。
有时,命运总会惊人的相似。唐敦航险些重复了岳父的故事。爱酒,好梅江烧,两人家在邻村落,是岳父看着终年夜的。娶了酿酒师的女儿,学会了酿酒的手艺,传承着梅江烧的手艺,其妻子都长其两岁。彷佛是梅江烧在串联着他们的人生。
时期终是在进步的。从老丈人手中接过的酒娘秘方,已经不知被倪师傅修正了多少回。他用手比了个七八厘米厚的高度,说他试过这么多。高粱烧的关键在酒娘秘方,每个师傅都有自己的独门窍门。酒娘决定着出酒率和酒的品质。“我老丈人给我的方子,只用了五六味中药,每斤高粱的出酒率只有三两、四两,我现在能够达到五两、六两,中药也加到了30多味。”倪师傅说。
这药方现在是两家共享的。倪师傅的儿子嫌酿酒赢利不易,便从事了装修行业。而半子唐敦航已酿酒25年,从娶了倪家女儿的那天起,继续了丈人的手艺。妻子代父授艺,成了名符实在的师姐。
我问唐师傅,是爱酒才娶了倪家女,还是爱倪家女而酿酒?唐师傅起初笑而不语,末了说了句:“都一样。”
高粱烧代表着妻子,妻子代表着高粱烧。对付唐师傅,可能真的一样。
醉在梅江里
这一季去梅江,若是不擅饮的人,得要做好被熏醉的准备。全镇5600多亩的高粱栽种面积,险些家家户户种高粱酿梅江烧。
在唐店村落,倪师傅给唐福禄和唐国成酿酒。酿酒用的不锈钢灶就停在唐福禄新造的三层小洋楼前。唐店算是梅江的高山村落了,唐福禄的屋子建在一个山头上。
屋子面南,倪师傅一锅40斤的高粱,一样平常半个小时出酒,从滴滴答的精华酒,到小溪流般的哗哗出酒,到后来滴滴答的差酒,又约半小时。倪师傅就这么站着,看灶,看高粱温度,或加水冷却,或加柴升温,一刻一直。他得从清晨7时,站到晚上6时。一天烧出四五百斤高粱,约两三百斤梅江烧。
那天,天好蓝,万里无云。最为精华的梅江烧,一滴出来,雇主唐福禄就叮嘱倪师傅给我尝尝。年少不更事呀,我真尝了!
那可是60度,乃至是70度的酒呀。滴在碗里的它,温温的。端碗入口,喷鼻香气扑鼻,直冲后脑勺;尝一口,温而纯,倒不像普通白酒的刚烈。后果是,我一下午都晕乎乎的。
唐福禄高兴着呢!
小雪将至,北方开始封冻。他在西藏从事装修装潢的儿女们,恰好回来。掐着儿女们回来的日子,他专门向打工的农场请了假,请来倪师傅酿酒。他准备用今年的第一口梅江烧欢迎着他的儿女。
唐国成也乐着。他家的新居已经结顶,眼下已进入装修阶段。在义乌打工多年的妻子,今年专门在家建房,并在劳碌中种了200斤的高粱。多年没喝上自家梅江烧的唐国成,就等着新酒宴宾朋了。“年前如果能够落成,燕徙仪式,这100多斤梅江烧估计还不足呢!
”唐国成笑着说。
有了唐敦航的唐店村落,还是内敛的。一年栽种、烧制200担,即两万斤高粱的唐敦航家的酒,可以无限量供应他们。与之比较,迪塘钱村落更猖獗。唐师傅给了张酒单,那是他这一回要在迪塘钱村落烧酒的人家。
单子上仅36户人家,这回须要酿的高粱有14000斤,估计能得梅江烧7000斤至8000斤旁边。唐师傅带着三个不锈钢灶,三口锅一起烧,也要烧上10天。而他碰着的更猖獗的是石埠村落,这村落他一进去就得一个月才能“脱身”。
站在唐福禄家门口,俯瞰着梅江大地,大自然一派恢宏气候。一个个山头,如连绵起伏的海波,浮游而去。夕阳西下,碧波山头泛着黄晕,温暖而安谧。我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