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掬水月在手》以独特的影像质感展现出叶嘉莹师长西席提出的“弱德之美”的内涵。王国维有言:天以百凶造诣一词人。“一世多艰,寸心如水”是叶嘉莹《踏莎行》的开篇之句,也可以视为其生平的写照。叶嘉莹生于1924年直奉军阀混战期间,生平历经抗日战役、国共内战、台湾白色胆怯、外洋飘零,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回到改革开放的中国。1993年,叶嘉莹从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出发,提出了“弱德之美”这一词之美感特质。“弱德之美”也来自于叶嘉莹自身的生命体认,她说:“我的生平不是很顺利,有很多坎坷。我有弱德之美,但是我不是一个弱者。”古典诗词是叶嘉莹的精神寓所,君子之淡然来也自于古典诗词之力量。正是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才有了“掬水月在手,弄花喷鼻香满衣”之境界。“弱德之美”不仅是对古典词体美感特质的描述,更具含着中国人,特殊是中国文人在面对强大外势压力,所采纳的隐曲之姿态的处事办法,是中国传统文化授予中国人独具魅力的精神天下。
《掬水月在手》追求影像化诗词的极致境界,长于化用自然之意态,以影像措辞表达出了悠远之诗意。影片有着细致而深入的内容纹理,影像化地描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形态,影像语汇追求精细与纯粹,极富审美魅力,这也是导演陈传兴在创作过程中积极选择表达方向的结果。《掬水月在手》供应了影像以勾勒万物,再链接诗词意涵的可能,这样的艺术创新实验比较较陈传兴之前的文学大师电影《如雾起时》《化成再来人》等走得更远。《掬水月在手》的构造富于巧思,章节按平生顺序与大门——脉房——内院——庭院——西厢房的建筑构造进行排列,缺失落的标题VI暗含着叶家北京四合院的消逝,也象征着叶嘉莹经历父逝和丧女之后,放下个人情绪,延续诗词薪火。陈传兴重视古典意象的传达,将其灵动而真切地缝合进了每首诗之中。不过,略微空泛的物象也给很多普通不雅观众带来了强烈的疏离感。
《掬水月在手》中吟诵的音律之美与意境构筑形成互文。叶嘉莹归国结缘南开大学,一贯积极推广吟诵诗教,对中国传统古典诗词推动遍及的功劳不可没。在影片中,叶嘉莹吟诵了《秋兴八首》《咏莲》《哭母诗八首》等,她说,“我留下的这一点海上的遗音,大概将来有一个人会听到、会冲动。便是现在的人都不接管,也没紧要,反正我是留下来了”。吟诵始自先秦,口传心授,生生不息,被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活态”,也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文化审美。“海上之遗音”延绵不断,承载着民族固有的美和先人的气息,影片让不雅观众临其境般地感想熏染到了古诗词文音律之美。《掬水月在手》有着丰富的音乐元素。音乐丰富了影片诗化质感,确立了总体基调,也成为主要的叙事构造元素。日本音乐家佐藤聪明以《秋兴八首》为本,创作电影音乐《秋兴八首》,八首音乐总长34分56秒,以筚篥、笙、二十弦琴雅乐传统乐器演奏,缓慢、低沉而带着幽美与宁静,化繁为简,声影合一。电影音乐与影像浑圆交织,又超越具象表达,延伸至深邃辽远的时空。
《掬水月在手》是一个人的心灵史诗,以影像完成了以叶嘉莹为象征的一代中国文人最贴近、最直不雅观的形象重修。《掬水月在手》探索了个人心灵史的影像构造,最难堪得的是,让我们第一次能够把目光放到了日常环境中的叶嘉莹身上,气息生动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迎面而来。个体的存在正好通过细微的日常体验来呈现的,诸多细腻的镜头敏感地捕捉了叶嘉莹的生命瞬间和生活情态,这个中隐匿着多重意义和历史性。不可忽略的还有口述历史部分。叶嘉莹的言说是描述性的,情绪是潜隐的,却也映射了个人丰富的历史情绪和家国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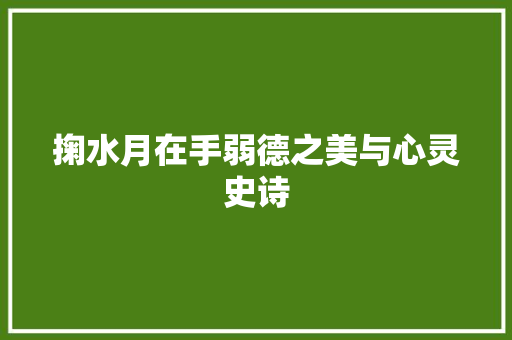
墨客痖弦曾形容叶嘉莹“意暖神寒”,是“空谷幽兰一样平常的人物”。这部电影让这种形象轮廓更为光鲜。没有影像参与的个人历史是不完全的。《掬水月在手》在纷繁繁芜的历史进程中激活了以叶嘉莹为象征的一代中国文人特有的魅力,这也使得本片具有了个人影像史诗的意味。(刘忠波)
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