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濯(zhuó,洗)
这首《沧浪歌》,出自《楚辞·渔父》一文。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幽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真切;中间采取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渔父》篇、《卜居》篇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取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靠近。
屈原沧浪遇渔父古时,汉江有一支流流经沔阳,名曰沧浪河。春秋战国期间,楚国大夫屈原流放之时,游经沧浪水,在张沟处遇渔父问渡,颇为伤感,渔父唱了一首《沧浪歌》启示屈原如何面对现实,传为历史佳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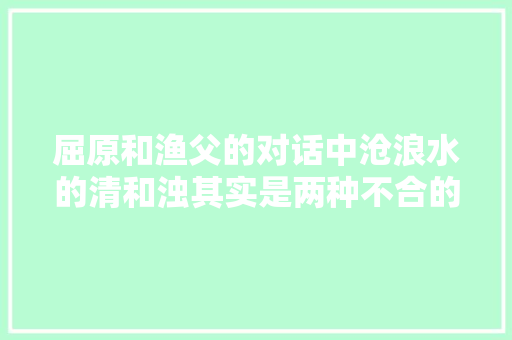
他们两人的对话,《渔父》篇中有详尽的记载,两人通过问答以遣词寓意: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干瘪,形销骨立。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
何故至于斯?”屈原曰:“全球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因此见放。”渔父曰:“贤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众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寻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如果用口语文来理解的他们的对话,大概便是渔父见屈原颜色干瘪,形销骨立,便问:“您不是三闾大夫么?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
屈原答“周围的人都肮脏只有我干净,大家都醉了,只有我复苏,因此被流放。”
渔父说到:“贤人不去世板地对待事物,而能随着世道一起变革。世上的人都肮脏,何不搅混泥水扬起浊波?大家都醉了,何不既吃酒糟又大喝其酒?为什么想得过深又自命清高,以至让自己落了个流放的了局?”
屈原断然地说:“我听说:刚洗过分一定要弹弹帽子,刚洗过澡一定要抖抖衣服。怎能让明净无比的身体,熏染上腌臜不堪的外物?我甘心跳到湘江里,葬身在江鱼腹中。怎能让晶莹剔透的纯洁,蒙上世俗的灰尘呢?”
渔父听了微微一笑,摇起船桨动身拜别,口中唱到:“沧浪之水清又清啊,可以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又浊啊,可以用来洗我的脚。”
文学家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汉赋是“受命于墨客,拓宇于楚辞”,在文体演化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略的主要地位的。
《渔父》中的人物有两个:屈原和渔父。全文采取比拟的手腕,紧张通过的形式,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情。全文六个自然段,分为三个部分。文章以屈原开头,以渔父结尾,中间四个自然段则是两人的对答。汉代学者刘向、王逸认为,《渔父》篇乃屈原自作;但当代《楚辞》研究专家,对此多持否定态度。马茂元师长西席认为,乃是楚人吊唁屈原之作,它从两种不同思想意识的比拟,表现了人们对付屈原沉湘自尽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刻理解。
《渔父》全文较长,个中最精彩的部分当属渔父唱出的这四句,因此这四句也被单独选出来,称为《渔夫歌》也是最能表示全文主旨的,这四句便是: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从《沧浪歌》的角度讲,《渔父》篇的主要性在于它供应了一个翔实的背景。
从《孟子·离娄》篇关于孔子曾听到童子唱此民歌的记载来看,可知它在春秋末年即已广泛流传,后来又被载入《楚辞·渔父》篇。
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屈原与渔父两个范例人物形象,他们秉持不同的人生态度与代价取向。屈原是一位恪守高洁的人格精神、“明净以取直、舍生取义”的空想主义者;而渔父则是一位顺应时期,与世推移,随遇而安的智者,看来他是一个隐士,并非真正以捕鱼为业的渔夫。
作为一位坚守儒祖传统的思想家、坚持自己的空想去改变现实的政治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墨客,屈原热爱公民,热爱祖国,从未希图躲避现实,更不肯在“兰艾杂糅”中亏损了明净崇高的实质;他以自沉湘江,表现出抗争到底的决心,和忠直清廉的高尚情操,这样,就使他的人格与作品同归不朽,永耀人寰。而渔父所吟唱的《沧浪歌》,则代表了盛行于楚地的范例的道家思想不雅观念。《庄子·人间世》篇有言:“天下有道,贤人成焉(造诣奇迹);天下无道,贤人生焉(保全生命)。方今之时,仅免刑焉。”
这和渔父所说的“贤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同一意蕴。他们识破了尘世的骚动,但并不回避,而是主见在随性自适中保持自我的人格、操守。这一点是屈原所不赞许,也并不真正理解的。
唐代墨客汪遵专门写了一首《渔父》诗,用诗歌进行了评价:“棹月眠流处处通,绿蓑苇带混元风。灵均(屈原)说尽孤高事,全与逍遥意不同。”
汪遵以屈原和渔父江畔问答的典故为题材,赞颂了渔父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间接表达了对屈原这一伟大爱国墨客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操。
该当说,《沧浪歌》所主见的,并非纯粹的悲观避世,专为个人全生自保打算,而是强调人不仅要刚直进取,也要在不损失本性、不同流合污的条件下,能够因时顺化,与世推移。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这分明是鼓励人们积极进取。“水清”比喻治世,而“缨”为帽带,是古代男子地位的象征,整饰冠缨喻准备出仕,有所作为;“水浊”比喻浊世,只能“濯足”。用老子的话说便是“和其光,同其尘”,大意便是涵蓄着光耀,混同着垢尘,这也符合孟子所持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不雅观点。
同样也是进行“清浊之辨”,而在孔子那里,对《沧浪歌》则作另一番解读,他说:“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
这段话是孔子给学生讲课时说的,大意是说:水清就能濯缨,水浊只可洗脚,这都是由水本身决定的。
据此,孟子引申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强调自身代价、主不雅观浸染,同样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