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毛主席对古诗词比较偏爱,他不仅爱读古人诗词,而且自己也善写诗词。他留下的浩瀚诗词,都成为民族最宝贵的文化和精神遗产。
毛主席不仅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而且,他还在实践中以自己的行动在践行这一方针。可以说,这一文艺方针的提出,正是老人家自己实践履历的总结。
毛主席常常改用古人和古人的诗词,如《七绝.试仿陆放翁》、《改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续李白〈梁甫吟〉》、《改鲁迅.〈亥年残秋偶作》等古人的诗作,都是语意出新的绝佳作品,深受人们的喜好。而在改写张元干《贺新郎》一词中的“举大白,听金缕”为“君且去,休回顾”,更是古为今用的妙笔。
毛主席改古人诗词的特点:一是整首改用,如《七绝.试仿陆放翁》便是最为范例的例子。二是对整首诗词中个别句子的改动,这类改写,是保持整首诗词的风格和主旨不变,而写是改写部分诗句或词句,以表达不同的思想或情绪。如改写张元干《贺新郎》一词中的“举大白,听金缕”为“君且去,休回顾”便属这一类。此外,毛主席还常常化用古人的诗句,也属于改写古人诗词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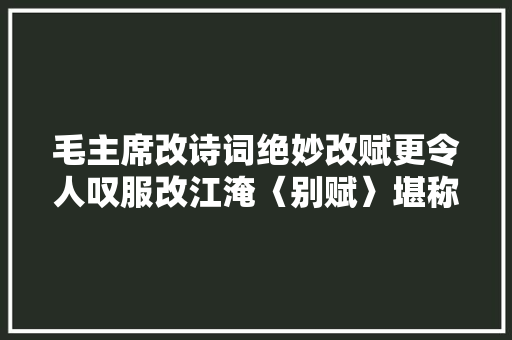
改写古人诗词,这在毛主席诗词创作中是比较多见的,而改古人赋中的句子为己所用的征象并不多见。这首《戏改江淹〈别赋〉》便是一个分外的例子,一些毛主席诗词爱好者乃至还把这一首归类为毛主席的诗词创作。严格说来,这种归类法是不足严谨的。
由于赋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它虽然也有诗的形式,但在实质上还是有差异的,诗词在格律上是有严格哀求的。而赋可不押韵,也不哀求对仗。表现手腕上,赋可平铺直叙,是介于诗词和散文之间的一种独立文体。
根据上文分折,毛主席的这首《戏改江淹〈别赋〉》应属改赋,而不应视作改诗。
为便于欣赏毛主席的改赋之妙,我们先对江淹的这篇《别赋》作以大略的先容。
江淹是南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六岁时便能写诗,任过左常待、尚书驾部郎、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职。江淹善辞赋,《恨赋》、《别赋》是他留存后世的经典名篇。
《别赋》,故名思义,是江淹以赋的文体形式所写的一篇赋。此賦中,江淹对世间各种离去作了归纳和总结,对戎人、富豪、侠客、游宦、羽士、情人等七种离去情绪分别作了深入细致的描写和剖析,写出了不同离去的不同特色。
从构造上讲,江淹在此赋的首句中便对世间离去作出情绪上的归纳,“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认为离去是最令人伤情的事儿。紧接着,赋中对七种离去遂一进行了描写。末了,作出归纳和总结:
因此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以是别离的双方并无一定,缘故原由有各类不同,但有别离就会有哀怨,有哀怨就一定满盈于心,使人意志损失,神魂滞沮,生理和精神上受到巨大的创痛和惶恐。
总之,江淹认为离去不是件啥好事,是件伤情的事情。
而毛主席改江淹赋中的一段话,却是反其意而用之,一扫此赋中的悲观感情而呈现出积极乐不雅观的心态,呈现出与原赋截然相反的情态。
原赋这段话是写恋人离去的: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乃至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这段赋文的意思是说,下界有男女咏芍药情诗,唱佳人恋歌。卫国桑中多情的少女,陈国上宫俏丽的春娥。春草呈现一片碧绿的颜色,河水泛起碧绿的微波,送郎君送到南浦,真令人伤心啊!
秋日的霜露像珍珠,深秋的明月似玉珪,珍珠般的霜露,光阴逝去还会回来,与你分别,思念的心在徘徊。
之以是展示了此赋的整段内容,是为了让大家对前后文所表达的情绪有个整体性理解。而毛主席所改的此赋是个中的四句,改赋如下: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
对照原文,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原賦的改动仅仅3个字,一是将地名南浦改为延安;二是将“伤”字改为“快”字。改地名是客不雅观上的须要。由于这首改赋是写于1939年7月9日,出在毛主席在送延安陕北公学的学生向抗日前哨开拔的演讲之中。因送别地点是延安,以是,毛主席才将原赋中的“南浦”改为“延安”。
而将“伤”字改为“快”字,这才是毛主席改这首赋的高妙之处和点睛之笔。这里的“快”字,是高兴和快乐之意。一字之改,境界全新,变伤感为高兴,二种感情的转换,尽在这一字之中。
陕北公学是共产党为抗日须要在陕北创办的一所学校,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侨胞,是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子的干部学校。送学员奔赴抗日前哨,毛主席心中自然高兴,但是,这毕竟是一种离去,若何表示这种不同时期的新型离去之情?因此毛主席才在演讲中借用江淹的这首《别赋》中的四句话,通过改写,翻新玉成新的语意,变伤感为豪迈,堪称是经典的改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