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儿女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嗟叹。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催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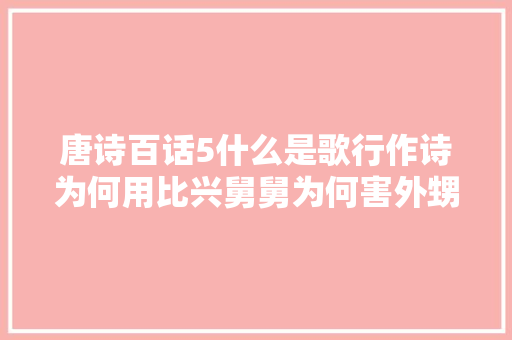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纪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去世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薄暮鸟雀悲。
这首诗的文体,名为“七言歌行”,是一种七言古诗的形式。
(一)歌行与律诗的不同之处
1.句数自由不固定,律诗句数有天命,如绝句为四句,律诗为八句,排律十二句以上等等。
2.歌行不须要对句,但律诗的颔联与颈联必须用对句。歌行作者偶尔会用几联对句,如刘希夷的这首《代悲白头翁》中的“已见松柏催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年年纪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等;当然也有全篇都用对句的,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
3.歌行的平仄粘缀没有律诗那样严格。
4.歌行不限韵数,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随便转韵。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这首诗用了六个韵脚,转韵五次。首联一韵(家),二联一韵(息),三、四联一韵(在、海),五、六、七联一韵(风、同、翁),八、九、十、十一联一韵(年、前、仙、边),十二、十三联一韵(丝、悲)。从协韵这个角度看,三、四联与十二、十三联就各是一首绝句,八、九、十、十一联就各是一首律诗。由此可见,一首歌行的句法、章法组织,包含了各种诗体在内。学写歌行体,同时便是学写各体诗。
(二)刘希夷的“以落花起兴”手腕
听说,刘希夷是宋之问的舅舅。他见外甥刘希夷所作《代悲白头翁》中有“年年纪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极为喜好;又知道刘希夷的这首诗还没有流传出去,就向外甥要了这两句,写入自己的诗歌。后来刘希夷反悔,透露了这个秘密,让宋之问受辱,于是他就派人用土袋子压去世了刘希夷,当时刘希夷还不到三十岁。这是唐人小说中记载的文艺轶事,未必可信,但从中可以看出刘希夷的这首《代悲白头翁》是非常有名的。
全诗十三联共二十六句,第一联至第六联共十二句为前半篇,以落花为中央,末了由“年年纪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转入后半篇,劝告青春兴旺的青年人,该当怜悯“半去世白头问”,当心自己老之将至。后半篇是全诗的主体,前半篇只是一个引子,这样的艺术手腕,叫“以落花起兴”。
(三)作诗为什么用比兴手腕?汉代有一位姓毛的学者,研究《诗经》,会给每一篇诗标明主题思想,称为“诗序”。在卷首的总序中,他提出“诗有六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风、雅、颂”是诗的三种浸染。浸染不同,文体也不同。《诗经》便是按照“风、雅、颂”三种文体编订的。“赋、比、兴”是创作方法。对付“赋、比、兴”的含意,朱熹的阐明最为简明准确:
赋——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朱熹
用我们本日的话来说,赋便是正面描写某种事物,修辞上可用渲染、夸年夜等。比是用一个事物比拟其余一个事物。兴是先讲一个事物,来引起主题思想中要用到的事物。这三种方法,赋最纯挚,比和兴似同实异,不易区分,常常“比兴”连用。可以这么说,比是直接比喻,兴是间接比喻。
作诗为什么要用比兴手腕呢?为什么不能像散文一样直白地说,而偏要用一个事物来比喻或兴起另一个事物?这是由于诗歌是形象的艺术,要引起人们想象。它不是数理化,用公式定懂得释一个抽象观点,诗歌用的是详细可感的事物形象。这即是所谓的形象思维。
刘希夷的这首《代悲白头翁》,先以落花来比人,以引起白头翁之可悲,比、兴皆用。这首诗比拟兴手腕的利用还非常大略,一读便知。歌行体发展到盛唐,李白、杜甫等大墨客都写了不少著名的歌行,他们的艺术手腕更高超,比兴的利用也更繁芜、更深刻、更隐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