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菊的生殖器下面,
蟋蟀在吊膀子。
写出来一看,虽然比粗人们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对付新墨客的由“烟士披离纯”而来的诗,还是“相形见绌”。写得太科学,太真实,就不雅观观了,如果改作旧诗,大概不至于这样。生殖机关,用严又陵师长西席译法,可以谓之“性官”;“吊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语源,但据老于上海者说,这是因泰西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来的,引伸为诱惑或追求异性的意思。吊者,挂也,亦即相挟持。那么,我的诗就译出来了——
野菊性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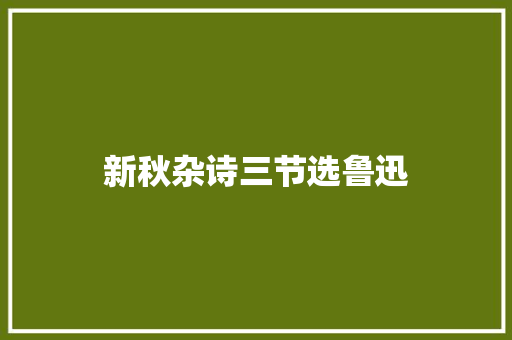
鸣蛩在悬肘。
虽然很有些费解,但彷佛也雅得多,也便是好得多。人们不懂,以是雅,也便是以是好,现在也还是一个做文豪的窍门呀。质之“新墨客”邵洵美师长西席之流,不知以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