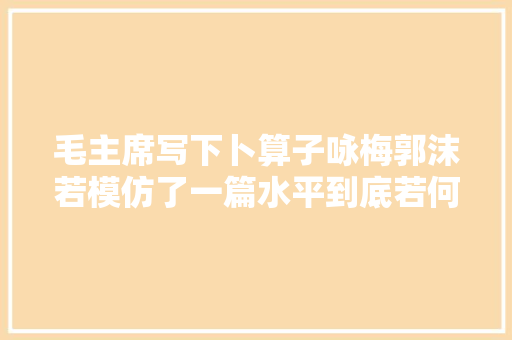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曾经给郭沫若填写过两首著名“相和诗词”,即《满江红·和郭沫若同道》和《七律·和郭沫若同道》。
前者是针对国际舆论的政治表态,后者是批驳海内的“改动主义”思潮。那么,作为毛主席的文学知音,郭沫若有没有为毛主席写过“和词”呢?
实在是有的,一九六一年,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问世之后,郭沫若也作了一首同名的和词。
一、郭沫若《卜算子·咏梅》赏析《卜算子·咏梅》——郭沫若
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
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
风雨任猖獗,冰雪随骄傲。
万紫千红结队来,各处吹军号。
口语翻译:
从前我们只能看到梅花的忧闷;如今我们终于见到梅花露出了笑颜。梅花盛放的时令,本来就有东风在孕育着春意。春天,是伴随着梅花的盛开,一起来到人间的。
听凭狂风雨猖獗地肆虐,梅花骄傲地伫立在雪窖冰天里。待到来年春暖花开之时,万紫千红的花朵成群结队而来,人间各处吹响了革命胜利的军号。
“曩”是从前,过去的意思。“曩见”便是指从前见到,这里特指作者过去见到的——陆游的梅花诗。
由于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是读到了陆游的同名词作之后写下的,二人的咏梅词,现在都已经被收录到语文教材里,以是在这里就不作详细解读了,单说郭沫若对陆游词的理解。
郭沫若认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表现的是一种封建文人的孤芳自赏。由于陆游在词中自比梅花,说自己是“寂寞开无主”,又说自己“无意苦争春”,把梅花写得爹不痛,娘不爱的。
陆游又有一首《朝中措·梅》,当中还有一句“东风不管”,潜台词是说“只有北风狂吹”。郭沫若因此批陆游“看不到公民的力量,因此感到孤独”,不如毛主席词中“幽美进取的情调”。
不过郭添若高明的地方是,在“曩见梅花愁”一句中,并没有直接点陆游的名,而是对“梅花”的意象做了进一步的提炼。
陆游词中的“梅花”,是指以作者本人为代表的怀才不遇的封建文人。毛主席词中的“梅花”是指倔强不屈,富有捐躯精神的革命先行者与孤胆英雄。
郭沫若在他的词中将毛主席的“梅花”又加上了一串“限定词”,于是他笔下的“梅花”既是革命的先行者,又是沐浴着“东风”的“孤胆英雄”。
由于有“东风”的关怀,以是我们如今见到的梅花是含笑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由于革命的“东风”代表着公民群众的力量,也代表着毛主席的关怀。
“东风”孕育着春天,有了“东风”,春天必将到来。“梅花”武断了这样的信念,于是听凭风霜雨雪来得如何剧烈,它都可以骄傲地昂开始特立在冰雪之中。
倒数第二句“万紫千红”,是指百花盛放时的场景。百花本是生根的植物,开放之后并不会移动,但是郭沫若极富创造力地让它们“结队而来”。
很显然,这里的“万紫千红”已被拟人化。那么它在这里比拟的是什么人呢?战士吹响了胜利的军号。当号声响起来时,沙场上红旗翻滚,百万革命大军人头攒动,便是那“万紫千红”。
以是在这首词里面,“梅花”象征着革命战士“个体”,“万紫千红”是“群体”。“梅花”是革命的先行者与孤胆英雄,“万紫千红”是追随者与革命的“中坚力量”。
通过剖析,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词写得很有技巧。首先,这首词相较陆、毛的原作,“意象”更加丰富、繁芜;
其次,这首词同时具有韶光与空间上的“张力”。前者是指“曩见”与“今见”的比拟,后者则是指从“春伴梅花”到“万紫千万”。
“春”的意象在这首词里并不是拟人的,如果说“东风”象征着毛主席与党组织对“梅花”的关怀的话,那么“春天”在这里事实上是指这种关怀带来的“有利环境”。
单独的“梅花”是伶仃的,但这里的“梅花”一贯有“东风”关怀,它并不孤独。刚开始是“东风”和单独的“梅花”在一起,末了是“东风”和全体革命战士一起。全体过程,“东风”是贯穿始终的。
再次,“风雨”二句形成了一个悖论,严厉的革命环境本来是给“梅花”制造困难的,现在这样的环境,反倒造诣了“梅花”的骄傲。
由于只有在严厉的斗争中,才能展现梅花的优秀品质。这就好比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
末了,“万紫千红结队”一句,直接将词作的感情推向了一个高潮,为整首词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如果我们不考虑思想感情与意识形态的话,纯挚从歌词的表现形式上来剖析这首词,郭沫若还是写得很成功的。
不过如果以批驳现实主义的史不雅观去评价这首词的话,那么它就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便是它可能“跑题”了。
由于“咏梅”词一样平常是指歌颂梅花精神的,但郭沫若在这里事实上歌颂的是“东风”。这首词中的梅花之以是能“骄傲随冰雪”,完备由于有“东风”伴它而生,“东风”在这里的浸染被“放大”了。
同时,郭沫若笔下的“梅花”遭遇的阻力不足强,非但不如毛主席词中“梅花”显得“倔强”,乃至连陆游词中“梅花”那种“零落成尘碾成泥,只有喷鼻香如故”的哑忍、悲壮之美都没有了。
结语郭沫若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文人,不过我们平时一提到他,首先想到的便是他的当代新诗。那是他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试验性创作,比如他的新诗《天狗》: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统统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
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不客气地说,这首诗在我们如今看来不但毫无美感,切实其实便是一个发癫的水准。某高校教授上课时,直接批驳这首诗写的是一个胆怯分子。
那么,你以为郭沫若的水平便是这样的吗?事实并非如此,实在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也写过不少“符合大众审美的旧体诗”,比如他少年时期的《夜泊嘉州》:
乘风剪浪下嘉州,暮鼓声声出雉楼。
隐约云痕峨岭暗,浮沉天影沫江流。
两三渔火疑星落,千百帆樯戴月收。
借此扁舟宜载酒,明朝当作凌云游。
上世纪二十年代,郭沫若考试测验创作新诗失落败往后,郭沫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返国抗日时,就转向写旧体诗词,他的说法是“旧瓶装新酒”。最初在返国途中他写了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愿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切切人齐蹈励,同心同德一戎衣。
又有一首《归国杂吟·春申江上》:
炸裂横空走迅霆,春申江上血风腥。
清晨我自向天祝:成得炮灰恨始轻。
这些诗都写得都很有古韵,且颇具文人风骨。解放往后,郭沫若由于政务繁忙,以是创作较少,再加上时期的缘故原由,风格也发生了很大变革。
总体上来说,郭沫若的旧体诗词中,也有不少写得还不错的诗,不过《现当代文学史》一样平常只收录他的新诗。
这紧张是由于这些旧体诗词只管比较符合大众审美,但是在思想内容上“创新”不敷。新诗虽然有点“步子大了扯了淡”,但是它们毕竟“发出了时期的先声”。
末了,郭沫若在《卜算子·咏梅》中,用旧词的形式注入新鲜的“革命思想”,也是他“旧瓶装新酒”的一种考试测验。至于这首词到底写得好不好,生于不同时期的人,恐怕会有不同的感想熏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