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作者姚锡娟与孙道临老师(左)摄于广州友情剧院
2000年“名剧名人名段朗诵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演出后合影。第一排左起:苏民、徐涛、姚锡娟。第二排左起:童自荣、吕中、曹雷、奚美娟、杜澎、张炬。第三排左起:林连昆、宋春丽、朱琳、孙道临。末了排为事情职员
姚锡娟看望尹桂芳老师(右)
2002年,在南京“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后合影。前排左起:张家声、孙道临、苏民、乔榛、姜江。后排左起:杨力、徐涛、肖雄、方明、凯丽、奚美娟、丁建华、姚锡娟、濮存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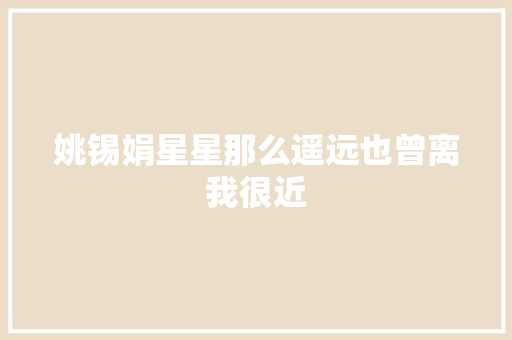
上海的盛夏不好过,热得让人无处藏身。年幼时哪有空调?风扇开到最大档,吹出的还是热风。以是我总是盼着夜晚的来临,洗完澡,吃完晚饭,就一溜烟地随着父亲到晒台上“纳凉快”去了。
晒台上凉风习习、兄弟姐妹间嬉闹争座、父亲用乡音吟着我听不明白的唐诗、转弯马路上那家豆浆店飘过来的阵阵喷鼻香味……还有啊,还有我坐在小板凳上,举头仰望天上那数来数去数不清的星星。父亲见告我,哪颗是牛郎星、哪颗是织女星、哪些是北斗星。我使劲找,使劲看,还比着哪颗星星最亮。偶尔争得躺在竹床上的佳位,那叫一个舒畅啊!
我直面迢遥神秘的满天星斗,充满好奇和抱负,眨着双眼,逐渐困倦,在深邃宁静的星空怀抱中睡着了。
我没有成为一个研究星星的天文学家,却成了一个戏迷、影迷。于是在我的生活中又一次涌现了那么多星星,他们生动在舞台上、银幕上。我仰着头,屛着气不雅观看他们精彩的演出,为他们喝采,喜好他们。然而他们也像天上的星星那么迢遥,遥不可及!
天上的仙女也有下凡的时候,何况他们是人间的精灵,有几次他们真的走到了我的身边,离我这么近。
(一)
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来到了上海科学会堂所在的那条马路上,那时该当是上海市文化局的所在地。大门口热闹非凡,红旗飘荡,锣鼓喧天,彷佛是由于所有民营剧团改归国营的大喜事。瞧瞧,我用的都是“大概”“该当”“彷佛”这样不愿定的词,但有一件事我是确定的,那便是看到了我心中那颗通亮的星星——俏丽的七仙女严凤英,她也在游行军队中。我禁不住奔向她,想见告她:“我喜好您,《天仙配》我看了十几遍了。”没承想我的话还没出口,笑颜满面的她就亲热地拉起我这个小戏迷的手,随着军队一起跑去。我都高兴晕了,做梦似的和她一起跑,估计跑了100米,文化局大门到了,星星就舍我而去……这颗刺目耀眼的星星后来受尽凌辱过早地陨落,我为她伤心哭泣,久久地思念她的“七仙女”“织女”“冯素珍”。六十多年前的事啊,与她携手同跑100米成了我永恒的影象,至今我的心中还留有她手上的余温。
1959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我来到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考场——中国福利会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的所在地。我是参加复试的考生,来得太早了,就只有我一个人,我悄悄静地坐在考场表面的椅子上,侧对着大门。溘然,一个熟习的身影进来了,那么高大、漂亮、帅气。天哪,他不是“电影天子”金焰吗!
我抑制着心中的惊喜,不动声色地坐着。殊不知他径直朝我走来,微笑着问我:“是考生吗?”我点点头。“紧张吗?”我又点点头。“不要紧张。”他手中拿着一张报纸,问我:“这是什么?”我轻声说:“报纸。”他迅速地卷起报纸:“如果这是一束花呢?”他做了个深深地闻花的动作,又说:“如果这是一条蛇呢?”我睁大眼睛望着他,他溘然惊骇地把手中的报纸往地下扔去……就这样,这位大明星给我上了一次生动的演出课。我大喜过望。与这颗星星的奇遇,终生难忘!
(二)
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当时从属于上海市电影局和上海市高教局,以是我们得天独厚,常有机会与星星们相遇。有时他们来开讲座啦,譬如张瑞芳老师、于蓝老师、陈强老师等等;有时候和上影的艺术家一起参加活动;有时候和他们一起参加演出。在这些幸福的相遇中,我这个未见过世面的学生也出过几次洋相,现在想起,还会掩面而笑。
那年,我们班上四个女同学被派去欢迎朝鲜电影代表团,到了火车站,才知道带领我们的是巨星赵丹老师。他是那么亲切激情亲切,没有一点架子,高兴地说我们带来了青春的气息。代表团出来了,我由于没有献过花,有点紧张,再加上自己干事从来粗枝大叶,以是一看到有人出来,就急匆匆把花献给离我最近的那个人。我刚要转身回来,只听那人笑着说:“我不是代表团的,我是翻译。”一听这话,我窘得面红耳赤,手足无措……这时只见赵丹老师出面了,他说:“哈哈,这解释我们两国公民长得多么相像啊,哈哈哈哈哈!
”顷刻间,《马路天使》中的那位男主人公的形象再现在我面前,他那诙谐风趣的神态、富有魅力的笑声传染了大家,也为我解了围。
有一年冬天,我们学校的老师、同学和王丹凤老师、路珊老师、陈述老师、冯奇老师还有祝希娟等一起,到安徽慰问演出。那时候我做什么都是重手重脚,走起路来也“腾腾腾”的劲道十足。演出前就在露天扮装,一个长桌子,几条长凳。有一次我和王丹凤老师坐在一条长凳上,我在涂底色,她在画嘴唇。我用手使劲地把脸上的底色拍匀,整条长凳都随着我的节奏颤动着,这颤动让丹凤老师凑在唇前的扮装笔无法下手,我却浑然不觉。等我“觉醒”过来,臊得只会连连说对不起。丹凤老师笑着安慰我,连说:“不要紧,不要紧。”她的好教化好脾气,连同那娇美的唇和笑颜永存在我的脑海之中。
(三)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师长西席杜熊文和秦怡老师一起参加了电影《外洋小儿百姓》的拍摄,剧中人关系是母子,以是此后熊文一贯称秦怡老师为“妈妈”。拍戏回来,他总是跟我提及秦怡老师的慈爱与辛劳,带着生病的儿子一起到摄制组,既有繁重的事情,还要照顾儿子……我听了非常冲动,也心疼秦怡老师,当然更万分倾慕熊文能与秦怡老师互助。我与她的第一次打仗,是上世纪80年代在昆明吧,我们一起在云南电视台参加活动。我竟能与心中的女神一起唱歌,一起用餐,过去是想也不敢想的。终于有一次在上海见面时,我情不自禁对她说出了心里话:“老师,您太好看了,我每次见到您,必是三步一转头,总也看不足啊!
”想必这样的话她听得太多太多了,她那双纯净深邃迷人的眼睛看着我,展露出清丽的笑颜。这笑颜让我忆起了《青春之歌》中的林红——那无与伦比的、大理石雕塑一样平常光洁崇高的形象。2011年,熊文陪顾小康师长西席一起到上海,约请秦怡老师来广州参加母亲节的朗诵会,89岁的她精神矍铄,俏丽依旧。她朗诵了自己写的诗《我们一起努力》,吐露了她与儿子努力降服病魔的心声,动听肺腑。星海音乐厅内耐久不息的掌声表达了不雅观众对这颗星星由衷的热爱,对这位伟大母亲的崇高敬意。今年她99岁了,我们在广州非常惦记她,祝秦怡老师福寿绵长!
(四)
中学的时候我开始爱看电影、听广播,喜好演出艺术、措辞艺术,尤其崇拜孙道临老师。无论在影院或是收音机旁,我都是他的“学生”。道临老师学贯中西,在电影、舞台和配音、朗诵艺术上都有着辉煌的造诣,单说他的措辞艺术,就影响几代青年演员和不雅观众。与道临老师这颗巨星的近间隔打仗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一年广州的冬天也特殊寒冷。记得他在不雅观看我们一次内部排练时,大家激情亲切哀求道临老师上台演出,他溘然说:“那我就和姚锡娟一起朗诵吧!
”那时我正在台上,毫无思想准备,手里还拿着稿子。道临老师上台来了,站在我阁下,一起看着我的稿子。我紧张得鼻尖都冒汗了,自己怎么有水平和这位大艺术家一起朗诵啊?好不容易沉着下来,当心翼翼地完成了这次意外的互助,深感荣幸。
1993年我举办个人朗诵专场演出,请道临老师题词,他特殊负责,第一次寄来的题词被邮政部门丢失了,他不厌其烦地重写了再寄来。2004年,又欣然许诺为我的朗诵专辑《回眸一笑》作序。1997年他还向北京音乐厅钱程师长西席推举我在“呼唤诗神”的演出中朗诵《卖火柴的小女孩》。从那时起,我们一群中青年演员聚拢在他的身旁,追随着他的朗诵艺术,生动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舞台上。他不仅是朗诵会的主要策划者,也是我们的导师。在“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上,我朗诵的《春江花月夜》和《望海潮》,在古诗词的情绪投入和韵脚的读音方面,都得到了道临老师关键的点拨。而当我在朗诵都德的《末了一课》时,他竟一贯站在侧台听,我回到后台就得到了他诚挚的鼓励。他既是老师,有时又是个“顽童”,常常做出一些惊险动作来恐吓我们,譬如假装滑跤啦、扭脚啦……然后高兴地用刁滑的眼力看我们一惊一乍的样子容貌。真是怀念啊!
在有道临老师举着大旗的那些年,朗诵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罹病后,我去看他,他依然兴致勃勃地朗诵起何其芳的诗《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巨星的猝然远去,令我们黯然神伤!
(五)
末了要捧出的这颗星星,是让我痴迷生平、想起来就要伤心落泪的越剧艺术大师、尹派艺术创始人尹桂芳师长西席。小时候,在大人的带领下去看尹师长西席的戏,她那种灵动和诙谐与生俱来,她的演出清新脱俗,她的舞台形象俊秀洒脱。能得到这样康健美好的艺术启蒙,是我的幸运。在上海这座文化大都邑中,她汲取着中外文化的精华,这使她从本真的脱俗上升到自觉的追求。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她的艺术达到了顶峰,佳作迭出。集稚气、秀气、才华、憨气于一身的曹雪芹笔下的“泥捏儿”贾宝玉(俞振飞师长西席语)、高洁若青松的三闾大夫屈原、痴情不改的张君瑞、侠肝义胆的程婴和陈琳、机警深情的何文秀、温润如玉的梁玉书和沙漠王子……数不胜数、维妙维肖的人物形象征服了越剧不雅观众,也风靡了上海。我从她的演出中不仅得到了艺术享受,领略了戏曲的曼妙,也理解了不少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我是她的戏迷,在台下为她摄人魂魄的演出拍红了手掌。80年代去她上海的家中探望,是我第一次在台下亲近这颗闪亮的星星。她的眼睛依然通亮清澈,她的腰背依然挺得笔直,她脸上仍挂着我认识的“宝玉”的笑颜。然而十年年夜难中她的身心饱受摧残,在死活线上蹉跎徘徊,究竟落下了半身不遂,不雅观众已不可能再在舞台上欣赏到她那竹苞松茂的艺术了!
我亲吻她的额,抚摸她残疾的右手——那曾经让无数不雅观众欣赏到出神入化扇子功的手啊……我欲哭无泪!
在她52岁到80岁的这段岁月中,她是如此困难又如此坚毅豁达地匍匐向前,仍旧执着于她未竟的奇迹。但是我不忍也不愿不雅观看为残疾后的她补拍的录像,这能代表她的艺术形象吗?我只是酸心肠问:“为什么她一部电影也没留下啊?!
” 2000年,星星回归星空去了……
现今,我不再仰望星空,是我的眼神不灵了,抑或是林立的高楼隐瞒住了满天星斗?幸而,那么多星星永久闪亮在我心中,在我的影象中……
星星那么迢遥,也曾离我很近。(姚锡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