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一种名为“悲秋”的情结。
▲秋叶。图源:摄图网
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将士由于自身境遇,常在秋日感同身受起宋玉的慨叹和悲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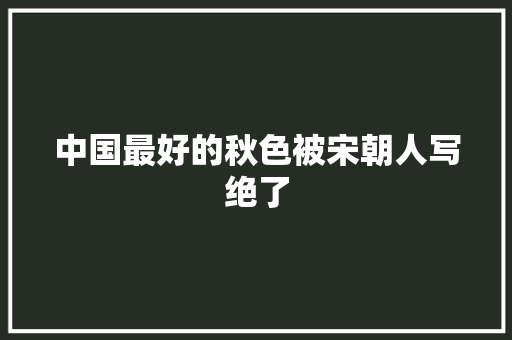
在零落的秋天景色下,人们为光阴易逝、生命凋零而感伤,更为离散的人事悲怆不已。
而宋词的悲秋情结,是从一个亡国之君的悄吟开始的。
01 李煜
开宝八年(975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军队在多日围城后一举攻破南唐后主李煜的金陵城。
李煜肉袒出降,亲手把国家奉上。
随后,这位亡国之君被押送至汴京,期待发落。
赵匡胤因李煜曾托病不应召、守城拒降等,封其为“违命侯”,以示羞辱。
接着,李煜便被安排在一座深院小楼之中,不得踏出半步。
曾为一国之君的李煜,面对这番囚禁的光景,昼夜忧思。
某个秋日夜里,院里的梧桐矗立在月光之下,看上去,阴冷,孤寂。那一刻,大概李煜与梧桐树之间产生了某种共鸣。
他写下《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记录下这个循环往来来往,孤独的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样平常滋味在心头。
亡国之恨,无人可语;人事缺憾,不可填补。胸中的离愁别绪让人透不过气,想逃,内心却仿佛陷入了缠绕的丝线当中,想剪剪不断,想理理不清。
▲月如钩。图源:摄图网
南唐国破的第三年,李煜逝于异域。
传言称,是宋太宗不满李煜作词时抒发的各类哀怨感情,在看到《虞美人》后终于忍无可忍,敕令将其毒去世。
无论是何种缘故原由,于李煜而言,大概这三年漫长得仿佛生平。早早结束,难免不免不是一件好事。
当往事随着旧人的拜别飘散,新人便开始讲述新的故事。
02 晏殊
生于公元991年的晏殊,恰好活在了大宋的升平期间。
自其作为神童入试,生平从政五十年,期间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地的大事,但也没整出过泣鬼神的幺蛾子。除了案牍劳形,此外,皆是风花雪月,歌舞酒席。
因此,他写的词,既有亭台楼榭中的歌舞升平,也有富余安逸下的苦闷忧思。
他也伤春悲秋,但不因家国而伤,更多是寄情山水草木,思考些人生问题。
在《清平乐·金风细细》中,晏殊便用婉转细腻的笔墨描述了他的秋日:
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
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阑干。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
晏殊耳边的秋风,一反人们心中寂寞凄厉的形态,而是如此地平淡、幽细,让人舒畅得也想甜睡于深秋之中。但梦醒之后,仍旧会因斜阳照栏,被提醒日暮已至,颇有些无可奈何。
▲落日余晖。图源:摄图网
这词,字里行间能让人觉得到华贵,但更多的则是闲雅。
原来抵牾的两种风格能够绝不违和地融于一体,大约只有这位“太平宰相”才能做到。
但,大宋真如面前所见这般壮大富余吗?
不过是有人知晓日暮,却更想沉溺于醉梦之中。
03 欧阳修
作为晏殊一手提拔起来的得意学生,欧阳修并没有同老师一样平常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而是选择进入改革的激流之中。
他曾经提醒过老师,“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身在其位,需谋其职,不应总是花天酒地。
只管如此,与老师合称“晏欧”的他,在这样一个繁华的时期,总免不了俗,风骚倜傥的他曾留下不少描述小儿女闺思的深情之作。
而秋日,恰好抒发离去的凄苦。《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便是这类词的代表作之一:
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悲惨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
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
能够如此细腻地描述闺中思妇的内心天下,想必是体会了不少才会有这一番笔墨。
▲月色夜竹。图源:摄图网
欧阳修年轻时,确曾风骚过,宴饮游乐、狎妓、写艳词,样样不落,这样的经历使他的文笔优柔细腻、感情朴拙。他的词作中,大部分表现了男欢女爱、离去相思、歌舞宴乐这样的内容。
然而,这些风骚美谈对被视为韩愈接班人、大宋精神偶像的欧阳修而言,并未化为嘉话,而是成为了被政敌攻击的痛处。一代偶像,终极毁于乱伦绯闻。
这样的风骚,人们认为放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更为得当。
04 柳永
当年轻的欧阳修刚刚投身科举考试时,人到中年的柳永已是第四次落榜。
二十多年的浮沉科举路,除了读书,柳永并没有闲着,而是流连多地看人间风景。尤其是最为繁华的江南,一容身便是七年。
登第前的柳永,大半生都流连于市井之中,以一种另类的办法声名鹊起。
▲江南古镇夜景。图源:摄图网
他出入青楼,留下的不止是感情,还有时期的“神话”。这位风骚才子写下的“青楼艳词”,时时让人惊艳,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爱他写的词。当时,妓女为了提高自己的有名度和身价,要特意请他题词才行。
这位多情浪子,注定情绪饱满、丰富。第四次落第后,开始对科举之路有些意气消沉,于是,他决定离开汴京。
离开之际,便深情地写下了这首与情人告别的《雨霖铃·寒蝉悲惨》:
寒蝉悲惨,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在这萧瑟冷落的秋日作别,实在难舍难分。此去一别,没有了分享的人,面前良辰美景有何意义?
这样颠沛流离的人生,直到他年过半百之际才结束。
05 范仲淹
跟柳永颠沛流离的人生一样,范仲淹也有过坎坷弯曲的经历。
范仲淹两岁丧父,随后便随着母亲再醮。童年时,他从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出生,直至被家中“兄弟”训斥他多管闲事,他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外人”。
知晓出生后,心情繁芜的他决定孤身一人踏上求学的道路。为了节省开支,平日会将煮好的一锅粥冷却,分为四块,然后早晚伴着腌菜各吃一顿。
幸好,这样的清苦日子只过了四年就结束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高中进士,入朝为官。
与前面词风婉转朦胧的词人不同,范仲淹的秋日,充满着保卫祖国的豪情与血性。
宝元元年(1038年)起,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参与经略西线边防,使得宋军在多次大败后,仍能够稳住西北边防。也正是在此时,他写下《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神。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之猛,猛到连对手都评价他“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而西北百姓,更是早已把“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歌谣传唱开来。
06 苏轼
在范仲淹前往西北的前一年,偏居帝国一隅的眉州(今四川眉山)降生了一位奇才。
传言,那一年的春天,眉州的彭老山百花不开,草木枯萎,皆因山河灵秀之气都被这位婴孩给吸走了——苏轼。
苏轼早期的声名,离不开欧阳修的安利。
当年,苏轼在科举中表现亮眼,随后,主考官欧阳修便多次跟人讴歌苏轼善读书、善用书,异日文章一定独步天下。还说过,30年后,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
事实证明,欧阳修看人很准。
苏轼文才之高,毋庸置疑,只是,为官几十年间,他也曾有过“平生笔墨为吾累”的无奈瞬间。
▲苏东坡。图源:图虫创意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遇了风大浪险的政治生涯中最大一次危急,史称“乌台诗案”。这场危急,可看作是王安石变法派系斗争中的余波。
当时,苏轼已调任至湖州,但朝中部分“新进”仍没有放过他。御史台几人捉住他上表文章和一些诗词中的字句,弹劾其愚弄朝廷,妄自傲大。
这波弹劾,让他被囚四个多月,末了贬谪至黄州,成为一个手无实权小官。
官海浮沉数十年,遭遇诬陷后的苏轼逐步无心参与到纷争之中,屡次请退,终于在1089年,获准外调杭州知州,离开是非之地。
曾经,苏轼笔下的秋日也有过人们熟习的样子容貌,孤独的、苦闷的、抵牾的……但末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概是《点绛唇·庚午重九再用前韵》中的达不雅观:
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江村落海甸。总作空花不雅观。
尚想横汾,兰菊纷相半。楼船远。白云飞乱。空熟年年雁。
如此感慨,是苏轼在回应杜甫当年的“老去悲秋强自宽”和“明年此会知谁健”。经历各类磨难之后,他依旧乐不雅观豁达,让人敬仰。
谁说自古逢秋悲寂寥!
07 黄庭坚
豪放热血的苏轼,门下弟子无数,而他最看重的有四人:黄庭坚、秦不雅观、晁补之、张耒。
“苏门四学士”之中,论学养和个性,最像苏东坡的大概是黄庭坚。
1086年,黄庭坚正式拜入苏轼门下,此时的他已经41岁了。这时,他才开始了人生中最快乐的三年:逐日与苏轼及其他门人朝夕相伴,切磋诗文,鉴赏字画。
除此以外,他生平多数光阴沉浮在黯淡的仕途之中,比如,曾因抵制劳民伤财的新政,被一贬再贬。
▲雾中孤舟。图源:摄图网
只管仕途坎坷,黄庭坚从未失落去本心。从前苏、黄二人还未相识的时候,苏轼早已通过他的诗作断定他“必轻外物而自重者”。
这位君子官员,只管官越做越小,却鲜有气馁、抱怨,只是把握好面前的统统,把事情做好便是了。
那些年,当黄庭坚从京师被贬到“蛮荒之地”黔州(今重庆彭水),再到戎州(今四川宜宾),他的心态一贯都很“稳”。
别人问他咋不焦急,黄庭坚张口便是:“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生平,又有何忧?”
在戎州时,某秋日夜里,黄庭坚同一群青年人赏月、饮酒。听到客人幽美的笛声后,他便忍不住写下《念奴娇·断虹霁雨》,定格这一晚心中的快意瞬间:
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桂影扶疏,谁便道,今夕清辉不敷?万里上苍,姮娥何处,驾此一轮玉。寒光零乱,为谁偏照醽醁?
年少从我追游,晚凉幽径,绕张园森木。共倒金荷,家万里,难得尊前相属。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
生平飘泊跌宕,又如何?该吃吃,该喝喝,耳边的乐曲,依旧以为悦耳动人。
随遇而安,这便是黄庭坚的生存聪慧。
08 秦不雅观
黄庭坚生平豪放不羁、豁达大度,与老师十分附近,而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不雅观,却显得有些“扞格难入”。
宋人条记记有一桩轶事。当年,30岁出头的秦不雅观,由于写了首饱含男女情愫的《满庭芳·山抹微云》,在民间名声大噪,尤其受女性的欢迎。某日,秦不雅观与苏轼久别相逢,稳坐豪放派一把手的老师上来就“夸”秦不雅观填词变厉害了,什么时候开始学柳永作词了?秦不雅观辩白道:“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师长西席之言,无乃过乎?”
但末了,秦不雅观还是成为了名流千古的婉约派一代词宗。对付这样的结果,该当可以用“口嫌体正派”来形容。
不过,他的词风,也是敏感薄弱的性情使然。
秦不雅观是个有才之人,但与杜牧十分相似,他同样因党派之争造成一身才学无处可施,进退两难。困顿不安的仕途让二心坎逐渐灰暗、阴郁。
秦不雅观笔下的秋日,是《满庭芳·碧水惊秋》里因旧人往事感伤的秋日:
碧水惊秋,黄云凝暮,败叶零乱空阶。洞房人静,斜月照徘徊。又是重阳近也,几处处,砧杵声催。西窗下,风摇翠竹,疑是故人来。
伤怀!
增怅望,新欢易失落,往事难猜。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谩道愁须殢酒,酒未醒、愁已先回。凭栏久,金波渐转,白露点苍苔。
看到零落的秋天景色,秦不雅观以为很难过。难过到纵然身旁有花,也无心去赏;纵然手边有酒,也难解千愁。
09 李清照
当秦不雅观这位多情之人为后世留下一首又一首直击心灵的婉约词作时,有位佳人横空出世,撑起了大宋婉约词的另一片天,在词史上为女性留名。
她是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
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的爱情,冲动过许多人。而二人的命运和结局,恰好见证了北宋的落幕。
李清照的前半生,是乐中有苦。只管赵家因政治斗争被贬、搬家,好歹夫妻二人还能在一起,患难与共。
▲李清照的词。图源:摄图网
但从靖康之难开始,她的人生只剩下苦中作乐。因战役和家中丧事,赵明诚先行南渡,李清照晚些前去会合。但会合没多久,赵明诚便因病去世,留下李清照一人去面对面前的兵荒马乱。
李清照的后半生,经历了不怀美意的欺骗、道德卫士的责怪,以及南宋朝廷的苟且。
面对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情状,纵然个性刚强,也难免有薄弱的时候。一首《声声慢·寻寻觅觅》,写尽她秋日里的干瘪和哀愁:
寻寻觅觅,冷生僻清,凄悲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干瘪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小雨,到薄暮、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靖康之难后的秋日,有的人如李清照一样平常,因国破家亡而难过;还有一些人,在投入保家卫国事业的过程中,有悲有喜。
10 陆游
陆游的生平,苦逼极了。他明明想做个战士,在宋金沙场上大展技艺,却大半生被那群主见屈膝降服佩服确当权派排挤,不得重用。
唯一一次军旅生活经历,是他在48岁的时候,受王炎约请来到抗金前哨南郑出任幕僚。
在南郑这片地皮上,陆游登高望远,看见了长安城的山脉。此时此刻,虽然战役远远没有结束,但他收复关中的激情亲切和期待却澎湃不止,于是写下《秋波媚·七月十六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抒怀: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宋朝军队收复失落地、胜利归来的情景,是了望时的想象,也是陆游的欲望。那时,他对国家的未来还充满着乐不雅观的感情。
面对那个总是懦弱、自欺欺人的南宋朝廷,确实该有人站出来唤醒大家的血性。
同样想当将领却被逼成文人的,还有陆游的好友,辛弃疾。
11 辛弃疾
辛弃疾生于、长于南宋的“沦陷区”,金朝的地盘。然而,在他做好准备往后,却绝不犹豫地投入到南宋的怀抱之中。
1161年,金朝对南宋发动战役,辛弃疾在济南附近的山区组织起一支农人叛逆师,随后投奔到当地叛逆师首领耿京旗下,从此参与到宋朝光复中原的伟大奇迹当中。
辛弃疾是一个文能挥笔,武能参战的全才。
▲辛弃疾像。图源:图虫创意
只管军事才干突出,但还是被懦弱的南宋给延误了。在官场上,他经历了多次反复无常的罢黜和起用,且用也总用不到点上,白白摧残浪费蹂躏了满腔热血和一身才干。
在那些被劾去职的光阴里,辛弃疾时时深陷于自己对国事无能为力的忧闷之中。
明明在游览风景如画的博山道,却溘然情绪上头,在道壁之中题写下《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青葱少年时,总是亢奋不已,无愁硬说愁;历尽千帆后,心中愁到极点却哑口无言。
此情此景,唯有轻轻用一句“天凉好个秋”带过那些说不出口的愁苦。
12 刘过
比拟起浮沉官海的主战官员,也有人生平未仕,在精神上加入了主战军队当中。陆游与辛弃疾的共同好友刘过,便是这样一位布衣爱国者。
刘过并非不想入仕,但考试运一样平常,四次落第,心中的抗金抱负只能通过词作抒发。
他的词,狂逸俊致,豪情万丈。四处流落的某个秋日,他刚好遇见了张路分举行的军事阅兵。他写《沁园春·张路分秋阅》,阐述他眼中的宋朝军事将领和军事场面:
万马不嘶,一声寒角,令行柳营。见秋原如掌,枪刀突出,星驰铁骑,阵势纵横。人在油幢,戎韬总制,羽扇从容裘带轻。君知否,是山西将种,曾系诗盟。
龙蛇纸上飞腾。看落笔、四筵风雨惊。便尘沙出塞,封侯万里,印金如斗,未惬平生。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平。归来晚,听随军鼓吹,已带边声。
这样气势磅礴的军队,很难让人不沸腾。但很遗憾,这样的沸腾,在那个时候,鲜少在真正的沙场上实现。
13 姜夔
南宋还有位著名词人,同样生平未仕,随处为家。他便是鬼才姜夔。
与那些关心前哨时局的爱国斗士不同,他更像是一位身负社会义务的记录者。
面对日渐颓败的王朝,他鲜有怒斥,更多只是诉说他亲眼所见的离乱、凋零,聊聊自己流落过程中的心情。
这位生活困难的流浪大师,每去到一个地方,总能感想熏染出一些什么。
而回抵家乡更是思绪万千。当在外飘荡多年的姜夔回到家乡鄱阳,登上声名显赫的彭家世族的小楼,一波波回顾袭上心头,作下《忆王孙·鄱阳彭氏小楼作》:
冷红叶叶下塘秋,长与行云共一舟。零落江南不自由。两绸缪,料得吟鸾夜夜愁。
望秋风落叶,姜夔想起了自己多年飘零的孤独与酸楚,想起了能够谅解自己的知心故人。
▲秋日的红叶。图源:摄图网
14 吴文英
当姜夔在宋词中开拓出不同于豪放、婉约两派的写作路径时,同样有一位词人作品十分独特,专注“做梦”。
他便是梦窗词的创始人,吴文英。
吴文英与姜夔一样平常,也是位江湖游士。在同样迷醉又不安的环境下,吴文英却很少表达对出生飘零的不满,或是怀才不遇的愤懑。比起谈政治,他更喜好谈情。
在他的340多首词作中,约有三成是爱情诗,这一比例超过了大多数两宋词人。
吴文英是一位情绪丰富而纤细的人,极其长于捕捉瞬间,尤其是主不雅观的瞬间。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词总能给人一种梦幻又真实的觉得。
凉薄的秋日,睹物思人,吴文英又做梦了。《解连环·暮檐凉薄》中,叫人有些分不清作甚虚实,但情绪还是一如既往地朴拙:
暮檐凉薄。疑清风动竹,故人来邈。渐夜久、闲引流萤,弄微照素怀,暗呈纤白。梦远双成,凤笙杳、玉绳西落。掩綀帷倦入,又惹旧愁,汗喷鼻香阑角。
银瓶恨沉断索。叹梧桐未秋,露井预言家。抱素影、明月空闲,早尘损图画,楚山践约。翠冷红衰,怕惊起、西池鱼跃。记湘娥、绛绡暗解,褪花坠萼。
梦窗的词,如梦,总是久久才能回过神来。不过,像他这样沉溺在自己的天下之中,喃喃自语,也是一种美妙的解脱吧。
15 文天祥
在风雨飘摇的南宋末年,有的人如吴文英一样平常不想多谈政治,多活一天是一天。但也总有人在浊世中挺身而出,作末了的努力。
他们知道面前是条“不归路”,但他们从不后悔。
大宋末了的风骨,在文官出身的文天祥身上。1275年,南宋皇室向天下发出勤王诏书,募人前往临安抵御蒙古人,但相应者寥寥无几,唯有文天祥二话不说,散尽家财组织起一支野生武装力量,加入到抗击元军的战阵之中。
但是,这样的抵抗并坚持不了多久。临安次年便沦陷了,南宋灭亡。
文天祥却连续奋战到末了一刻,直到1279年的崖山海战。
南宋灭亡后,有位名为王清惠的昭仪在被俘往燕京的路上写了一首《满江红》,引起了浩瀚文人的把稳。文天祥在被押送至金陵后,也读到了这首词,他思虑一番,提笔仿作一阕《满江红·代王夫人作》:
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最苦是、姚黄一朵,移根仙阙。王母欢阑琼宴罢,神仙泪满金盘侧。听行宫、半夜雨淋铃,声声歇。
彩云散,喷鼻香尘灭。铜驼恨,那堪说。想男儿年夜方,嚼穿龈血。回顾昭阳离落日,伤心铜雀迎秋月。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
文天祥借王夫人之口,陈述灭国之痛,但拟写此词,最紧张的目的是旋转原词中的结尾:面对亡国,不应盼求忍辱偷生,而应坚守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那是秋日,但,大概是大宋三百年间最坚毅的一个秋日。
文天祥在南宋灭国四年后殉国,真正为这个朝代画上了句号。
▲开封,曾经的北宋首都。图源:图虫创意
世间万物,皆逃不开盛衰更替。在秋日,人们可以为“逝去”而感伤,但也可以为“迎新”而倔强。
永久向前的韶光,终归会抚平统统。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唐圭璋等:《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
张玉璞:《“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齐鲁学刊》,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