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卜树,
不高高,
浑身吊些木刀刀。”
这第一卜树的特点是,个头不很高,但浑身“吊”满了“木刀刀”,这许许多多的“木刀刀”,便是它分歧凡响的地方了。而其余一卜呢?就高可齐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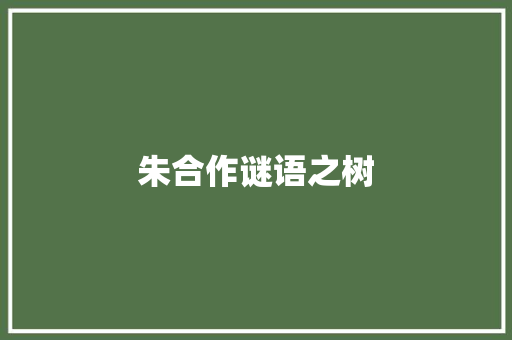
“一卜树,
万丈高,
一风过来刮断腰。”
这第二卜长得是很高,但身体却是不结实,大风那么一吹刮,就折断成了两半儿。这是两卜啥树呢?
这“树”实在不是“树”。说“树”只是打比方,它们实际是两只有趣的谜语:前面一只是“黄豆”,便是我们磨豆腐所磨的那种“豆”。后一个便是“炊烟”了,是山村落人家在做饭时,从烟囱中飘向天空的那一股高高的“烟”。
黄豆大家都熟习,春天种在地里头,等到秋日成熟了,浑身高下就结(吊)满了像小刀片一样的干豆角。那豆角中满含着一排排豆粒,干硬的豆角能把人的手划破。如此呢,不便是“一卜”长得“不高高”的“树”了么?
至于那“卜”高可“万丈”的大树,就要从另一个方向来理解了。有两句著名的古诗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秋夏两季风尘不动的岁月里,从黄土窑洞中飘绕出来的炊烟,也正和大漠中的“孤烟”一个样,一贯可以飞升到蓝天的最高处,何止百丈和千丈!
当然了,大千天下,天复地载,万物悉备,哪里会只有这么孤零零的两卜树儿呢?自然还会有更多的树,环绕在人们的生活中。这第三卜树儿么,也同样很奇妙:
“一卜树,
五股股,
当停卧个白虎虎。”
沿着前面的思路,我们也不难能想到,这“树”也不是什么植物界的“树”,而一定是一只俏丽的文化树,是谜语。便是的,不过,它的答案要轻微繁芜一点了,它说的是一个相互折衷的动作:是我们用饭端碗时,一个常常用到的动作:即五个手指头,中间端着一只盛饭的(白)瓷碗。这么着,那胳膊和从胳膊上延伸出来的五个手指头,就成“一卜树”,和它的“五股股”枝桠了。而手指头中间的那只(白)碗,便是当停(当中)“卧”着(而不是站着)的“虎虎”了。
自然了,谜语是打着比方说事儿,它紧张的思维路线是类比和遐想,那也就不仅仅只限于用“树”来做比方了。也可以用窑洞来比喻呀。如此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有了这样一眼窑:
“半崖上有个窑窑,
窑窑里有一片油糕。”
这个谜语的答案实在是“嘴巴”和“舌头”。人的嘴巴像不像半崖上悬着的一眼“窑”?那“舌头”又像不像一片“窑”中的“油糕”呢?这里边持续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把嘴巴比作了“窑”,把“舌头”比成了“油糕”。实在,“嘴巴”和“舌头”既不是“窑”,同时也不是“油糕”。把它们说成是“油糕”和“窑”,是谜语设谜的须要。统统都是打比方。还有这么一眼窑:
“一颗枣,
装一窑。”
这一回还真的便是“窑”——便是我们所住的“窑洞”。不过,这个谜语的重点不在“窑”,它的重点是那颗“枣”。
这是一颗啥样的“枣”?竟然能把“窑”装满!
实在它根本不是“枣”,而是像“枣”的样子容貌一样的麻油“灯”,也便是从老辈子那里传下来的那种,灯壶壶里边装着麻油的“灯”。能有那么大的枣儿吗?不可能。谜语都是从老辈子留下的聪慧果,只有那“窑洞”中的“麻油灯”,点起来才更像一颗通红透亮的“大红枣”。像“红枣”那么大,也像“枣”那么亮。它浑身柔和的射线,也确确实实能“装一窑”。“窑”多大,它(灯光)多大。以上是一眼虚拟的“窑”,是为了衬托那颗“枣”。当然也有写实的“窑”:
“脑小,
肚大,
尾巴朝天扎。”
这“窑”是一眼“真实的窑”,便是供我们用饭睡觉的“窑”。它仍旧是在打比方,只不过是用某一种动物来作比方,它是把“窑洞”中烧火做饭的“灶火(口)”,比作了动物身上的“脑袋”。把窑洞中晚上供人们睡觉的炕,比作了动物的大肚皮,而又把窑洞中冲天而起的高烟囱,比作了动物“扎”起的“长尾巴”。而这么着形象的一比喻,窑洞就完备变成了一头活蹦乱跳的动物了,你不爱它都弗成。
根据谜语遐想类比的原则,既然有“窑洞”的谜,那屋子也一定能入谜呀!
就有个屋子的谜语呢:
“三片瓦,
盖房房,
里头住个白娘娘。”
这便是一间“屋子”了。不过,这房间里住的“白娘娘”,又是哪家的“娘娘”呢?她住在一间仅仅用“三片瓦”盖起的屋子里,个头可真够小的!
它的个头是不大,这仍旧是在打比方,说的实在是“荞麦”。荞麦的形状不是呈三棱状态么?“三片瓦”,指的便是它的呈三棱状态的种皮。“三片瓦”里边藏着的荞麦仁,不是一派的白色么?因此,它只假如“娘娘”,就一定是一个“白娘娘”。
遐想是无穷无尽的,类比也永久是无限的。既然有平房的谜语,那楼房的也一定可以有:
“空中一座楼,
楼里住个花媳妇。”
这便是一座楼房的谜。这楼房挺神奇,就悬挂在半空中。半空中能悬什么楼?它当然不是楼,是大树上筑着的那个球形的喜鹊窝。喜鹊窝筑在树杈上,自然便是空中的楼。楼里的那个“花媳妇”,显然是一只女喜鹊。
“葛针门,
葛针寨,
里头盛个花秀才。”
它说的还是这座“楼”,主人也仍旧是喜鹊。只不过刚才是一只“女喜鹊”,现在是一只“男喜鹊”。而这一个喜鹊窝,刚才说它是“楼”,现在又说是“寨”。实在的还在树枝上,仍旧悬在半空中,只不过比喻的办法变换了。对付这种变革无穷的比喻,你的觉得怎么样?谜语这颗聪慧果,变革起来真有趣。还有一间泥巴房,主人也不是喜鹊了:
“南面上来个巧匠匠,
不带锛锯斧杖杖,
盖的屋子稳当当。”
这房里住的是燕子,这屋子便是个燕子窝。燕子窝都筑在窑洞之家的窑檐口,就像紧贴在弧形窗户之上的半只泥巴碗,实实在在“稳当当”!
“土门,
土窗,
里头盛个老张。”
也不知是“房”还是“窑”,也不知“老张”是那个?它实在是一只大老鼠,这一回指的是老鼠洞,也算是老鼠的窑洞吧?老鼠洞都打在黄土中,自然是“土门”和“土窗”,里里外外都是“土”,确确实实够“土”的。只不过,这一回老鼠有了姓,老鼠摇身成“老张”。
比方可以随便打。
“圆又圆,
扁又扁,
两只耳朵一只眼。”
这谜语说的是石磨。它又是怎么比喻的呢?“圆又圆”和“扁又扁”,是写实,是形容。石磨的两只大磨扇,确实是两块整整洁齐,又圆又扁的石头块。可“两只耳朵一只眼”,就肯定是一种比喻了,指的是磨面要有的“磨眼”,与拉磨要用的“磨把子”。
再来一个磨:
“上石崖,
下石崖,
白胡子老汉迸出来。”
这一次仍旧在说石磨,但重心已经不才面的“白胡子老汉”身上了——实在是在说“磨豆腐”。磨豆腐虽然离不开磨,可已和纯粹的说磨有所差异了,若假如没有那个“白胡子老汉”儿,在石崖的中间“迸出来”?还能够叫做磨豆腐么?
“一个布盒盒,
装五个兔娃娃。”
这是在说“鞋子”了。鞋子是个“布盒盒”,那“五个”所谓的“兔娃娃”,自然便是脚掌上伸出的脚指头。脚指头变成了“兔娃娃”,这真是变的太好了!
“是你不是你,
跟你在一起。”
是影子。你的影子是你吗?“是你不是你”,谁又能说清?反正“跟你在一起”,形影是永不分离的,永永久远在一起。
“金豆豆,
银豆豆,
反过正过没口口。”
是鸡蛋。鸡蛋多么宝贵啊,以是才变成了“金豆豆”,同时也变成了“银豆豆”。仍旧是在打比方。可实际上前面是铺垫,它的目的不才面这一句:“反过正过没口口”。“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个中,万八千岁······”它自古就没有“口口”啊!
如此的绝妙与经典,除了从老辈子那儿来,谁能够凭空想的出来呢?
“家里养了一群鹅,
吱吱嘎嘎跳下河。”
“南面上来一群雁,
叽叽呱呱进了店。”
谜语虽然是两个,指的却是一件事:煮饺子。不管是“鹅”还是“雁”,都是捏好的“原饺子”。也不管是“河”,还是“店”,也完备是为“煮”饺子预备的“开水锅”。不过呢,这些个“天鹅”和“大雁”,彷佛并不怕“开水锅”。不是“叽叽嘎嘎跳下河”,便是“叽叽呱呱进了店”。真正的“赴汤”如“赴水”(下河)啊!
上面吃过了饺子,下面再尝个粽子吧。粽子的谜语很华美:
“三角四楞长,
珍珠抱红娘。
想吃红娘肉,
解带脱衣裳。”
是不是华美和诱人?这“珍珠”和“红娘”是谁呀?便是小米与大红枣。“红枣”与“小米”你知道吧?清涧河流域是天下红枣与糜谷的原产地,是栽培枣树和糜谷最早的地方之一部分。用清涧河流域的谷米与红枣包出的粽子,哪怕从五月“端午”存放到“端十五”,也绝不会变质与变味。深深的一口咬下去,甜丝丝,凉丝丝,余喷鼻香缠绕在嘴齿间,三日也赶不走,一辈子也忘不掉!
再来碗米酒吧:
“瓷州城里起了云,
罗州城里雨儿淋。
铁州城里发大水,
推了主人的肚肚城。”
持续筑就了四个“城”。实在,这城都是些啥城呢?“瓷州”是大瓷缸,是做米酒时,让黄米发酵的大瓷缸。由于让黄米发酵是第一步,以是算是“起了云。”有了云彩就该当下雨呀,“罗州城”便是过滤“原酒”的“罗子”。发酵好了的原酒都是煮熟米粒的稠粥状,必须拿罗子来过滤,把米汁滤大锅中——中这间是有点下雨的意思。把米汁在铁锅中烧开来,那大铁锅就自然是“铁州城”。把做好的米酒喝进肚皮里,这便是末了的“肚肚城”。不过,为何要“推了主人的肚肚城”?由于,米酒喷鼻香,最好喝;喝的多,难免就“推了”“肚肚城。”这里边又藏个比喻:是拿发大水作比喻,夏天下雨发大水,物件让大水卷走叫“推”。所谓“推”了“肚肚城”,便是你喝的太多了。喝的那么多,不“推”能成吗?
遐想是无穷无尽的,比喻也是无限的。如此呢,我们清涧河流域的谜语,也就数也数不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临了再说一个吧,这一个最有趣,是一只自相缠绕的“悖”谜语: “埋
埋,
可炕歪,
歪。”
实在,在我们清涧河流域的词典中,是不常用“谜语”这个词语的。我们把谜语都叫做“埋”——“Mai”。“埋”便是“谜语。”“谜语”便是“埋”。说“埋”便是指这句话里有一些“埋伏”,也便是有“伏笔”,理解起来大概要费一点斟酌。
“埋,埋,可炕歪,歪。”
实在便是拿着谜语说谜语,终极指的是“笤帚”,是笤帚斜着扫炕的这个过程与动作。翻译成大口语,便是:
“谜,
谜,
谜便是满炕扫,
也正是扫炕的你。”
“歪”是干什么?便是“笤帚”斜着打扫炕上灰尘的动作呀!
斜着不便是“歪”了吗?而实际上,“歪”也不仅仅是斜着,还有层向前挪动的意思在里边。扫炕不是要挪动“笤帚”么?那就叫向前“歪”。因此,在清涧河流域的词典中,自然就有了这么个:“歪”——“wai”!
可这么着来翻译,就索然寡味了,还有点谜语的味道吗?谜语都是从老辈子那里传承下来的聪慧果,是清涧河两岸居民的集体无意识——同时是集体故意识。由于浑然如天成,它也就早已犹如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是一种不可解构的整体了。一解析,就变味,就精灵之气全失落了,哪里还再像个谜语呢!
只能照着原样说:
“埋,
埋,
可炕歪,
歪。”
谜语说到此处了,我们也打个比方吧,打个比方来结尾:实在,在清涧河流域的地皮上,谜语就像一卜树,有树干,有枝桠,枝桠上面结着许许多多的谜语果:有大雁。有天鹅。还有兔子和有灯笼。有鸡蛋。有红枣。乃至还大磨盘······千奇百怪啥都有,就像那卜“黄豆树”,“浑身吊些木刀刀”。不过,却不是“不高高”!
大小高低正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