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第四场开场词
-拓展-
1.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出自魏晋陶渊明的《饮酒·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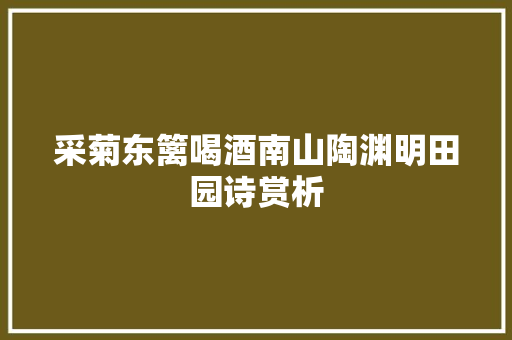
结庐(lú)在人境,而无车马喧(xuān)。
将房屋建造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却不会受到世俗交往的喧扰。
结庐:建造住宅,这里指居住的意思。结,建造、构筑。庐,简陋的房屋。
人境:鼓噪扰攘的尘世。
车马喧:指世俗交往的喧扰。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只要心中所想阔别世俗,自然就会以为所处地方僻静了。
君:指作者自己。
何能尔:为什么能这样。
尔:如此、这样。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jiàn)南山。
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
悠然:闲适淡泊的样子。
见:瞥见,动词。
南山:泛指山峰,一说指庐山。
山气早晚佳,飞鸟相与还(huán)。
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环抱,飞鸟结伴而还。
山气:山间的云气。
早晚:傍晚。
相与:相交,结伴。
相与还:结伴而归。
此中有真意,欲辨(biàn)已忘言。
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分辨清楚,却已忘了若何表达。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诗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间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由于“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纵然处于繁盛热闹繁荣的环境里,也犹如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空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真风告逝,大为斯兴”,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蚀,全体社会腐败阴郁,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隐居田园,躬耕自资。“结庐在人境”四句,便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滋扰之后所产生的感想熏染。所谓“心远”,即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进弃世,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托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古人激赏其“词彩精拔”。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中的“心远”是阔别官场,更进一步说,是阔别尘俗,超凡脱俗。 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代价尺度,打听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扯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办法,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而且,乃至更主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全体自然和宇宙而存在。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以是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墨客在自己的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有光阴抬开始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法则,既可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以是,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散逸而清闲,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彷佛有共同的旋律从民气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早晚佳,飞鸟相与还”此四句叙写墨客归隐之后精神天下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有光阴举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环抱,飞鸟结伴而还。墨客从南山美景中遐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朴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仕,末了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墨客在《归去来兮辞》中曾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宛如彷佛自己无意于仕而仕;鸟之倦飞知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
“采菊东篱下”四句,古人对此评价甚高。张戒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那么,张戒所说的“味”是什么呢?为何说“此味不可及”呢?我们知道,陶诗不尚藻饰,不事雕琢,明白如话,朴素自然,故古人常用“平淡”两字以概其诗风。但陶诗之平淡乃从“组丽”中来,是平而有趣,淡而有味。这种貌似平淡实则醇美的特色,实为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非常人所知,亦非常人所能。张戒所说的“味”,当是陶诗醇美的韵味。此种韵味之以是“不可及”,缘故原由固然浩瀚。我们撇开文学教化、艺术才能等条件,可以说这种韵味只有像陶渊明那种不愿顺俗浮沉,不肯汩泥扬波的墨客才能写出,也即只有寄心于远、心境“至闲至静”者才能写出。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末两句,墨客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情。诗里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秋夕篱边),也可理解为全体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恬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融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表示了墨客安贫乐贱、励志守节的高尚风致。 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真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若何用措辞表达。“忘言”普通地说,便是不知道用什么措辞来表达,只可融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
此诗紧张描摹墨客弃官归隐田园后的悠然自得心态,表示出陶渊明决心摒弃浑浊的世俗功名后回物化然,陶醉在自然界中,乃至步入“得意忘言”境界的人生态度和生命体验。此诗以“心远”纲领全篇,并分三层揭示“心远”的内涵。首四句写身居“人境”而精神超脱世俗的虚静忘世态。中四句写静不雅观周围景物而沉浸自然韵致的归天忘我心态。末了两句又深进一层,写“心”在物我浑化中体验到了难以言传的生命真谛此诗意境从虚静忘世,到归天忘我,再到得意忘言,层层推进,是陶渊明归隐后写意自然人生哲学和返璞归真诗歌风格最深邃、最充分的表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无我之境、以物不雅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首诗便是陶渊明“以物不雅观物”所创造的“无我之境”的代表作。
创作背景
这首诗大约作于公元四一七年,即墨客归田后的第十二年,正值东晋灭亡前夕。作者感慨甚多,借饮酒来抒怀写志。
2.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出自魏晋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年轻时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性情,生来就喜好大自然的景致。
少:指少年时期。
适俗:适应世俗。
韵:气质、情致。一作“愿”。
丘山:指山林。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误落 一作:误入)
缺点地失守到仕途罗网,转眼间阔别田园已十余年。
尘网:指尘世,官府生活污浊而又拘束,犹如网罗。这里指仕途。
三十年:有人认为是“十三年”之误(陶渊明做官十三年)。一说,此处是三又十年之意(习气说法是十又三年),墨客意感“一去十三年”腔调嫌平,故将十三年改为倒文。
羁(jī)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笼子里的鸟儿怀念以前生活的森林,池子里的鱼儿思念原来嬉戏的深潭。
羁鸟:笼中之鸟。
恋:一作“眷”。
池鱼:池塘之鱼。鸟恋旧林、鱼思故渊,借喻自己怀恋旧居。
开荒南野际,守拙(zhuō)归园田。
我愿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南野:南面的野外。一作“南亩”,指农田。
际:间。
守拙:意思是分歧流合污,恪守节操。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绕房宅周遭有十余亩地,还有那茅屋草舍八九间。
方宅:宅地方圆。一说,“方”通“旁”。
榆柳荫(yìn)后檐,桃李罗堂前。
榆树柳树成荫遮盖了后屋檐,桃树李树整洁的栽种在屋前。
荫:荫蔽。
罗:罗列。
暧(ài)暧远人村落,依依墟里烟。
远处的邻村落屋舍依稀可见,村落上方飘荡着袅袅炊烟。
暧暧:迷蒙隐约的样子。
依依:柔柔而缓慢的飘升。墟里:村落。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diān)。
深深的街巷中传来了几声狗吠,桑树顶有雄鸡一直啼唤。
颠:顶端。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庭院内没有世俗琐杂的事情烦扰,静室里有的是安适清闲。
尘杂:尘俗杂事。
虚室:空室。
余闲:空隙。
久在樊(fán)笼里,复得返自然。
久困于樊笼里毫无自由,我今日总算又归返林山。
樊笼:蓄鸟工具,这里比喻官场生活。樊,藩篱,栅栏。
返自然:指归耕园田。
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不由自主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述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屯子生活的淳厚可爱 ,抒发归隐后愉悦的心情。这是第一首。紧张因此追悔开始,以光彩结束,追悔自己“误落尘网”、“久在樊笼”的压抑与痛楚,光彩自己终“归园田”、复“返自然”的惬意与欢欣,真切表达了墨客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山林隐居生活的无限神往与怡然陶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谓“适俗韵”无非是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这是墨客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诚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厚的村落庄、宁静的自然,彷佛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以是“爱丘山”。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情,看破官场后,执意离开,对官场阴郁的不满和绝望。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墨客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缘故原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尘网:尘世的罗网。“三十年”该当是“十三年”,他从开始作江州祭酒,到辞去彭泽县令,前后一共十三年。以是“一去三十年”是“一去十三年”之误。这两句是说,自己不得已出去做官,一去便是十三年。
起首四句,先说个性与既往人生道路的冲突。“适俗韵”无非是指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吧,这是墨客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诚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厚的村落庄、宁静的自然,彷佛有一种内在的共同之处,以是“爱丘山”。前两句表现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情,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墨客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缘故原由。但是人生常不得已,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常日的选择;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便是为了养活家小、坚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须要做官。以是不能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转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羁鸟:被束缚的鸟。池鱼:池塘里养的鱼。故渊:指鱼儿原来生活的水潭。这两句是说,关在笼中的鸟儿留恋居住过的山林,养在池中的鱼儿思念生活过的深潭。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际:间。拙:笨拙。自谦之词,与世俗的机巧相对而言。这两句是说,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这四句是两种生活之间的过渡,前两句集中描写做官时的心情,从上文转接下来,语气顺畅,毫无阻隔。由于连用两个相似的比喻,又是对仗的句式,便强化了厌倦旧生活,神往新生活的感情;再从这里转接下文,就显得自然妥善,丝毫不着痕迹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是简笔的勾勒,以此显出主人生活的简朴。但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竞艳于堂前,素淡与绚丽交掩成趣。
“暧暧远人村落,依依墟里烟。”暧暧,是模糊不清的样子,村落相隔很远,以是显得模糊,就像国画家画远景时,每每也是淡淡勾上几笔水墨一样。依依,形容炊烟柔柔而缓慢地向上飘升。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致,给人以沉着安详的觉得,彷佛这天下不受任何力量的滋扰。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下子将这幅美好的田园画活起来了。这二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而稍加变革。但墨客绝无用典炫博的意思,不过是信手拈来。他不写虫吟鸟唱,却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由于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最富有屯子环境的特色,和全体画面也最为和谐统一。模糊之中,是否也渗透了《老子》所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去世不相往来”的空想社会不雅观念,那也难说。单从诗境本身来看,这二笔是不可短缺的。它恰当地表现出屯子的生活气息,又丝毫不毁坏那一片和平的意境,没有鼓噪和烦躁之感。以此比较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那种为人传诵的所谓“以动写静”的笔法,难免不免太强调、太吃力。
这八句是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彷佛墨客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不雅观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逐一先容: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落、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墨客点化,都添了无穷的情趣。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尘杂是指尘俗杂事,虚室便是静室。既是做官,总不免有许多自己不愿干的蠢事,许多无聊应酬吧。如今可是全都摆脱了,在虚静的寓所里生活得很清闲。不过,最令作者愉快的,倒不在这清闲,而在于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又是指顺适本性、无所扭曲的生活。这两句再次同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呼应,同时又是点题之笔,揭示出《归园田居》的主旨。但这一呼应与点题,丝毫不觉勉强。全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新生活的愉快,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这样的结尾,既是用笔风雅,又是顺理成章。
这首诗最突出的是写景———描写园田风光利用白描手腕远近景相交,有条有理;其次,诗中多处利用对偶句,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比拟手腕的利用,将“尘网”“樊笼”与“园田居”比拟,从而突出墨客对官场的厌恶、对自然的热爱;再有措辞明白清新,几如口语,朴实无华。这首诗呈现出一个完全的意境,诗的措辞完备为呈现这意境做事,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总之,这是经由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
创作背景
陶渊明任官十三年,却一贯厌恶官场,神往田园。他在公元405年(义熙元年),即四十一岁时末了一次出仕,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即辞官回家。往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本诗便是个中一首。
3.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出自魏晋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我在南山下栽种豆子,地里野草茂盛豆苗稀疏。
南山:指庐山。
稀:稀少。
晨兴理荒秽(huì),带月荷锄(chú)归。
清晨早起下地革除杂草,夜幕降临披着月光才回家。
兴:起床。
荒秽:形容词作名词,
荒漠:指豆苗里的杂草。
秽:肮脏。这里指田中杂草
荷锄:扛着锄头。荷:扛着。
道狭草木长(cháng),夕露沾我衣。
山径狭窄草木丛生,夜间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裳。
狭:狭窄。
草木长:草木成长茂盛。
夕露:傍晚的露水。沾:露水打湿。
衣沾不敷惜,但使愿无违。
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愿我不违背归隐心意。
足:值得。
但使愿无违: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就行了。
但:只。
愿:指神往田园生活,“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与世俗与世浮沉的意愿。
违:违背。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通俗俗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墨客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
本诗共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反响了作者躬耕劳动的生活。暗用杨恽诗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两句写墨客归田园后在南山的山脚下种了一片豆子,那地很荒,草长得很茂盛,可是豆苗却稀稀疏疏的。起句平实自若,如叙家常,就像一个老农在和你说他种的那块豆子的情形,让人以为淳厚自然,而又亲切。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为了不使豆田荒漠,到秋后有所收成,墨客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玉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说比做官要辛劳得多,可这是墨客乐意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墨客在《归田园居》(一)中所说的那样:“少无适俗韵,本性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墨客厌倦了做官,“守拙归田园”才是最爱。从“带月荷锄归”这一美景的描述就可以看出来,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反而乐在个中。
后四句是本诗的第二层,抒写的则是作者经由生活的磨励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虑之后,对真善美空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污浊官场的破碎。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通过道窄草深,夕露沾衣的详细细节描述,显示出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艰巨。墨客身体力行终日劳作在野外,以是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它绝不像那些分开劳动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般轻松洒脱。但是作者仍不辞劳苦,连续坚持下去,正像他在《庚戌岁玄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所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衣沾不敷惜,但使愿无违。”对付墨客来说,人生的道路只有两条任他选择:一条是出仕做官,有俸禄担保其生活,可是必须违心地与世俗与世浮沉;另一条是归隐田园,靠躬耕劳动坚持生存,这样可以做到任性存真坚持操守。当他辞去彭泽县令解绶印归田之际,就已经做出了决议,宁肯肉体耐劳,也要保持心灵的纯洁,他武断走上了归隐之路。为了不违背躬耕隐居的空想欲望,农活再苦再累又有何惧?那么“夕露沾衣”就更不敷为“惜”了。这种思想已经成了贰心中牢不可破的武断信念,本诗结尾两句’,可谓全篇的诗眼,一经它的点化,篇中醇厚的旨意便合盘现出。
陶诗于平淡中又富于情趣。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墨客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墨客,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
个中洋溢着墨客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满。“种豆南山下”平淡之语,“带月荷锄归”柔美之句;前句实,后句虚。全诗在平淡与柔美、实景与虚景的相互补衬下相映生辉,柔和完美。
创作背景
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不由自主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本诗便是个中的第三首。
4.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出自魏晋陶渊明的《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落,非为卜其宅。
从前想移居住到南村落来,不是为了要挑什么好宅院;
南村落:各家对“南村落”的阐明不同,丁福保认为在浔阳城。
卜宅:占卜问宅之休咎。这两句是说从前想搬家南村落,并不是由于那里的宅地好。
闻多本心人,乐与数晨夕。
听说这里住着许多纯朴的人,乐意同他们度过每一个早晚。
本心人:指心性纯洁善良的人。李公焕注云:“指颜延年、殷景仁、庞通之辈。”庞通,名遵,即《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之庞主簿。
数:屡。
晨夕:朝夕相见。
怀此颇熟年,今日从兹役(yì)。
这个动机已经有了好多年,本日才算把这件大事办完。
怀此:抱着移居南村落这个欲望。
颇熟年:已经有很多年了。
兹役:这种活动,指移居。
从兹役:屈服心愿。
敝(bì)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简朴的屋子何必求大,只要够摆床铺就能心安。
蔽庐:破旧的房屋。
何必广:何须求宽大。
蔽床席:遮蔽床和席子。
取足床席:能够放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取了。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邻居朋友常常来我这里,谈谈过去的事情,大家各抒己见;
邻曲:邻居,指颜延之、殷景仁、庞通等,即所谓“本心人”。
抗:同亢,高的意思。
抗言:抗直之言,高谈阔论或高尚其志的辞吐。
在昔:指往事。这两句是说邻居常常来访,来后便高谈阔论往事。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见有好文章大家一同欣赏,碰着疑难处大家一同研讨。
析:阐发文义。所谓析义,紧张是一种哲学理趣,与一样平常剖析句子的含义不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春秋两季有很多好日子,我常常同朋侪一起登高吟诵新诗篇。
“春秋”两句:大意是说春秋多晴朗景象,恰好登高赋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zhēn)酌(zhuó)之。
经由门前相互呼唤,聚在一起,有美酒,大家同饮共欢。
斟:盛酒于勺。
酌:盛酒于觞。
推敲:倒酒而饮,劝人饮酒的意思。这两句是说邻人间相互呼唤饮酒。
农务各自归,空隙(xiá)辄(zhé)相思。
要干农活便各自归去,空隙时则又相互思念。
农务:农活儿。
辄:就。
相思:相互怀念。
相思则披衣,说笑无厌时。
思念的时候,大家就披衣相访,谈谈笑笑永不厌烦。
披衣:披上衣服,指去找人谈心。
厌:知足。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这种饮酒说笑的生活的确很美好,抛弃它实在无道理可言。
此理:指与邻里过从畅谈欢饮之乐。
理:义蕴。
将:岂。
将不胜:岂不美。
兹:这些,指上句“此理”。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穿的吃的须要自己亲自去经营,躬耕的生活永不会将我欺骗。
纪:经营。
其一
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落,非为卜其宅。闻多本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休咎,而在乎邻里之善恶。墨客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神往南村落,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墨客听说南村落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乐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期,对充满虚伪、刁狡、钻营、排斥的社会风气咬牙切齿,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墨客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熟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迁移转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墨客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落的欲望早就有了,终于实现的时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屋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个中,墨客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里那边所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旧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
何时面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去世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风致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壁。
末了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详细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义熙七年(411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墨客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诗中所说的朋侪,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人“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顾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剖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互换。墨客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期。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期间。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乐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往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想熏染是光鲜而强烈的:墨客厌恶阴郁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屯子田园、亲人朋友的朴拙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安歇。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墨客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墨客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措辞,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近,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地。“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涯鸿鹄。又如墨客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情,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剖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真切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由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楚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括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沉着。陶诗看似平凡,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分外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抵牾,大概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阐明,以坦然旷达的肚量胸襟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表示。
其二
古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期,“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难堪,其名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清闲之笔写得意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噜苏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奥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轫,概括全篇,解释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失火之后,新迁南村落,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得意。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时令,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意见意义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落的“本心人”可与共赏新诗。以是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平凡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墨客之神色超旷,也如在面前。
移居南村落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推敲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约请的虚礼,态度村落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姿,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墨客;也可能是墨客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墨客有酒便一起推敲,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落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以是愈觉蕴藉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以为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空隙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说笑无厌时。”有酒便相互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落,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诚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清闲家垦植,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韶光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若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故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若。这种往来来往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来来往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大略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交情的深厚。披衣而起,可见纵然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墨客与村落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定,那么披衣而起、说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韶光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以是,将墨客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意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欲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由于乐中有理,由任情写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统统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表示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样平常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不雅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彷佛也可以用来阐明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本色内容和表现办法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崇高,社会地位优胜,逐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博识莫测,实在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不雅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分开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厚勤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以是,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非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来日诰日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来日诰日然不雅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玄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墨客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宁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洁的人间情意,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见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游手好闲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天下不雅观批驳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轫,以勤扫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因此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写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若而用意宛转深厚,以是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长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样平常墨客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缘故原由就在刚刚分开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创作背景
这组诗写于公元410年(晋安帝义熙六年),当时作者46岁。公元408年(义熙四年)六月,陶渊明隐居上京的旧宅失落火,暂时以船为家。两年后移居浔阳南里(今江西九江城外)之南村落村落舍。《移居二首》当是移居后不久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