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南宋 陈亮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
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云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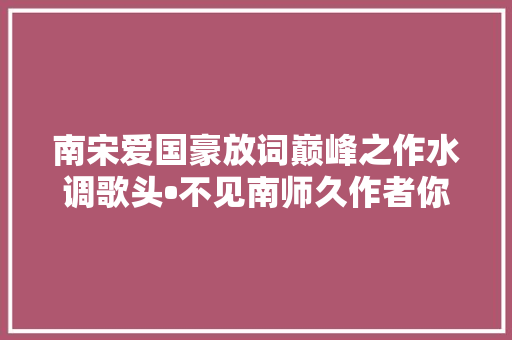
陈亮(字同甫,1143-1194)这位词人,绝大多数读者或许都没听过,但说到他的好朋友,估计没人不知道,那便是大名鼎鼎的词中之龙辛弃疾。稼轩光是为这位好友写的词作就多达七、八首,有一首乃至可以保举为千古豪放词第一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陈亮还是一位思想家,在南宋期间名声非常大,是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见经世致用,这个学派你可能没听过,但是他们有一个对手你肯定听过,那便是主见心性之说的朱熹学派。在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冬,陈亮就约着辛弃疾、朱熹等人,在紫溪(今江西、福建交界处)会面,想要对各自的学说作一磋商,可惜陈、辛二人等了朱熹十来天他也没来,末了就各自散去了。
本日要读的这首词,作于淳熙十二年(1185),此时,宋室南渡已近60年,在第三次宋金制定条约(1164)时双方约定:宋金两国为叔侄之国,宋主称金主为叔父;每年金国天子生日以及每年元旦之时,宋国须遣使朝贺;以及割地赔款等其他条约。自此之后的每一年,南宋出使北方金国的使者,就像洋洋河水东流不尽那般,陆陆续续,相继而来,上一班使者刚回来,下一班使者又要出发,身为南宋爱国文人的作者,必当对这种妥协妥协的现状义愤填膺。在这一年(1185),作者的好友章森(字德茂)又被派往出使北方,以祝贺金主完颜雍生辰(万春节),章森此时任大理少卿,试户部尚书,也是一位爱国文人,与陈亮、辛弃疾等交好,陈亮为给好友壮行,便作下此词勉励对方,并且在词中绝不掩饰笼罩地抒发了两个人共同的报国空想。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开篇便点明当时的南北形势,偏安的南宋朝廷,已经良久没有规复中原的行动了,妥协妥协的太久,甚至于北方的女真人,还以为我们没有人才了。“漫说北群空”化用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中典故“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韩愈文中的意思是,伯乐长于创造好马,只要他一经由河北,河北的好马便都被他发掘出来带走了。陈词中反用此意,以回嘴当时颇为盛行的一种不雅观点,即南宋已无意规复中原了,而南宋的士人们也没有几个再有这种志向了。不过回嘴归回嘴,金国统治者可是一贯这样认为的,以是章德茂此行,就略有一丝悲壮的含义在了,既要屈辱地掩护着一个弱小国家的肃静,又要压制自己心中无限愤慨的爱国志气,想要不辱义务,并不随意马虎。
词人想到此,就立马勉励起朋侪来,“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在出使到金国,并与对方交手的当场,大使只手独撑局势,不卑不亢,昂扬特立,终极彰显了我大宋使者不可屈从的英雄形象。词人能写出这几句,也解释了,当时出使金国的使者中,屈从于对方威慑的,该当不在少数!
“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
”这三句突发议论。可笑我堂堂汉家使者,如今却只能像东流不息的河水那般,奔赴北方。这个“自笑”,有一种十分无奈、无力且自嘲的意思,上两句“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将作者心中的豪壮之情激荡出来,但激荡出来又能如何呢,再威武的使者,再不卑不亢的外交辞令,也不能改变国家妥协弱小的实质呀,英武的汉使个人,对应的却是弱小偷安的国家,作者郁积于心中的“自笑、自嘲还有无奈”,便可想而知了,你都能体会到他咬牙切齿的愤恨之情,以及愤恨之后那种只能捶打自己胸口的苦闷和无奈。
“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前面三句,将屈辱的现实和个人的无奈迸发出来,但作者毕竟是肚量胸襟规复空想的爱国文人,他不能让这种沉沦的气氛霸占自己内心,于是这两句又以豪迈的词句、昂扬的面貌和的雄壮空想,对着朋侪说道:这一次,暂且再去拜一拜吧,但我始终相信,迟早有一天,我大宋军队会规复中原,到那时,我们定要将胡虏的头颅,悬挂于藁街城门之上。穹庐,指北方金国。藁街,西汉期间都城长安城中有一条专门供外国使者居住的街道就叫藁街。《汉书·陈汤传》中记载,匈奴单于郅都,屡犯西汉边庭,后来有一次汉将陈汤在作战中俘虏郅都,便将其带回长安,斩其头颅悬挂于藁街之上,“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词人化用此威武的典故,将自己心中昂扬的空想倾吐而出,表明他认为妥协妥协只是权宜之计,规复中原、统一祖国才是终极的目标。
下阙全用议论,但句句都是豪情万丈,纯挚读一遍便能使人产生豪迈的情怀。“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指被金国盘踞的中原地区,你可以遐想到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时期,我们那些伟大的先民和塑造了我们民族性的先祖,是他们,一贯以来都在黄河流域生生不息,但,繁衍到我们这一代,这先祖躬耕的地方,却沦为胡虏之手。于是词人接下来说,“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在金人盘踞区,该当也会有那么一两个仁人志士,以被金人统治为耻吧。
“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万里腥膻,指中原故土沦为胡虏之手。千古英灵,指尧、舜、禹等古代先贤。这三句假问古代先贤,实问当世之人,尤其针对妥协妥协的主和派。中原中原,已经充斥着金人膻肉酪浆之气,而千古英雄而今安在呢?那激荡千古的浩然正气,何时才能古今相通呢?这三句问话,便将词民气中的抵牾倾泻出来,贰心中的感情是激越的,内心是愤恨不平的,眼下是完备茫然的,而他的灵魂深处,早已被这抵牾的空想和现实,折磨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实在,在金国入主中原后的几十年内,其贵族统治集团已经开始腐败,并且日益骄纵,已经有一些衰败的迹象了。以是词人在末了两句,又回到了昂扬的空想上来,胡人的气数、失落败的命运已经毋须多问了,而我大宋王朝的国运,却犹如这赫赫中天一样平常,我大宋的国运也复兴在望了!
这首词可以有很多种办法的解读,但本日我想说的只有一种,那便是“屈辱的现实和昂扬的空想”!
你可以从这首词中多次读出作者的感情变革,说道大宋朝英武的使者时,说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时,说道“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这些中原英灵时,作者的感情明显是昂扬激烈的;而说道主和派霸占主流时,说道汉家使节被迫朝拜金国天子时,说道中原大地被胡虏盘踞时,作者的感情又明显是愤恨低落的。
你能看出,那些冲动大方的词句,全部都是词人的空想;而那些低落的言语,却都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这种抵牾的状态在词民气中剧烈激荡,他的内心被激荡出了丰沛的情绪,他必须要表达出来,而且,只有那些昂扬的空想才是词人想说的,那些屈辱的现实他根本提都不想提,但是,不提行吗?不提,那些屈辱就不存在了吗?
终极,我们作为词作的欣赏者会创造,词人是想用昂扬的空想来压倒屈辱的现实,但是却步步败给现实。以是整首词写的波澜起伏,抑扬错落,乃至意气飞扬。而这些,都未定议于作者的思想感情,而是那个他永久也无法改变的抵牾现实!
这个空想与现实的“巨大抵牾”才是这首词最最核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