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去国之思,离国之痛。
《卫风·河广》云:“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客居异域,遥望思念自己的家国,情深而无奈。这类诗词在宋朝达到了极致。
北宋壮盛期,版图只有唐朝的1/5至1/3;南宋偏居一隅,再来一个腰斩。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燕然”,苏轼“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云中”,岳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贺兰山”,陆游“僵卧孤村落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轮台”,都不在宋朝版图之中。
陆游“去世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陈亮“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辛弃疾“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去国之思上升为离国之痛,终于到末了成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去世?留取赤心照汗青”的亡国之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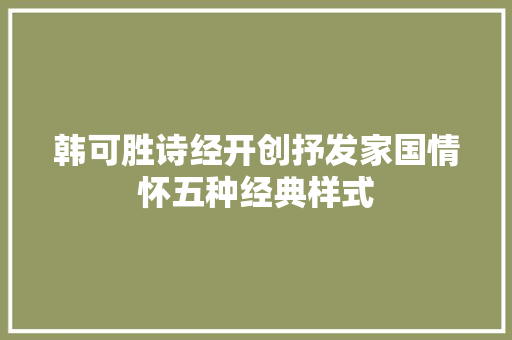
第二类,怀古忧今,盼国复兴。
《王风·黍离》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央摇摇。”远行者经由故都,见宗庙宫室遗址上黍稷离离,内心忧伤不已。这类诗词发展为后来的怀古诗词。个中的不少诗词,不仅仅勾留于怀古,还深藏着对国家复兴的期待。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是曹操期待结束生灵涂炭、规复天下一统的沉思,“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师未捷身先去世,长使英雄泪满襟”是王昌龄、杜甫的深情呼唤,“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刘禹锡、杜牧对历史兴亡的感慨。
第三类,舍家报国,勇往直前。
《秦风·无衣》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发兵,修我戈矛。”对付这首诗歌,曹植的名句“捐躯赴国难,视去世忽如归”堪称最好的概括。这类诗词在唐代边塞诗中达到了高峰。
唐代的边塞诗,题材广阔,意象伟大,基调昂扬,大气磅礴,歌行、绝句、律诗各种文体兼备,堪称唐诗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亦是古诗词中家国情怀的最好表示。
高适“相看白刃血纷纭,去世节从来岂顾勋”、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去世犹闻侠骨喷鼻香”、祖咏“幼年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李白“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卢纶“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李贺“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王翰“醉卧疆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李颀“白日登山望烽火,薄暮饮马傍交河”、严武“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疆场匹马还”……唐代的边塞诗有捐躯的悲壮,却没有屈辱的悲哀。这是大唐的精神,也是值得推崇的家国情怀。
唐代的边塞诗是高峰,但并不是说之后这类诗词就没有了。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一年三百六旬日,多是横戈立时行”、清代将军杨昌浚“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东风姿玉关”,读来依然让人血脉偾张。
第四类,时运不济,忧国忧民。
《小雅·节南山》云:“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无缝承接这一忧国忧民感情的人,当数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传诵千古,绵绵不绝。
之后,唐代大墨客杜甫亦堪称代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豪门酒肉臭,路有冻去世骨”“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如此悲天悯人的情怀,让杜甫成为公认的“诗圣”。
李白与杜甫之高下,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窃以为,就艺术的天才性而言,杜不如李;就思想的深刻性而言,李不如杜。这个思想的深刻性,很大程度上就表示在家国情怀上。
杜甫之后,白居易“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忧民多于忧国。北宋李纲“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明代于谦“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劳出山林”,也值得一记。
第五类,歌颂英雄,安邦定国。
《大雅·皇矣》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这里,歌颂的是周王文治武功、开疆拓土,救民于水火。
汉高祖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是对自己的歌颂;唐太宗李世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是对重臣的歌颂;唐朝诗僧贯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是对吴越王的歌颂。
上述五种类型常常交织在一起,乃至在同一位墨客或同一篇作品中都有交织,使得任何分类都有些顾此失落彼。但不加以条分缕析,又会失落于笼统和混沌。
从“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苟利国家死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埋骨何须故里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东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家国情怀”从来都不但是摄民气魄的文学书写,而更近乎每一个中国民气中的精神归属。
(作者:上海市写作学会常务副会长、上海江东书院创始人 韩可胜)
栏目主编:龚丹韵 笔墨编辑:夏斌 题图来源:IC photo 图片编辑:邵竞
来源:作者:韩可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