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舍
地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以他的对各类学问的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意见意义,以他的对朋友的提携辅导的朴拙,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每逢当我瞥见他的笑脸,握住他的优柔而戴着一个翡翠戒指的手,或听到他滔滔不断的讲说学问或故事的时候,我总会感到他必能活到八九十岁,而且相信若活到八九十岁,他必定还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有说有笑,还能那样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永不驳回朋友的哀求,或给朋友一点尴尬。
地山竟自会去世了——才将快到五十的边儿上吧。
他是我的好友。可是,我对付他的出生知道的并不十分详细。不错,他确是见告过我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可是,大部分都被我忘掉了。一来是我的记性不好;二来是当我初次瞥见他的时候,我就以为“这是个朋友”,不必细问他什么;纵然他原来是个匪贼,我也只看他可爱;我只知道面前是个可爱的人,便是一点也不晓得他的历史,也没有任何关系!况且,我还笃信他会活到八九十岁呢。让他讲那些有趣的故事吧,让他说些对各类学术的心得与研究方法吧;至于他自己的历史,忙什么呢?等他老年的时候再说给我听,也还不迟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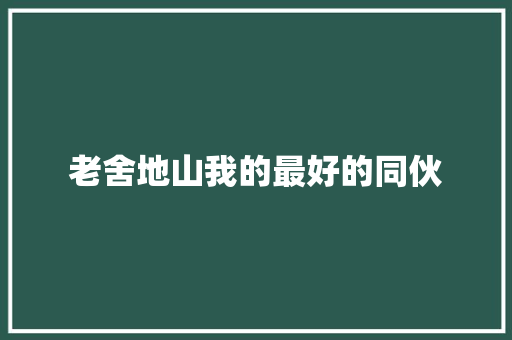
可是,他已经去世了!
我知道他是福建人。他的父亲作过台湾的知府——说不定他就生在台湾。他有一位舅父,是个很有才而后来作了不十分规矩的和尚的。由这位舅父,他大概自幼就靠近了佛说,读过不少的佛经。还许由于这位舅父的关系,他曾在仰光一带住过,给了他不少后来写小说的资料。他的妻早已去世去,留下一个小女孩。他手上的翠戒指便是为纪念他的亡妻的。从英国回到北平,他续了弦。这位太太姓周,我曾在北平和青岛见到过。
以上这一点:事实恐怕还有说得不十分精确的地方,我的记性实在太坏了!记得我到牛津去访他的时候,他见告了我为什么老戴着那个翠戒指;同时,他说了许许多多关于他的舅父的事。是的,清清楚楚的我记得他由陈说这位舅父而谈到禅宗的是非,由于他老人家便是禅宗的和尚。可是,除了这一点,我把好些极有趣的事全忘得一干二净;后悔没把它们都条记下来!
1940年,许地山、周俟松结婚十一周年纪念
我认识地山,是在二十年前了。那时候,我的事情不多,以是常到一个教会去帮忙,作些“社会做事”的事情。地山不但常到那里去,而且有时候住在那里,因此我认识了他。我呢,只是个中学毕业生,什么学识也没有。可是地山在那时候已经在燕大毕业而留校教书,大家都说他是个很有学问的青年。月朔认识他,我险些不敢希望能与他为友,他是有学问的人哪!可是,他有学问而没有架子,他爱谈笑话,村落的雅的都有;他同我去吃八个铜板十只的水饺,一边吃一边说,不一定说什么,但总说得有趣。我不再怕他了。虽然不晓得他有多大的学问,可是的确知道他是个极天真可爱的人了。一来二去,我试着步去问他一些书本上的事;我恐怕他不肯见告我,由于我知道有些学者是有这样脾气的:他可以和你交往,不管你是若何的人;但是一提到学问,他就不肯开口了;不是他不肯把学问白白送给人,便是不屑于与一个没学问的人谈学问——他的神采表示出来,跟你来往已是降格相从,至于学问之事,哈哈……但是,地山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他乐意把他所知道的见告人,正犹如他愿给人讲故事。他不由于我向他请教而轻视我,而且也并不板起面孔表示他有学问。和谈笑话似的,他知道什么便见告我什么,没有自持,没有厌倦,教我佩服他的学识,而仍认他为好友。学问并没有毁坏了他的为人,像那些气焰千丈的“学者”那样。他对我如此,对别人也如此;在认识他的人中,我没有听到过背地里指摘他,说他不足个朋友的。
不错,朋友们也有时候背地里讲究他;谁能没有些毛病呢。可是,地山的毛病只使朋友们又气又笑的那一种,绝无损于他的人格。他不爱写信。你给他十封信,他也未见得答复一次;偶尔回答你一封,也只有几个奇形怪状的字,写在一张随手拾来的破纸上。我管他的字叫作鸡爪体,真是丢脸。这大概是他不愿写信的缘故原由之一吧?另一毛病是不守时候。口头的或书面的关照,何时开会或何时集齐,对他绝不发生浸染。只要他在图书馆中坐下,或和朋侪谈起来,就不用再希望他还能看看钟表。以是,你设若不亲自拉他去赴会就约,那便是你的差错;他是永久不记住时候的。
一九二四年初秋,我到了伦敦,地山已先我数日来到。他是在美国得了硕士学位,再到牛津连续研究他的比较宗传授教化的;还未开学,以是先在伦敦住几天,我和他住在了一处。他正用一本中国小商店里用的粗纸账本写小说。那时节,我对文艺还没发生什么兴趣,以是就没大把稳他写的是哪一篇。几天的工夫,他带着我到城里城外玩耍,把伦敦看了一个大概。地山喜好历史,对宗教有多年的研究,对古生物学有浓厚的兴趣。由他领着逛伦敦,是多么有趣、有益的事呢!同时,他绝对不是“玉轮也是外国的好”的那种留学生。说真的,他有时候过火的厌恶外国人。由于要批驳英国人,他乃至于连英国人有礼貌,守秩序,和什么喝汤不准出响声,都算作为屈曲可笑的事。因此,我一到伦敦,就借着他的眼睛看到那古城的许多瑰宝,也看到它那惨淡的一方面,而不至胡胡涂涂的断定伦敦的玉轮比北平的好了。
不久,他到牛津去入学。暑假寒假中,他必到伦敦来玩几天。“玩”这个字,在这里,用得很妥当,又不很妥当。当他碰着朋友的时候,他就忘了自己:朋友们说若何,他总不驳回。去到东伦敦买黄花木耳,大家作些中国饭吃?好!去逛动物园?好!玩扑克牌?好!他彷佛永久没有忧郁,永久不会说“不”。不过,最好还是请他闲扯。据我所知道的,除各种宗教的研究而外,他还研究人学、民俗学、文学、考古学;他认识古代泉币,能鉴别古画,学过梵文与巴利文。请他闲扯,他就能——举个例说——由男女恋爱扯到中古的禁欲主义,再扯到原始时期的男女关系。他的故事多,书本上的佐证也丰富。他的话一下子低降到贩夫走卒的俗野,一下子高飞到学者的深刻高明。他谈一整天并无倦容,大家听一天也不感疲倦。
不过,你不要让他独自溜出去。他独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院,必是入图书馆。一进去,他就忘了出来。有一次,在上午八九点钟,我在东方学院的图书馆楼上创造了他。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去唤他,他不动。一贯到下午五点,他才出来,还是由于图书馆已到关门的韶光的原故。找到了我,他不住的喊“饿”,是啊,他已经饿了十点钟。在这种时节,“玩”字是用不得的。
牛津不承认他的美国的硕士学位,以是他须花二年的光阴再考硕士。他的论文是《法华经》的先容,在预备这本论文的时候,他还写了一篇相称长的文章,在世界基督教大会(?)上去宣读。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先容玄门。在一样平常的浮浅传教师心里,中国的佛教与玄门不过是与非洲黑人或美洲红人所信的原始宗教差不多。地山这篇文章使他们闻所未闻,而且得到不少宗传授教化学者的夸奖。
他得到牛津的硕士。假若他能连续住二年,他必能得到文学博士——最名誉的学位。论文是不成问题的,他能于很短的期间预备好。但是,他必须再住二年;校规如此,不能变更。他没有住下去的钱,朋友们也不能帮助他。他只好以硕士为满意,而离开英国。
在他离英以前,我已试写小说。我没有一点自傲心,而他又没工夫替我看看。我只能抓着机会给他朗读一两段。听过了几段,他说:“可以,往下写吧!”这,增多了我的勇气。他的文艺见地,在那时候,仿佛是侧重于风格与情调;他自己的作品都多少有些传奇的气息,他所喜好的作品也差不多都是浪漫派的。他的家世,他的在南洋的履历,他的旧文学的教化,他的喜研究学问而又不忍放弃文艺的态度,和他自己的生活办法,我想,大概都使他方向着浪漫主义。
单说:他的生活办法吧。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崇奉,虽然他对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备没有影响。他的言谈举止都像个墨客。假若把“墨客”按照世俗的阐明从他的生活中扩展起来,他就应该有很古怪奇特的行动与行为。但是,他并没作过什么怪事。他明明知道某某人对他不起,或是知道某某人的毛病,他仍旧是一团和气,以朋友相待。他不会发脾气。在他的嘴里,有时候是乱扯一阵,可是他的私生活是很严明的,他既是墨客,又是“俗”人。为了读书,他可以忘了用饭。但一讲到用饭,他却又不惜费钱。他并不孤高自赏。对付衣食住行他都有自己的主见,可是假若别人喜好,他也不便固执己见。他能过很苦的日子。在我初认识他的几年中,他的饭食与衣服都是极大略朴俭。他结婚后,我到北平去看他,他的房屋衣服都相称讲究了。大概是为了家庭间的和美,他不便于坚持己见吧。虽然由破夏布褂子换为整洁的绫罗大衫,他的脱口而出的笑话与戏谑还完备是他,一点也没改。穿什么,吃什么,他仿佛都能随遇而安,无所不可。在这里和在其他的好多地方,他彷佛受佛教的影响较基督教的为多,虽然他是在神学系毕业,而且也常去作星期。他像个禅宗的居士,而绝不能成为一个清教徒。
1938年,许燕吉和父亲许地山
不但亲戚朋友能影响他,便是不相识而有时打仗的人也能临时的旁边他。有一次,我在“家”里,他到伦敦城里去干些什么。日落时,他回来了,进门便笑,而且不住的摸他的刚刚刮过的脸。我莫名其妙。他又笑了一阵。“教理发匠挣去两镑多!”我吃了一惊。那时候,在伦敦理发普通是八个便士,理发带刮脸也不过是一个先令,“怎能花两镑多呢?”原来是理发匠问他什么,他便答应什么,于是用喷鼻香油喷鼻香水洗了头,电气刮了脸,还不得两镑多么?他绝想不起那样打扮自己,但是理发匠的建议是不能驳回的!
自从他到喷鼻香港大学任事,我们没有会过面,也没有通过信;我知道他不喜好写信,以是也就不写给他。抗战后,为了喷鼻香港“文协”分会的事,我不能不写信给他了,仍旧没有复书。可是,我准知道,信虽没有,事情可是必定办了。果真,从分会的报告和朋侪的函件中,我晓得了他是极热心会务的一员。我不能希望他按时回答我的信,可是我笃信他必对分会卖力气,他是个极随便而又极不随便的人,我知道。
我自己没有学问,不能妥切的道出地山在学术上的造诣何如。我只知道,他极用功,读书很多,这就值得钦佩,值得效法。对文艺,我没有什么高明的见地,以是不敢批评地山的作品。但是我晓得,他向来没有争过稿费,或恶意的批评过谁。这一点,不但使他能在喷鼻香港“文协”分会以老大哥的身分德望去推动会务,而且在全国文艺界的联络上也有重大的浸染。
是的,地山的去世是学术界文艺界的綦重大的丢失!至于谈到他与我私人的关系,我只有落泪了;他既是我的“师”,又是我的好友!
啊,地山!你记得给我开的那张“佛学入门必读书”的单子吗?你用功,也希望我用功;可是那张单子上的六十几部书,到如今我一部也没有读啊!
你记得给我打电报,教我到济南车站去接周校长周校长,即许地山的夫人的妹妹。吗?多么有趣的电报啊!知道我不认识她,以是你教她穿了玄色旗袍,而电文是:“日时到站接黑衫女”!当我和妻接到黑衫女的时候,我们都笑得闭不上口啊。朋友,你托友好作一件事,都是那样有风趣啊!啊,昔日的趣事都变成今日的泪源。你怎可以去世呢!
不能再往下写了……
选自老舍《想北平》,公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7月
2019年恰逢老舍师长西席诞辰120周年。本书以公民文学出版社2013版《老舍全集》散文卷为底本, 以老舍生平所到之地为线索,将其不同期间、有关各地的散文集结成集。如其出生地北京、留学地伦敦、任教地济南青岛,抗战期间辗转的武汉、成都、重庆、昆明等地。本书可以作为老舍自传性的随笔,串联起其大半生的紧张生命轨迹。所选篇目既有为广大读者耳熟能详的《想北平》《大明湖之春》等,也有不太常见的《滇行短记》《八方风雨》等。通过这些京味诙谐又饱含深情的笔墨,让读者得以回顾时期的变迁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途经程、更加全面地领略老舍散文的独特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