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 张 妮
编者的话:“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听见太白唱醉的明月,这是杜甫赞过的春雨,王维的空山就在心里……”在为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创作的主题歌中,康震将古典诗词与当代歌词镶嵌在一起,让人们在穿越诗词古韵的同时,得到了时期的感召力量。他见告《环球时报》,“中国古典诗词实际上是缩微版的中华文明演化史,古诗词之以是能不断抖擞新生,是由于它始终都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展现着更为深奥深厚的精神推动力”。
康震在接管《环球时报》专访时坦言,既作研究者又作传播者,实在是一件特殊不随意马虎的事。“首先要持续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平,这是遍及推广的根本,又要以适当的形式将研究成果精准地推向社会大众。古典诗词既要在书斋里涵咏沉潜,又要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进当代人的生活。归根结底,既要尊重古人,也要尊重当代人,让古诗词与新时期共振。”
《长安三万里》实在是一个当代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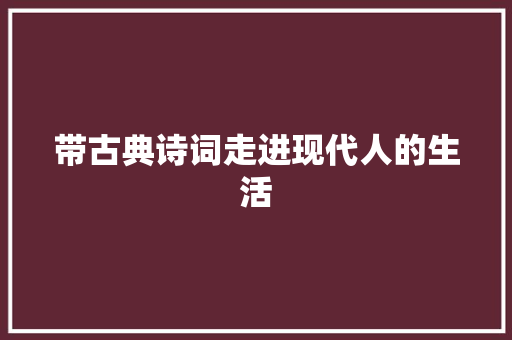
近年来,康震先后担当中心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诗画中国》《朗读者》等节目的鉴赏专家、文学顾问。因在节目中对古诗词独到的见地、精准晓畅的表达、儒雅的气质,收成了一大批传统文化的粉丝。“我参与这些节目的一个最主要目的,便是希望通过当代传播办法,让古典诗词更随意马虎被当代人所理解,使当代人的心跟古代人的心碰撞起来,连接起来,让更多人体会到古诗词之美。”
在康震看来,古典诗词光鲜地表示了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原谅性、和平性。“从《诗经》到现在,古典诗词走过了三千多年的进程,展现了古典诗词、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诗词的类型、主题、内涵、体式、艺术、审美,始终在不断地走向创新拓展,不断地绽放出诗词新蕾。古典诗词的创作者从帝王将相、士农工商,到中外使者、贩夫走卒,无所不有,创作的区域则超过黄河高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原域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至于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期间的诗词创作,则表示了中华文明的统一特性与盛世气候。而古典诗词中强烈的人性主义情怀、和平主义方向,更是不胜列举。”
当然,古典诗词的措辞与内涵,毕竟与当代生活有一定的间隔,须要通过一定的转化才能让当代人更好地理解。因此近年来很多电视节目通过画中有诗、演唱古诗词、场景再现等办法,使人们穿越回历史场景中,回到诗歌创作的故事中,或者以虚拟办法与古墨客进行直接对话。让康震感触最深的是《中国诗词大会》中的“画中有诗”环节。“比如说,我要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可能会先画云,再画一个人坐在那看,然后画水,这些场景在很多诗里都会有,等我把末了关键的一笔画出来之后,大家纷纭猜我画的是哪首诗。这是该节目收视率最高的环节之一,由于它制造了悬念。实际上,猜中还是没猜中并不主要,最主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吸引大家去回顾、调动、检索自己的诗词储备。”
2023年,电影《长安三万里》的热映,为古诗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打开了新办法、新思路。“在我看来,这部电影之以是动听,并不是由于它讲了李白的故事和高适的故事。李白和高适实在是一个人的两面,他们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完全的人。这个人有着少年的浮滑和梦想,同时历经现实的风霜和生活的磨砺,实际上代表了生活的两面。”康震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人的人生感悟和当代人同频共振,发生强烈共鸣,把古代人的诗心跟当代人的存心结合在一起,转换成了一个当代故事,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部电影给我们一个主要启迪:传统文化一定要站在当代的态度去解读,才能古为今用。古诗词要在当代得到新生,就必须让它跟当代人的情绪生活建立紧密联系。”
做研究与做传播彼此促进
康震在大学读书期间师从中国古典文学著名学者霍松林师长西席,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很多人便是由于他在电视节目上的精彩点评爱上了古典诗词。有不雅观众感慨:“不是哪个学者都可以用诙谐风趣的措辞讲出肚子里的学问,还能让别人都听得懂,引起共鸣。”既是学者,又是传播者,是康震的独特之处。两种身份如何兼顾?“作为学者,首先要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学问,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个根本上,才能进行精准的传播,而不是混乱的、缺点的传播。同时,随着传播的不断深入,又会反过来匆匆使你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是一个彼此促进、相辅相成的过程。”
康震认为自己在传播上的上风,得益于他的职业——西席。“无论是在教室上讲课,还是面向社会大众做讲座,老师有一个很主要的任务,便是传授、传播,你要利用深入浅出的办法,让学生、让社会大众真正理解你的所思所想,所学所讲。”他举例称,苏轼写的那首词“一蓑烟雨任平生”,怎么来理解?首先要跟不雅观众讲清楚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处在人生低谷,但通报给我们的却是正能量——不惧风雨,才能迎来生活中的阳光。苏轼之以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很主要的缘故原由便是他敢于面对挫折,并将自己降服挫折的过程通过诗词表达出来。“当你把墨客当时面临的情境变成自己的情境来讲解,把古代的情景还原到当代的场景中,把古人面临的问题和当代人面临的困难和寻衅勾连到一起,才能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古典诗词一贯能永葆青春的一个缘故原由,便是我们现在依然须要它,它能雅化你的生活。当你身处高山上,很自然地就会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你爱上了一个姑娘,依依惜别时,就会想起‘相见时难别亦难’。古典诗词是一个民族情绪的影象,它就像一个小小的U盘,把它插到电脑上打开,就会创造里面的空间非常大。”康震认为,作为学者,要想让古典诗词在当代生活中连续扮演生动的角色、青春的角色、引发情绪的角色,要做的事情有两部分,第一是根本性研究事情,站在古代的态度上对诗的字词句、墨客的创作背景做准确的还原。第二是创造性转化事情,要让这首诗在当代人的情绪生活与人生进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当然,这个事情须要专家学者、威信媒体等社会各界联合起来一起做。”
通过绘画与小读者对话
作为古诗词文化的传播者,康震在实践中创造,给成年人和孩子讲诗,有很大不同。比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对付一个有阅历的成年人来说,他通过这首诗能遐想到自己的发展进程,但孩子理解的可能只是字面意思。“如果面对中小学生,该当把这首诗的基本情形先容清楚,但诗背后的道理不能讲得太过艰深,由于他没有这种体会,就会以为这首诗离自己很迢遥。随着孩子的不断发展,未来会有自己的领悟。”
对付中小学生的诗词教诲,比来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争议。比如,有人认为,孩子该当在理解的根本上背诵诗词。但也有人认为,该当先背诵下来再逐步去理解。对此,康震认为,孩子即便不能理解诗词的含义,也可以前辈行背诵,增加诗词储备。当然,如果能在理解的根本上背诵,效果会更好。对付中小学生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几个要素要搞清楚:第一,墨客写这首诗的时期背景是什么;第二,墨客写这个事物的真实情境、心态是若何的;第三,诗的字词句含义是什么。这些是最主要的。
近年来,康震将很多精力投入青少年诗歌教诲,继几年前出版《康震古诗词81课》后,他最近又推出了新书《康震诗词课(青少版)》。他这样先容二者的差异:《81课》出版后,虽然读者很喜好,但也有家长读者反响书太厚,篇目太多。因此,《康震诗词课(青少版)》从篇幅上减少了很多。选的诗词篇目都来自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在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各阶段都选择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更像一个简约版的中国诗歌选本。“我对这些诗词的解读实际上是在教室解读之外的比较个性化的解读,也是建立在研究根本之上的进一步阐述。如果说学生们在教室长进修这些诗词是1.0版的话,我的《诗词课》可能是1.1版。”
为了让孩子对诗词的理解更加生动、形象,康震还在新书中加入很多自己创作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当你读一首诗的时候,脑海中会浮现出各种各样的场景。我的绘画表达的是自己对这首诗的理解。画面虽然比较形象,但也随意马虎把诗境固化,以是我的绘画只是一种开放性的沟通,至少我跟小读者进行了一次对话,孩子们也可以根据一首诗,画出自己心中的场景,我的画只是起到勾引浸染。”康震认为,诗和画本来便是同一个审美体系中不同的表达,正所谓“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我也希望把诗和画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都展现给小读者,让他们真切体会到中国绘画、诗词内在的紧密联系。”
除了古诗词,最近几年汉服、古风歌曲和舞蹈等也都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在康震看来,这种征象和社会心理反响了一个主要趋势:我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越来越有自傲,我们越来加倍现本民族的文化是中国人走向未来的主要精神支撑和动力。“这也解释,我们的国家和老百姓越来越成熟,只有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水平,一个成熟自傲的民族才会真正把本民族的文化看作安身立命的精神根本。也只有一个富强的国家才能下大力气、大心思去整理自己的文化,弘扬自己的文化,这是一条文化自傲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