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每个时期都有实在际特性,我们现在阅读古人的东西不免会带上今人的态度。只是,阅读强调的是精神共通而非背离,更不是追求一种外在的形式。这是我们在当下读古诗尤其要把稳的。
本日的人读清诗要比清人读苏东坡的诗隔阂更深,只管清人离我们近而离苏东坡远。有人会说这是由于现实物质生活的差异,是由于当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已有极大的不同;有人会说是表述办法的差异,本日的人谁也不再咿咿呀呀之乎者也地抒怀;还有人说是生活改变了我们,生活不同,写进诗里的诗料就不同,总不能把我们所常闻习见的高铁互联网智能AI写进一首七律里吧;抒发的情绪也不一样,北京纽约朝发夕至,保不齐往后人类还到火星上去定居,谁还会“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端人”呢?但这并不是最紧张的缘故原由。如果说新生活改变了诗的样貌,那么这在古代也同样在进行着。比如,苏东坡就曾把秧马等当时的科技发明写进诗里,清人的诗中更是无奇不有,黄遵宪丘逢甲梁启超都有相应的理论主见和创作实践——诗歌本就有这样的功能,它长于把生活的变革纳入个中。而表述办法的差异,更不是关键成分。比如郁达夫写的是口语散文,却不大脱得了旧文人的底子;被称作“中国的中国墨客”的郑愁予,写的也是口语诗。说是情绪的差异也难让人信服。由于古人今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怕相去也不太远。可为什么许多人口口声声表达着“忧郁”“孤寂”,读起“人间几次伤往事” “人事音书漫寂寥”却多少有些无感呢?
我想,在当下读古诗,会被视为“异类”,会涌现难与古人精神相通的困境,更根本的缘故原由还在于时期风潮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仅仅是生活办法、物质条件的改变。我们本日所处的时期与产生那些古诗词的前工业时期完备不同。即便是进行文化产品的消费,我们也很随意马虎被市场细分精准定位,如好莱坞电影不雅观影者、韩剧不雅观众、“跑男”粉丝等等。很多文化产品的生产也多遵照市场的规则,并按流水线的办法成批量地被制造出来,而古诗词那种充满个性化的表达难以被批量制造和生产。这些定位有形无形之中在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心态。故而有人会以为古诗词那种充满个性化的表达已经显得不太合时宜,古诗词的阅读太过小众,并不适宜大众阅读。故而我们哪怕同样在面对被包装成旅游文化产品的江河山川时,更多的是走马不雅观花消费着“山形依旧枕寒流”“三峡星河影动摇”,却难以在心中油然升起“人间几次伤往事”的“人事音书漫寂寥”的怅惘。
古人用诗歌书写的是生命,他们的生命存在与我们当下的生命存在已然相去甚远。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阅读古诗的心情,也阻隔着我们与古人的精神相通,难有“理解之同情”。但我们在当下就不读古诗了吗?我们就读不懂古诗了吗?我想也未尽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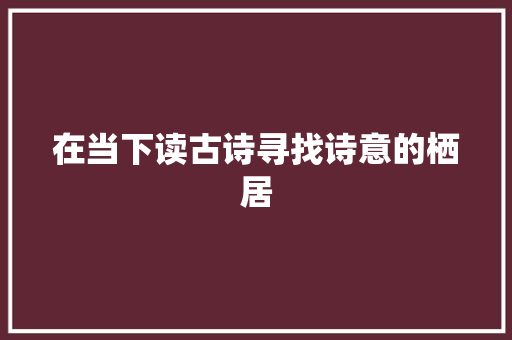
只管从上古的巫、史到明清时期的隐士、绅士,和我们都相隔了光阴的千年、百年,但书写古诗的人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贵族。“为天地立心,为平生易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年夜志壮志,与当下我们的家国情怀并无二致。“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心无彩凤双飞翼”和“当时只道是平凡”,依然能够打动我们为情绪悸动的心灵。以是,我们在当下读古诗,要摒除的是小众心态。无论读古诗词,还是看盛行书,谈时尚电影,都只是个人的文化产品选择。无所谓过期还是时髦,在乎的是喜好和兴趣。而要追求读古诗能够通达领悟,更该当杜绝暴躁心态,沉浸个中领略其间的精神文化本色。
实在,我们与古人都是尘世间的“远行客”,都是一定蹒跚前行的同路人和探索者,都会遇见生命的困顿。我们在为自己的生命探求一个诗意的栖居时,与古人一样,都有着足够的诚挚和十分的期待。而古人造就了这样一个精神的家园,那平平仄仄的声符、草长莺飞的江南、画船听雨的时令,那千树万树梨花开遍的塞外,那响起一声长笛散入满城东风的高楼,那李白杜甫苏轼的月夜,那闪烁着琥珀光芒的醉乡,不便是一个最充满诗意的自由的寓所吗?
真正的诗词爱好者,他们的读诗体验真实而独特,浪漫而美好,在当下读古诗,他们读到的可不但是一个幻梦。愿我们都能抛开偏见,静下心来,在当下读古诗,为自己的灵魂探求到一个诗意的栖居之所。
(作者单位为华侨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