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回车驾言迈,悠(yōu)悠涉长道。
转回车子驾驶向远方,路途迢遥,长途跋涉,难以到达。回:转也。驾:象声词。言:语助词。迈:远行也。一说喻声音悠长。悠悠:远而未至之貌。涉长道:犹言“历长道”。涉,本义是徒步过水;引申之,凡渡水都叫“涉”;再引申之,则不限于涉水。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一起上四野茫茫无边无涯,阵阵东风吹绿百草。茫茫:广大而无边际的样子。这里用以形容“东风摇百草”的客不雅观景象。东风:指东风。百草:新生的草。所遇无端物,焉(yān)得不速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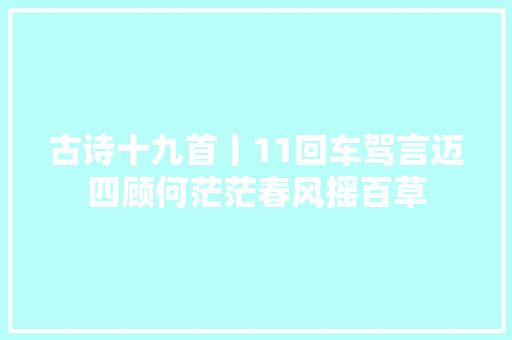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的盛衰各有不同的韶光,只恨建立功名的机会来得太迟。各有时:犹言“各有其时”,是兼指百草和人生而说的。“时”的短长虽各有不同,但在这一定韶光内,有盛必有衰,而且是由盛而衰的。立身:犹言树立生平的奇迹根本。早:指盛时。人生非金石,岂能龟龄考?
人的生命不如金石般坚固,哪里能够永生不老?“人生”句:言生命的薄弱。金,言其坚。石,言其固。寿考:犹言老寿。考,老也。纵然老寿,也有尽期,不能长久下去。奄(yǎn)忽随归天,荣名以为宝。
倏忽之间生命就朽迈去世亡了,只有好的隽誉才是真正的宝藏。奄忽:匆忙也。随归天:犹言“随物而化”,指去世亡。荣名:隽誉。一说指荣禄和声名。【简析】
《回车驾言迈》是《古诗十九首》之一。《古诗十九首》的时期和作者向来是汉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各种不雅观点异彩纷呈。今人一样平常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该在东汉献帝建安之前的几十年间。此诗当为作者因感慨人生苦短而作。
这是一首通过对客不雅观景物兴废更替的描写,来抒发因人生短暂,以是人应“立身”宜早,应以“荣名”为宝的说理诗;同时也是一首抒写仕宦虽有建树但又并不十分得意的士子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励自警的诗。全诗共十二句,可分作两层。前六句为笫一层,写墨客由叙事写景引发出对人生的遐想和感慨;后六句为第二层,写墨客连续抒发自己对人生的议论和感慨。此诗情文并茂,富含哲理,其艺术风格朴实自然,行文如行云流水,但又不浅露,而是余味曲包,耐人寻味。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这两句是说,调转车头我驾着车子开始远行,路途迢遥不知何时才能到达。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这两句是说,举头四顾,但见原野茫茫,东风吹拂摇动着原野上无边的青草。
“所遇无端物,焉得不速老。”这两句是说,一起上我所见的不再是我认识的旧物,不能不使人感到岁月催人老。
首起两句叙事,写墨客要驾车远行。是出门离家游宦,还是衣锦回籍省亲,墨客并没有言说。不过结合全诗来说,诗中的主人公应是游宦京都多年,在功名奇迹上略有建树,虽不是一帆风顺,但也并非完备失落意潦倒。从首起“回车”二字来看,他该当是准备动身离开京师返回自己的故乡。从墨客笔下的描述来看,此时该当是一年中景致最为美好的春天。但现在眼下美好的春光,并没有个墨客带来美好的心情。诗句中一个“何”字,一个“摇”字就模糊地带有沧桑感。紧接着墨客由面远景物引发出对人生的遐想和感慨,一起上,昔日来时的景物都不见了,当然这里的故物,不仅仅局限于物,也应指人,如亲朋古旧。正如曹植诗言:“不睹旧耆老,但见新少年。”“所遇无端物,焉得不速老 ”这两句诗是全诗的纽带,既是对前四句叙事写景发出来的遐想和感慨,又是开启后六句议论感慨的由头所在。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这两句是说,人生和草木的兴盛和衰败都有各自的时限,苦恼的是自己没有很早地建立起自己的功名。
“人生非金石,岂能龟龄考。”这两句是说,人没有像金石那样坚固,怎么能龟龄无尽期?
这两句用来比喻人的生命短暂和短匆匆。
“奄忽随归天。荣名以为宝。”古今注本于荣名有二解。一说荣名即隽誉;有一说荣名则谓荣禄和声名。许多人把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认为前者认为人生易尽,还是珍惜声名为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东西;后者认为人生短暂,不如早取荣禄声名,及时行乐显身。这两种境界有高下之别。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儒家正统知识分子都以搏取功名,建树奇迹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以是不能说追求荣禄和声名,便是庸俗的,就只是为了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正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因此墨客把“荣禄和声名”作为人生之宝,是无可非议的事。从全诗来看,墨客还是负责地对生命进行了思考,立足于追求永恒的隽誉,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对人生的态度还是积极进取的,并以此自警自励。
显然,这是一首哲理性的杂诗,但读来却非但不觉枯索,反感到富于情韵。这一方面固然由于他的思虑贴近生活,自然可亲,与后来玄言诗之过度抽象异趣,由四个层次的思虑中,能感到墨客由抑而扬,由扬又以抑,再抑而再扬的感情节奏变革。另一方面,大概更主要的是,这位墨客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打仗到了诗歌之境主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营构,情景的交融上,达到了古人所未有的新田地。诗的前四句,历来为人们称道,不妨以之与《诗经》中附近的写法作一比较。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央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王风·黍离》是《诗经》的名篇。如果不囿于先儒附会的周大夫宗国之思的教养说,不丢脸出亦为行人所作。以此诗与之比较,虽然由景物起兴而抒内心忧苦的心裁略近,但构景状情的笔法则有异。《王风·黍离》三用叠词“离离”、“靡靡”、“摇摇”,以自然的音声来传达情思,加强气氛,是《诗经》作为上古诗歌的范例的朴素而有效的手腕。而此诗则显得较多匠心的营造。“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迈”、“悠悠”、“茫茫”、“摇”,叠词与单字交叠利用,同样渲染了苍茫凄清的气氛,然而不但音声历落,且由一点——“车”,衍为一线——“长道”,更衍为全体的面——“四顾”旷野。然后再由苍茫旷远之景中落到一物“草”上,一个“摇”字,不仅生动地状现了风动百草之形,且传达了风中春草之神,而细味之,更蕴含了墨客那思神摇荡的心态。比起《黍离》之“中央摇摇”来,此诗之“摇”字已颇具磨炼之功,无怪乎古人评论这个摇字为“初见峥嵘”。这种构景与炼字的进展与前折“所遇”二句的布局上的枢纽浸染,已微逗文人诗的特色。唐皎然《诗式·十九首》云:“《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浸染之功。”(浸染即艺术构思),可称慧眼别具;而此诗,对付读者理解皎然这一诗史论析,正是一个好例。
皎然所说“初见浸染之功”很故意思,这又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之艺术构思尚属于草创阶段。此诗前四句的景象营构与磨炼,实在仍与《黍离》较近,而与后来六朝唐代墨客比较起来,是要大略得多,也自然得多。如陆云《答张博士然》:“行迈越长川,飘摇冒风尘。通波激枉渚,悲风薄丘榛。”心裁亦近,但刻炼愈甚,而流畅不若。如果说《十首诗》是“秀才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那末陆云则显为秀才本色了。由《黍离》到此诗,再到陆云上诗,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演进足迹,而此诗适为中介。以是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说“《十九首》谓之《风》馀,谓之诗母”。
对付人生目的意义之初步的朦胧的哲理思考,对付诗歌之文学实质的初步的朦胧的觉醒。这两个“初步”,大概便是此诗乃至《古诗十九首》整组诗歌,那永久的艺术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