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赵翼有论诗五首,第一首也说“预支五百年诗意,到了千年又觉陈。”虽然史事永久不会变,且诗歌永久受史事的制约而解读空间受限,但是它的解读空间(也即新意)却是始终存在的。这个有限的空间永久都填不满,就像一个瓶子的空间是有限的,往里装石头后它看似满了,但仍能注入砂砾,砂砾注满后,仍能注入净水,纵然净水注满了,水分子之间的空隙仍旧是存在的。我们会瞥见由于时期的进步和个性的不同,诗家们各逞巧思,在极逼仄的咏史空间里大展技艺。如其《论诗五首·其一》云:满眼活气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萧统《昭明文选》将咏史列为一门类,与百一、游仙并束于第二十一卷,自此咏史诗成为古典诗学一大传统,这是咏史诗的源流,在此略作交代。有秦一代,开大一统之先制。虽厥功至伟,然二世而亡。个中的兴衰教训是很有范例意义的,故古来诗家,多着眼于此。秦史之以是成为经典的吟咏题材,与有秦一代朝代兴衰的范例性固然有关,也与他是第一个历史记载颇为完备的朝代有关,这得益于司马迁的《史记》。韶光愈前,记载愈备,后人“众所周知”的事物便越多。共性越多,有利于吟咏引发他人的共鸣。
焚书坑儒为题之咏史兼评咏秦诗的核心史事有许多:焚书坑儒,阿房宫,封五大夫松,沙丘之变、博浪沙等等,限于篇幅,这里只以焚书坑儒与阿房宫二事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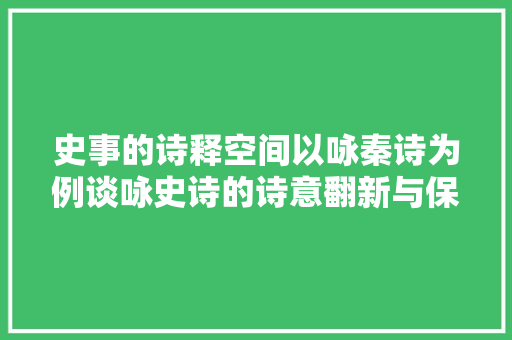
值得把稳的是,焚书与坑儒是两件事情。后人吟咏的大多是“焚书”一事,这里并举紧张是为纠正一个缺点:即“焚书”是一个持续性的、全国性的政策,而“坑儒”只是在咸阳发生的一次事宜,虽然以义近并举,但二者本不相埒。后人有题目为《焚书坑》的便是没有搞清二者的差异,这里聊作阐明。
秦始皇本纪
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示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旬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焚书”的史料,下面的诗歌是对上述同一史料的阐释、发挥、吟咏。
焚书坑(唐·章碣)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
评:这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首咏“焚书”史事的诗,诗思奇特,三四句“未冷”“不”两个判断词下得极得力,反讽意味甚浓。而题目“焚书坑”的问题上文已述,兹不再议。
焚书坑(唐·罗隐)
千载遗踪一窖尘,路傍耕者亦伤神。 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
评:与第一首实在出自同一心裁,无非也是一句秦皇的快意算盘打错了。前两句也凑的很,不能算是佳作。
秦始皇(清·殷葆诚)
六国云亡周社墟,古今坟典悉烧除。 祖龙枉有愚民策,刘项当年不读书。
评:这是清人的作品了,他综合了一下前二作的诗意,捏合成作,险些毫无己见,这样的咏史诗作与不作,有何差异?
读秦纪(宋·萧澥)
筑了连云万里城,东风弦管醉入耳。 悲惨六籍寒灰里,宿得咸阳火一星。
评:这首诗涉及到咏史诗的一个技巧,即联系到其他史料,以诗歌为媒介,联通了两则史料的内质,在打开新的切入视角的同时,使得文本更有张力,议论更加独到和精妙。这首诗题目为《咏秦纪》,四句分咏了四史事,长城—造阿房宫—焚书—楚人纵火,四个史事中切换自若,逻辑严缜。秦皇以为筑造了万里长城,就可以梦想安逸,可是当年焚书的灰烬里,就种了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祸胎了。此作堪称这一技巧的范例利用。再举一个例子:读秦纪(明末清初·陈恭尹):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 夜半桥边呼童子,人间犹有未烧书。这首诗打通了秦皇“焚书坑儒”和张良“圯上受书”两则典故,也颇具巧思,议论独到。与元诗《博浪沙》“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民间铁未销。”出自同一心裁。
阿房宫为题的史诗趋向:讽刺与嗟叹
关于阿房宫也有一件要阐明的事情,便是项羽并没有火烧“阿房宫”,后世可能受司马迁表述不清及杜牧《阿房宫赋》(“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影响,误以为项羽烧的是阿房宫了。《汉书·东方朔传》有“举籍阿城以南,周至以东,宜春以西”的记载,可见直至西汉,“阿宫”还是存在的。
一样平常来说,咏阿房宫的切入点有两条,一是建造阿房宫,意在讽刺,典出如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二是项羽焚宫,意在惜叹,典出如下:项羽引兵西屠咸是,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第七》),我们以历代类题的诗作来看,虽然时有翻新处,但难出于藩篱之外。
以唐人诗为例,胡曾有《 阿房宫》诗云:“新建阿房壁未乾,沛公兵已入长安。 帝王苦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胡曾是晚唐咏史三大家之一,有《咏史诗》150首存世,体系颇备。此作颇为平庸,不过阐述兴衰的一样平常规律,并无新意;又宋人常棠有《秦皇庙》一诗云:“古庙三间矮棘丛,帝魂枉自气凌空。 早知今日立足窄,前此阿房不作宫。”此作由局促的秦皇庙比拟宏伟的阿房宫,讽意全出。
上两例我们很明显的能看出来,唐宋随着“理性与感性”的审美方向,是产生了“讽喻”与“感叹”的立意分野,然唐宋之外,实在他乡墨客对咏史诗的处理也是因循旧制,日本人鸟山芝轩有《秦始皇》诗云:“弃掷皇坟与圣经,漫求仙药究蓬溟。盛称水德真堪笑,不救咸阳火一星。”------这这天人的诗,笔者在《东瀛诗选》里读到时颇为惊异。他贯通了“五德终始说”和“项羽焚宫”两则典故,亦具讽意。个中诗思,似亦为古人所未发。虽然造语俗浅,但一日人能发明此意,颇不随意马虎。
结言
前文已述,咏史诗的写作“还原+生发”的模式,纵览以上诸作,大抵皆是一二句阐述史事(还原)、三四句议论(生发)的固定格式,可知此种行文已成定式。而獭祭众诗,亦可证明咏史空间的生发虽受史料的制约,但有巧思的吟咏总是能在个中找到自己的特定视角,发明新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