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唐代墨客李白的一首即景抒怀诗。
开元二十七年(739),39岁的李白经由扬州宝应(当时叫安宜),瞥见黄鹂吃桑葚,顿感夏天已至,光阴飞逝,久客他乡,一事无成,伤感之下,而有此作。
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在于即景抒怀,移步换景,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浑然天成,用极小的切口,抒发巨大的悲哀,展示出极高的艺术表现力。
“黄鹂啄紫椹,五月鸣桑枝。”首联是说,五月,“我”骑马经由白田这个地方,瞥见黄鹂在啄食紫色的桑葚,听到它们在桑树枝头唱歌。这是写“白田之景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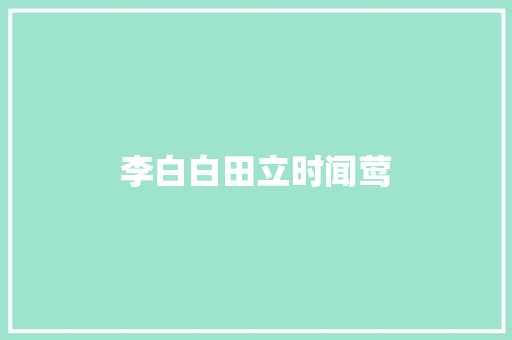
“黄鹂啄紫椹”,一下子就将韶光观点提出来了。紫色的桑葚,代表初夏。黄鹂彷佛在提醒墨客,韶光已经来到了初夏。黄鹂一直地歌唱,仿佛在欢迎夏天的到来。“黄鹂啄紫椹”与“五月鸣桑枝”的两处细节描写,让夏天惊惶失措线到来。一个“啄”字,一个“鸣”字,两个动词,让韶光汩汩流淌,同时也让初夏变得趣兴味盎然,美不胜收。
“我行不记日,误作阳春时。”颔联是说,“我”一起只顾马一直蹄,匆忙赶路,早已忘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初夏已经到来,“我”却误以为还在阳春三月。这是写“白田之所感”。
由于瞥见“黄鹂啄紫椹”,听见黄鹂“五月鸣桑枝”,以是才会感到光阴匆匆,知道自己已经身在初夏了。要不是黄鹂的提醒,墨客还误以为在春天。墨客忙劳碌碌,一直地奔波,求取功名,一眨眼就快四十岁了,仍旧一事无成。墨客对付光阴飞逝的感叹,也是对付青春流逝的惋惜,对付怀才不遇的悲愤。
“蚕老客未归,白田已缫丝。”颈联是说,蚕儿已经老了,游子尚未归来,白田一带都开始缫丝了。这是写“白田之农事”。
初夏是一个收成的时令,蚕儿吐丝,女子缫丝,一片劳碌的景象。蚕儿尚能结茧,农夫尚有收成,可是墨客却一无所获。走在异域的墨客,不禁怀念发迹乡。什么时候才能功成名就,荣归故里呢?在一个收成的时令里,墨客也渴望得到伯乐的赏识,得到朝廷的重用,建立功名,流芳百世。
“驱马又前去,扪心空自悲。”尾联是说,策马奔驰,“我”一刻一直地向前走;光阴飞逝,人到中年,一事无成,手抚胸口,内心的悲哀有谁知道?这是写“白田之所悲”。
可是,前路漫漫,出息未卜,哪里才是归程呢?一直地往前奔忙,真希望得到重用。然而,扪心自问,真的有希望出人头地吗?真正的出路又在何方?“大道如上苍,我独不得出”,或许正是李白当下心悲的紧张缘故原由。
纵览全诗,行文流畅,情绪自然,语境浑然,沉郁悲愤,融万千悲愤于一景,是即景抒怀诗中的绝妙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