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成教诲,诗书礼乐,诗为其始
“诗”字的素心
“诗”字,从言,从之,从寸(手)。“言”是个象形字,像一个人不苟言笑说话的样子。许慎阐明说“直说为言”,便是诚挚不欺之言。“之”者,出也。“寸”者,手也。
“诗,志也。”“志”上面也是个“之”字,下面是个“心”字,意思是由心而生的东西。“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民气感于外物,先藏于心而未发,便是心志;吟诵出来,直言而歌,先吟后书,口言手写所成者便是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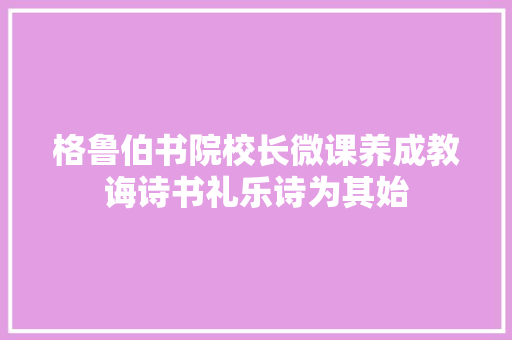
《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大略来说便是:诗是直抒胸臆,歌是把诗的文辞咏唱出来,咏唱出来往后还要以声来“节之”,不让声音乱跑,“律”是声律,末了要用旋律和乐器来调和歌咏之声,使人的歌声与乐音的声音相互和谐,以实现天人相同,万物相合。这句话很伟大,几个字就把诗歌声乐与情绪心志的关系讲清楚了。孔子“兴于诗”、“成于乐”大概便是从这里受到的启示。
“诗”是怎么产生的?
西周以前是神鬼主义,西周开始转向重视人,是人本主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进步,这种进步便是孔子讲的“敬鬼神而远之”:把宗教的崇奉和人性的张扬,结合起来,这样的文化:一方面不是无神论,主见敬神,爱崇崇奉;另一方面,以人为本,张扬个性。两面统一起来叫“自然人文主义”,是中国文化早熟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文学上如何反响出这个伟大的转向呢?便是从“卜辞”到“诗”的进步:“卜辞”是“事鬼之志”,诗歌是“事人之志”。从卜辞通神鬼到“诗言志”,这算是中国文化最早的一次人性,人文启蒙,是从神治到人治,从巫术转变为文学,这在中国人文思想史上有伟大的意义。
随着诗与中国文化的进一步领悟,写诗也成为获取功名的一个路子。唐宋往后,直到明代八股文,八股文,便是八首诗词--“以诗取仕”成了一种时期风气。古典考试,不是宣扬的那样僵化掉队。
读诗四法
一是读,二是诵,三是吟,四是咏。“读”是用声音朗诵出来,用平仄来表现诗歌的情绪思想。诵是在朗诵的时候用字调、节奏、腔调来节制,“以声节之为诵”,“吟”是依字调漫声行腔,“咏”是行腔的声音形成幽美的旋律。吟咏当代人基本不会了,“读”和“诵”还是可以做到的。
作诗三法
一是“格物”:格物便是取物入诗,是中国文学写作的最基本、最大略、也是最高明的方法。
二是“用韵”:每首诗两句对一联,叫对联。用韵有四法:一是平仄相间;二是平仄相对;三是双句押韵;四是前后相粘(请进直播间听取详解)。
三是“用典”:便是利用典故,是推陈出新,借古人来表达。
若何学习写诗?有三法:
一是为难刁难:意思相对、平仄相对。
二是填诗:我们看宋词,有记载的词牌名600多个,个中的名物、平仄、格律全是规定好了的,以是有人说,宋词的作法,便是填,以是作词也称为“填词”。
三是炼字:北宋汴京有个陈舍人,有时得到一部旧本的《杜甫诗集》,读到一首题为《送蔡都尉诗》的诗时,创造“身轻一鸟,枪急万人呼”后面的字没了,想了良久,不知填哪个字。他找来几位朋友研究,有人填“疾”,有人填“度”,有人填“落”,有人“起”,有人填“下”,大家都不能满意。后来,陈舍人在别处又找到原诗,才创造杜甫用的是一个 “过”字,把鸟飞的神态、速率、场景感表达得非常贴切,对杜甫的用字如神的功夫心生敬佩,更加把稳学习杜甫。
诗与当代教诲
孔子说:“兴于诗”,“不学诗,无以言”。教诲小孩子,自己读书,是从读诗开始的。诗是中国文化里非常本真和原始的情道文化之开端。
郭店楚简中的其余一篇儒家类的竹简叫《性自命出》,被认定为孔子的孙子(子思)之作,最核心的四个字便是“道始于情”,情绪是道德的开始,聪慧的开始,理性的开始。诗书礼乐人格养成四教,以诗为始,是养情致性的要法,由情入德的实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