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新韵)
神农辨草点仙葩,建盏铜炉煮雪芽。
一啜余喷鼻香清瞽目,三分新翠饮流霞。
枯肠潜润生诗色,俗气冰消入释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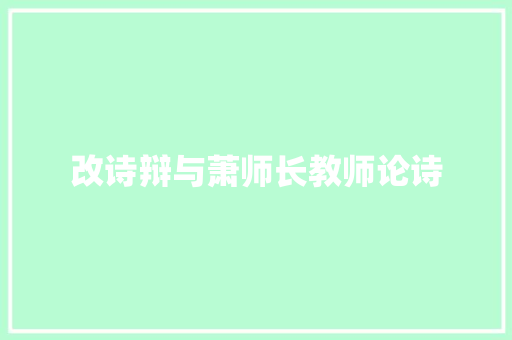
自笑常贫不爱酒,有君何苦弹冯铗。
萧郎评:
此诗借助写茶,表达出安贫乐道的情怀。尤其是引用冯谖弹铗的典故,却反过来说,有茶则不必那样造作(嘿嘿,经由我的启蒙,论者终于知道此诗的中央思想了,不随意马虎。他之前一贯以为冯谖的典故必须是要表达怀才不遇之感。待我遍及了一下语典和事典,引申义和本义之后才有所提高)。构思和立意都较好,只是在对典故的理解和利用上,在遣词造句方面,还有些不敷(此点不提也罢,谁敢说自己很足?)。
从句子上说,起句写神农,并无必要。这不是要列茶史,茶的来源,制作过程,都不是重点(这个见仁见智了,题面是“茶”,而不是品茶,泡茶,不雅观茶,作为咏物诗,如何不犯题面,而又能让人快速知道写的啥,本身便是犹如隔板猜物一样平常,不讲讲由来,一个茶叶有啥好写的?何况律诗起句哀求雄崛,还有啥能比炎黄二帝更高的?昔者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是为茶之起源之一,这样好的书袋不掉可惜了)。重点要归引到自己的心性品质方面,且建盏历史短(建盏虽短确实著名的茶器,象器笺二十曰:宋蔡襄茶录云:“茶色白,宜红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与神农就衔接不足(茶出身黄帝之手,又以宝器烹煮,以显其品位非凡。我一个喝茶的,看到黄帝选的仙葩,第一个觉得不应该是赶紧喝了永生不老么?这衔接还不足?)。首二联第五字,点、煮、清、饮,都是动词,后面接名词词组,因而构成摞眼,显得句法呆滞(就这个算是硬伤,写的时候确实没把稳。)。颔联因对仗不能改,那就须要在一二句中改至少一处(那也该当是清、饮、生、入四个里改俩,方能破此呆板)。考虑到写茶,煮饮这两词,都属于茶事用语,偏直白了,可考虑调换。从茶事来看,除了像普洱之类烂叶子沤的压紧茶要煮,青绿茶多不宜久煮久泡,煮字最宜改(这个是现在的喝法,且不说唐人抹茶法须要加调料,前面提到建盏,就当是宋朝人喝茶吧,在宋朝,“点茶法”成为饮茶办法的主流。宋朝的点茶法是将茶饼烘干、碾碎、磨成末,然后将茶末放在茶碗里,注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即调膏),然后再注入沸水,同时用茶筅搅动,茶末上浮,形成粥面。这咋看咋像煮油茶吧。以是煮字ok)。
颈联单独看,立意尚可。潜算动词,也带一点形容词的性子,与冰的名词对仗不工(这个之前和论者辩过,潜可算副词,否则潜入就都是游进去了。潜伏便是水下闭气,直至憋去世)。释家,是空门了,作者可能还没出家(出毛线的家,茶最初为寺院僧人所喜,由于可以避免念经打盹,又可以清凉消暑,肃清暴戾之气。岂不闻茶圣陆羽都是出身寺庙,也是在寺庙里先打仗到茶的),用的不甚妥当。
尾联是本诗的精华所在,通过与冯谖的比拟,突出茶的浸染,也暗衬出作者的风骨。只是前面短缺铺垫,且对典故的认识不足深刻。冯谖索要鱼、车、家,实在是在作秀,有他深刻的用意。索要鱼吃,是为了与其他门客饮食平等、报酬平等。(此处就摘录一下之前和论者辩论的原文吧:至于你说的这个典故,何必非要执着于冯谖为啥要呢?上升到为啥要就到了这个典故背后引申义了,我实在只须要勾留在字面,让大家联系到他要的啥就行了。而且要精确利用到引申义,必须哀求前面有渲染郁郁不得志的铺垫,否则引用典故便是掉书袋,起不到应由的浸染。显然我并有渲染,便是没有用到引申义的意思。徐晋如老师说典故有语典和事典之分。套用这个说法,如果用弹铗喻怀才不遇便是事典,如果只用他弹铗要吃要喝,便是所谓的语典。)哀求出有车,并不是自己霸占车,而是想要得到礼仪尊重。抱怨无以为家,是为了照顾老母。为啥他不哀求酒啊,美女啊之类的报酬呢?这些属于奢侈享受,不是他追求的。以是此处用酒,就与冯谖的本意不足吻合(你在好看看,原句前面还有自笑,不是堪笑。自笑者,笑自己尔。不要酒,唯己贫尔。这不是老冯不要酒,实诗者自谓尔。否则子非鱼怎知鱼之乐,我非谖怎知谖要酒)。且穷苦而不爱酒,不足为奇,反而正常。穷苦却要爱酒,一样平常都是要被人责怪的(我就强烈责怪陶渊明、李白)。
八句弹字,此处是击打的意思。《康熙字典》列此意在寒韵,举例恰好便是这个典故:“又击也。《史记•孟尝君传》冯驩弹其剑而歌。”弹字此时平声无疑。八句就形成三平尾,乃律诗大忌,出律。(这个吧,咋说呢,我在写之前便是看了汉典,标了两个音,想着人家大概有所本,选了弹字。二者现在也有弹幕一说也是四声,三者单字如果读四声放这里还比较得当。否则换成怨表意也还清楚,声韵就更没问题了。实在个人以为念tán也是正解,下次从大流吧。)
揣测作者的立意,并考虑了上述问题,拟延续总体风格,从茶的清高之气入手,用鹤云风竹等与茶之雅韵融洽的物象相互映衬,用苏东坡、陶渊明这样令人倾慕的高人逸士来提升境界,逐渐铺垫冯谖的干系物象,以较为自然地引到尾联点题。(嘿嘿,靶子来了,准备开枪)
试做修正,供参考:
茶(新韵)
涤烦怡性啜仙葩,建盏铜炉白雪芽。
喜少鱼腥沾鹤袖,欣多春气纳云霞。
竹风常弄东坡影,车马不喧陶令家。
我与冯谖贫一似,有君却可弃长铗。
涤烦怡性啜仙葩
(前面说了起句当雄崛,涤烦怡性此茶之本用,起句就和盘托出,看他后面如何承去)
建盏铜炉白雪芽
(这哥仨放一起是用来展示的么?刚才说煮不好,没有这个动词,三组名词如何串联?)
喜少鱼腥沾鹤袖,
(彷佛去污剂也有此功效。鹤袖?今人谁着此物?此语典用的不好,这也是今人写古诗的一大通病,分开实际。峨冠博带虽然憧憬,本日除了抖音毕业仪式上穿,谁能在生活里穿?况且没有胡子,一个个看上去就和中车府令一样,能好看到哪去?)
欣多春气纳云霞。(欣喜二字不算合掌?颔联二句本应在起句的根本上做一个延伸,或者补充解释,起句写了茶的功效,喝一口“涤烦怡性”,继而摆出来一堆茶具展示,接下去欣喜二句只能阐明看着这些茶具,喝着雪芽很高兴,如饮云霞。)
竹风常弄东坡影,(颈联的功能为转,或由景转情,或由物及人,或感情转为升华。前面写了喝茶,后面这两句多数该当转成喝完之后的觉得。这个竹风弄影就不知道是个啥觉得了?风吹影动,意思喝完之后是醉了立足不稳,还是味道或有或无?而且为啥是东坡影,不是阮籍影?至少他们还喜好往林子里跑了。)
车马不喧陶令家。(这句就转的远了,苏东坡至少还写过几首茶诗,这陶渊明和茶有啥联系,实在恕我孤陋寡闻了。此二句由物及人倒是不错,但所列之人彷佛都与茶关系不大。不知用意何在?)
我与冯谖贫一似,(第一老冯不贫,至少被孟尝君创造往后卖力收税,并且帮着孟尝君狡兔三窟,这样的人那能如我辈一贯贫呢。况且正如论者一贯强调的,用典要理解典故的意思,不论是引申义还是本意,至少从来没人说冯谖弹铗是为了哭穷吧。如此引用就比较个别了)
有君却可弃长铗。(好吧,这句没大改。不过“有”和“却”都是仄声,中间一个“君”,算不算孤平了?就算两仄夹一平是否是孤平有争议,但是至少这样的平仄安排音调不谐是肯定的)
总的来说,该写版是按照自己的思路由物及人,由茶叶想到了高人雅士,可问题是这些高人和茶都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不以品茶有名,张岱彷佛都比老苏在茶界的名气大。这与其说是改写,不如说是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