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除了纪念屈原的说法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存在,比如闻一多师长西席写有专文《端午考》,推论端午是个关于龙的节日,并列出了干系的文籍记载,联系到《说苑.奉使》和《国策.赵策》所记的吴越地区居民的习俗,得出了端午节原来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奠的节日。
还有一种说法因此为端午节起源于恶日。根据是《后汉书》、《论衡》等书中所记载“不举五月子”的内容,并根据孟尝君的卒年早于屈原,来证明以不举五月子为紧张内容的恶日是端午节的始源。
实在不论是图腾祭奠还是恶日传说,所列出的依据都要比纪念屈原的说法更为充分,以是我们再说屈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的时候,如果只说端午节的话,彷佛并不是太得当,毕竟两者的关联性并不是太强。不如说说被称为“以一人之手,创千古之业”的骚体诗。
骚体诗是屈原创立的诗歌文体,也被称为楚辞体,在《汉书.艺文志》中属于“诗赋”一类。这类诗歌一样平常都富于抒怀身分和浪漫气息,篇幅、字句比较长,形式比较自由,在句尾常日带有“兮”字。与之前的诗歌比较,紧张有以下几点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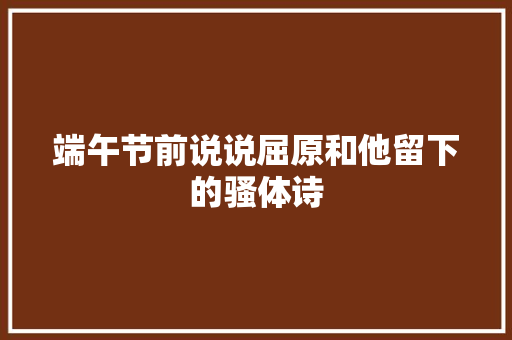
首先“骚体诗”在句式上有很大的打破,在屈原创造出“骚体诗”之前,诗歌的句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这种诗歌我们在《诗经》中常常能够看到。在屈原的早期诗歌中也常常采取这样的四言体,比如《橘诵》便是利用的这种句式。
这种四言体句式,由于容量有限,在表现比较繁芜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情绪时,就难免让人以为有些束缚和局限。屈原后期的“骚体”句式虽然只是比四言句式多了两、三个字,但是全句的容量一下扩大了许多。就像以古人们评价七言长于五言时所说的那样“每句多两字,故迁移转变而不迫匆匆”。
其次在屈原“骚体诗”之前的诗歌,常日都采取分章叠唱、反复咏叹的形式。许多的诗歌都是在每一章中变动几个字,以此来表现场景的推移或者感情的递进。这样的形式虽然便于记唱,但是却使得全诗的容量变小了。
屈原的“骚体”不拘于古诗的章法,如宋人所说,古诗有节有章,而屈原之赋却有节无章。屈原的诗有发轫,有展开,有回环照料,脉理极其分明。可以说屈原的“骚体诗”凭心而言,不遵矩度。
再有屈原的“骚体诗”所表现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感触和心境,他开始要在极其广阔的规模上,展现自己追求空想的进程。当十几句或几十句的篇章无法容纳下他这样繁复的生活内容,和丰富的思想感情时,他便开始创造一种气势恢宏,有着极大容量的长篇系统编制诗歌,比如著名的诗歌《离骚》,长达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九字。
正是由于屈原的勇于创新,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才涌现了这种既差异于先前《诗经》,同时又与后来的五、七言诗所不同的“骚体诗”。就像明人所说“经之后,赋之先,天地间忽出此一种笔墨”,屈原无愧于“以一人之手,创千古之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