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红
学习是做人提高素养与干事提升质效的一个先决条件,且是必不可少的主要条件。毛泽东成为传世伟人、做出劳苦功高的主要先决条件即是他那贯穿生平的勤学不辍卓有成效的广深学习,堪称为学有方、有道。他的为学始终崇尚:既学有字之书又学无字之书。
向书本、历史求教,学思相匆匆毛泽东是善于向书本、历史学习而得法受益最多的典范。他精确的学习不雅观与有效的学习法在个中起了很大浸染。1915年6月25日他在一封《致湘生信》中写道:“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约”,指较主要、关键、喜好的)这一“三先三后”的为学之道,是他生平遵照的学习良方。
毛泽东在纯粹的学习生涯中紧张遵照“先博而后约”自不待言了,纵然走上革命道路后依然如此,根据革命的实际须要去学习。他阅读极广地向浩瀚丰富的书本和历史学习,辩证汲取个中精粹并灵巧运用于革命及治国实践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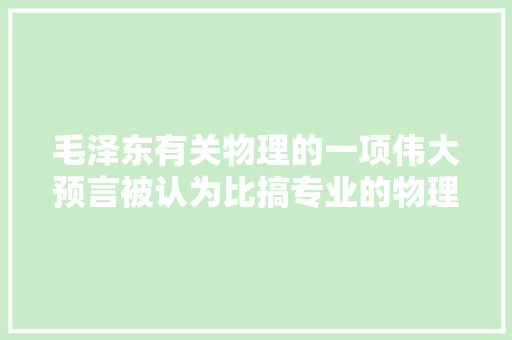
延安期间,毛泽东曾经号召大家:“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节制的知识多。只假如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当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阅读。”他带头学过的书后来辗转带到中南海的就有千余册,如马列理论著作《成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哲学著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社会学大纲》《思想方法论》,自然科学著作《科学大纲》及《鲁迅全集》《战役论》等。这些书是他“先博”之光鲜象征,也是“后约”之详细表示。这还不包括他在京、去外地向当地图书馆借阅的。足见他非同一般的博览群学贯穿生平。“后约”则每个历史期间有所不同:首先是实际须要。如延安发奋读哲学著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带头学政治经济学著作,这是为适应当时斗争实际、社会主义经济培植实际的急迫须要而选择的。其次是他本人最喜好、认为最值得学的。鲁迅著作他兴趣不减、屡学不辍,专门研学了一辈子;《林肯传》《拿破仑传》《戴高乐传》等天下名人传记也是他常学不厌、常学常“新”的。再次是在某门学科上要有所打破,理解得更深一点。一部二十四史他数十年手不释卷不知疲倦学得不亦乐乎。
“先中而后西”方面,他从小到老对中国书本都广泛持久学,在此根本上对西方中译本也学了不少,尤其是对马列著作和西方各国领导人的传记、回顾录或文章、讲(演)及西方各国出版的名家名著;他从延安开始建立藏书室进京后已成规模,但借书仍是获取知识的主要路子。1964年9月9日他在一封信中说:“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个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操心为盼!
”新华社编印的反响西方各国政要的动态、辞吐、不雅观点、文章、讲话、传记、平生等宣布的《参考资料》《动态清样》等内参他险些期期都看,是充分理解认识西方国家政情社情民情等的主要路子。
◆1958年2月,毛泽东在装置车间不雅观看涡轮转子。
“后专门”的事也习认为常。他生平都在尽可能从繁忙事情中挤出韶光学习理解自然科学、工农业生产知识。1958年7月2日,在中南海瀛台参不雅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住所后,就让事情职员找两本参不雅观时看到的书《无线电台是若何事情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来学。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没几天,他便找来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翱翔的普通读物学习。直到逝世前几年视力虽很差了,但还极存心地阅读一些印成大字本的自然科学书刊。
毛泽东一向认为:学史籍可知兴衰;学文学可不雅观世情;学哲学可明是非。他学书本知识特殊是历史,是为了借鉴历史,从中寻求管理国家的聪慧、履历、教训。他学史只管很有个人兴趣身分,但借史明理、借古喻今、古为今用是他学史的常态和目的。他生平都在学研历史中探索真理。
许多问题,理解其来龙去脉,处理起来会有更多思路也更主动有效。毛泽东十分长于从历史中获取灵感,常顺手拈来些史实以解释现实事情中需办理的问题,思考办理这些问题的方法。这多见于他的会议讲话和学史批注中。他读到《史记》说萧何曾经实施“耕三余一”的政策,就思考:那时能做到这点,可能因地多人少,地皮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他在《汉书》里看到汉武帝曾沿汾河乘楼船到闻喜一带,就感慨地说: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
由此附和“引黄济汾”的设想。凡此各类,立足本日把历史学活,思想自然会丰富起来。
1939年5月20日,在中心干部教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驳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宝贵品。对付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本日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役夫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继续这一份宝贵的遗产。这对付辅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主要的帮助的。”1960年12月24日,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他又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科学态度阐明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该充分地利用,批驳地利用。”“我们应该长于进行剖析,应该批驳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驳地加以利用。”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
在1958年11月郑州会媾和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他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学习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等。而且率先垂范学习,即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与陈伯达、邓力群、胡绳、田家英等一起研学这两本书。还亲自安排学习活动,规定每天下午一起学并嘱咐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朗读,边读边议集中学了21天。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不寻思则不能造于道,不寻思而得者,其得易失落。”毛泽东的学习特点光鲜,既学书本又超越书本。他的许多思想理论既源于学过的书又高于书。他不仅广泛汲纳书本知识,而且能交融贯通实践履历,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之以是能这样,最主要的在于他学习不是去世记硬背名目繁多的知识点,而是长于边学习边有效结合实际一直思考,即学思结合、学思相匆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思考中他很长于质疑、看重剖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终都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精华。
勤学善思的毛泽东学史每有心得总爱写批语,这是他边学边思的结晶。他学《南史·韦睿传》,被梁武帝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韦睿的业绩所冲动,在该卷圈点有加,笔墨批注达25处之多,如“躬自调查研究”“不贪财”“劳谦君子”“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等。他有许多经典名言都得益于学史,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备荒思想,就来源于朱升为朱元璋献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略。有名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公民战役思想,直接源自哲学大家王船山的哲学原句。他好学古籍,讲究古为今用。如他发掘“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言简意赅古语重新抖擞出生命力,有的成为我党所遵照的思想,有的成了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
向社会、实践寻问,学甚至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毛泽东历来反对去世学习、读去世书,他反复强调: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是弗成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他倡导带着问题、联系实际向实践、向社会、向公民群众学习。
他总结出一种富有成效的学习方法,苦口婆心地说:“读书是学习,利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主要的学习。从战役学习战役——这是我们的紧张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旧可以学习战役,便是从战役中学习。革命战役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便是学习。”为此,他进一步提出一个马列主义的原则: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精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同样是做社会调查,毛泽东与他批评过的“钦差大臣”不同在:有光鲜态度,有武断明确的出发点,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公民做事,脚踏实地走群众路线,而群众路线也是一种学风。
他讴歌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主见求学要结合社会实际,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正是为了践行开门求学原则,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曾利用假期稽核湖南屯子。北伐战役期间,他于1927年专程赴湖南稽核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人运动,并写出了《湖南农人运动稽核报告》。随后连续做大量社会调查:井冈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调查等,而且他每次到屯子调查都是满腔激情亲切,手写口问。通过调查办理了一系列屯子和农人问题。正是在广泛深入调查屯子的根本上他提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尤其是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作为卓越的军事家,直接和参与指挥的战役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巨、胜利之大,战役履历之丰富,思想之深刻,在古今中外战役史上罕见,这紧张得益于他能从战役实践中学习战役。正是因他亲自经历过战役的胜利与失落败,通过不断学习和总结,坚持学甚至用。他指出:“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等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长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役中学习才能办得到。”一次有人问:“主席,你指挥打仗这么好,从哪里学来军事的?”他笑言:“我在师范上学,当教员出身,哪里学过什么军事?固然有些人经由军事学校学习后再去打仗,但我们红军中更多的人是从战役中学习战役,边打边学习。”他和朱德一起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搪塞仇敌”等一系列游击战术原则。他针对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少数左倾分子对他的诋毁与谬见,驳斥说:“是的,我不睬解他们那种蠢猪式的打仗方法;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时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也看过不少关于外国战役的书,但我的军事知识紧张是从战役实践中得来的。”他1936年研学而著的《中国革命战役的计策问题》,便是他经历数次反“围剿”和长征而对红军在十年地皮革命战役中的战斗进程和履历教训之“决斗苦战史履历”的高度总结,提出了一系列主要计策创见。
当然他强调战役实践主要性时,并不否认学习古人军道理论和间接履历的必要性。他指出:“统统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道理论,都是古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役履历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役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该当着重地学习它。”但这些从战役实践中总结出的间接履历,只有同自己的战役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转化为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心党校的开学仪式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谈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时曾谆谆告诫:“我们党校的同道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去世的教条。对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运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如果你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雅观点,解释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夸奖,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解释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利用”,这是他倡导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也是他身体力行、一向遵照的研学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义。在全面抗战到来之初的紧迫形势下,他决心沉下心来结合中国革命实情研究点学问。延安期间堪称他学哲学、研马列的高峰。1937年8月同郭化若发言时说得很明白:“抗日战役有许多新情形、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弗成。”1938年1月他给艾思奇写信说:“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面前几天。”为研究哲学他在1938年和1939年曾先后组织过3种形式的哲学谈论小组,每周旁边谈论一次。他私下的学习也一刻未放松。对1939年5月艾思奇编辑出版的约37万多字的《哲学选辑》十分重视地负责学了三遍,并在学习中结合中国革命现状针对性地深入思考,得到聪慧、寻求办理问题的“钥匙”,他动笔将思考的精华分别用黑铅笔、羊毫和红蓝铅笔作批注和圈画,写了3200多字的批语。为学习军事问题,还专门组织萧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等人组成关于克劳塞维茨的《战役论》研究会。边读边议每周谈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谈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每次谈论他除插话外总在末了揭橥自己的意见,环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谈得较多。
丰富深入的学习使其理论思维和理论创造非常生动而先后催生了《抗日游击战役的计策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论著,且学研的最大收成是确立了他此后看待实践、剖析问题的两最根本的理论思维“工具”:实事求是、对立统一。为系统总结中国革命履历以辅导其连续提高并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缺点,他以特大激情亲切与精力广泛网络并阅读各种马列著作。在延安他结合丰富的革命实践真学真用,创造性地撰写了《抵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籍。
1964年8月25日,毛泽东曾对一个外国青年学生代表团说道:“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诲我们若何革命,但是也不即是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施革命又是一件事情。”这是他的履历之谈。的确,在“实施革命”的风云岁月,他始终把学习视为根据实践须要获取思想资源的主要路子。
向科学家、学者请教,举一反三除了人文社会科学,毛泽东还曾广泛阅读科学技能方面的知识,也提出过许多深刻的推动中国科学技能发展的计策思想。同时他特殊尊重、爱护科学家,与他们结下深厚友情;他们对他充满敬意,对他充满哲理的科学预见十分重视。
1951年,毛泽东同周世钊等人说:我想学自然科学,最好有两三年的韶光来专门读,可惜现在不现实了。虽不能专门去学但一有韶光尽可能阅读自然科技书本。1958年在《事情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专门讲:“提出技能革命,便是要大家学技能,学科学”,“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能,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1955年1月15日,他在中南海调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开中心布告处扩大会议,地质部部长、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参会,专门谈论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奇迹。他主持会议并开宗明义说:“本日,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全体会议经由大家切磋,末了毛泽东果断拍板“中国自己研制原子弹而重点打破国防尖端技能”。
◆1951年,毛泽东和钱三强在庆祝七一酒会上。
决策原子弹研制后毛泽东仍兴头很高,溘然话锋一变,转而以哲学家的思辩同钱三强谈论起原子的内部构造问题,留下一段载入史册的精彩对话。毛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吗?”钱答:“是这样。”毛问:“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一时答不出。会前只管曾有所准备但毛泽东所提从未有人研究过也未有人提出过。数分钟后钱严谨实答:“这个问题还没有新的认识。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便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问:“它们是不可分的吗?”钱答:“现在的研究,是这样。能不能分,还没有被认识。”毛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不雅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该当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
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见大家未表态,他笑言:“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这是一项伟大的预言。往后的事实证明它惊人准确!
半年后,美国第一次创造了反质子;一年后,又创造了反中子,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对此,有科学家说,毛泽东比我们这些搞专业的物理学家还行!
1964年物理学家创造了基本粒子“夸克”时,一向很关注基本粒子研究的毛泽东谈及时还引证《庄子》一书《天下》篇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解释“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这一哲学论断。
毛泽东哀求全党干部研讨农业,学农业科学技能,努力把中国农业生产提高到当代化水平。他带头深入屯子,钻农业科学技能,提出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他哀求把稳抓“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等环节,使农业生产科学化。到1962年他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全体干部都要研究农业:“拿我来说,经济培植事情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睬解。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付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舆解,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舆解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器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随后,他还不失落机遇地向科学家请教要修正“八字宪法”,加上“气”和“光”(景象和日光)。
1963年1月竺可桢出席中科院党组扩大会阐述科研事情如何增援农业生产的见地后,8月利用休假撰文《论我国景象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论述了增加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并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详细建议。毛泽东在国家科委内刊上看后激动不已,便于1964年2月6日约见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纵情论谈。他毫无拘束地向他们理解谈论了一些科学问题,揭橥了自己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见地,讲了在科学技能发展中抵牾斗争推动事物提高的道理。他热心希望他们为占领科学技能尖端、赶超天下前辈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他对竺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
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填补了‘八字宪法’的不敷。”竺答:“天故意外风云,不大好管呢!
”毛说:“我们两个人分工互助,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
◆1965年1月,毛泽东与李四光握手交谈。
参加这次约谈的李四光回顾说:“主席知识渊博,通达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形,对冰川、景象等科学问题,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寝室里,乃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本,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夸夸其言。”毛泽东亲切地称李四光为“李四老”并曾邀到中南海怀仁堂一起不雅观看豫剧《朝阳沟》。1952年他看李四光关于石油地质的报告后不懂个中的“山字型”布局,一次会议上碰面了便谦逊地开门见山请教。1969年5月19日,二人单独发言,话题涉及宇宙数亿万年间的事情即天体、地球及生命起源等,在谈到太阳系起源问题时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还说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望其找几本书给他,并请帮他网络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李四光问:“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毛泽东随即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后来,李四光就把自己写的《地质力学概论》《地质事情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等及老地理学家章鸿钊的著作《石雅》一并呈送给毛泽东。为省毛泽东的韶光精力,李四光极仔细整理出一份资料,个中领悟了地质学说中各种学派的不雅观点及自己的评论,在此根本上持续写了7本书且每写完一本便叫秘书立时送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亲自校正后呈送给毛泽东。
由此足见毛泽东对各种学科的学习中有着多么深度广阔的举一反三、交融贯通本领!
毛泽东曾在所写著名诗词中感叹:“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既是对自己的严格自律警示,也是对大众的鞭策勉励。一方面,他的学习是发自内心对知识、对思考、对思想的一种渴望,因其主动与渴望,他才有一种真学精神,才能实实在在“不需扬鞭自奋蹄”而争分夺秒高效学习;另一方面,只管人的惰性与生俱来,但他总勇于向自身
1939年5月20日,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诲动员大会上向全党哀求: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仇敌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知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知足便是我们学习的最大顽敌,本日开会后要把它战胜下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依赖学习不断发展壮大。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办理“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的本领惶恐症。为此毛泽东强调: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学习,建立学习制度。中共中心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诲部,统一领导学习运动。在陕北,党创办了中心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30多所学校来培养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他与刘少奇等中心领导亲自给学员上课。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艺讲课。
他谆谆教导:“一故意志,万事皆成。我劝同道们也和我一道学习。事务太多,韶光不敷,然亦可以挤一点。养成学的习气,就能学下去。”他捉住精髓,强调“学习一定要学到底”。表现有三点:一是端正学习态度,要靠“挤”和“钻”,事情忙和看不懂都是不好学的借口。延安学习运动时中心哀求各级干部每天须挤出两小时学习。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指出: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道不下苦功,有些同道把事情以外的剩余精力紧张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舞蹈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该把事情以外的剩余精力紧张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气。各级干部一星期必须挤两个半天,有操持地读书学习。二是学习内容要只管即便“学到底”。他认为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统统也是书即“无字天书”。统统民族、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能、文学、艺术的统统真恰好的东西都要学。读无字的书就要在实践中学,特殊要在群众实践中学。三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延安期间常有领导干部以年纪大为由,认为学习没希望。他认为这种想法严重不对,“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真正的学问是要在“无期大学”里点滴积累起来的。为此,“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同道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入这个大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好多革命年代发展起来的领导干部年事已高。纵然这样他还强调要有办法勾引高中级干部学习,推广到党政军民学。看不清了可以印大字版的书。以上三点,他身上的动听事例不胜列举,直到临终前他也未放弃对书本的钟爱和对学习的坚持,临终前一天的5时50分在全身布满多种抢救东西的情形下还读了7分钟的书,在书喷鼻香中离世,可谓活到老、学到去世,令人无比动容,他以身作则无可辩驳地为全党做出了“将学习进行到底”的榜样!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
转载请联系《党史博采》
侵权必究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党史博采微信"大众号:dangshiboc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