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郑绩(1813-1874年),字纪常,号戆士,别署梦喷鼻香园叟,广东新会双水区桥美村落人。自少攻读四书五经,多才善辨, 能书工诗,擅绘画兼习医术。年青时期,屡试不第,遂绝意仕途, 另谋出路。初业医,后放弃,转而以卖字画为生。四处泛游, 受到书坛画苑有名人士赏识,名声大噪。上自官吏,下至平民, 遇有喜庆屏寿幛,以得他的字画为荣。因而所到之处,前来求字画的人,常挤满屋舍;而投赠报酬的钱银肉食,不可胜数。但是,他生性任侠,重义轻财,乐善好施,周济穷苦,以至家徒壁立,家无积储。中年, 又放弃卖字画生涯,转而经营盐业。因他操纵有术,进出居奇, 不半载便获大利。贩盐三十余年,全无拖欠应缴的盐饷,而自己盈利亦很可不雅观。
咸丰七年(1857年),湖北省为筹军饷, 来广东招人捐官(官衔),无人相应。郑闻知此事,认为子民百姓受国家君主恩德, 如今版图有警,怎能坐视?于是,暗中变卖家产,捐输千金以为倡导。同治五年(1866年)秋,大水因广州,积水难退,居民受害, 当局计议疏通“六脉渠”下水道,苦于用度无着落,迟迟未能动工。 郑知悉后,慨然带头出资千金,并亲自肩担浚渠工程,打消水患。 同治八年,官方多次行文追征连阳地方“十万逋课”(即十万元欠税),有关人士束手无策。郑出于同情心,动用他的关系和影响力, 四处张罗,飞函求援,不旬日遂解连阳的困难。
新会县衙的差役向来横行霸道, 城乡名流亦不敢和他们抗争。有郑氏族妇和堂嫂口角忿而自尽,知县令查访案情,以便办理。 而差役借机打单,拆毁本家儿临近房屋数间,把用具衣服抢夺一空。 郑闻知,率本家儿家人赴县鸣冤。知县方不雅观海闻知,大为年夜怒, 查讯属实,重办了这郡差役,令归还所抢的财物,罚赔修屋银300两。从此,县役的凶威稍敛。同治九年(1870年),乡邻有莫、 郑两姓械斗,各聚千人,炮火鏖战七昼夜,去世十余,伤以百计。 县官武弃无能制止,便到广州请郑还乡排解。他亲到械斗场所, 在双方炮火互射的空间,昂然年夜方陈词,说以短长,令众感悟,即日缴械罢斗, 相与和好,官民齐称其为“一代之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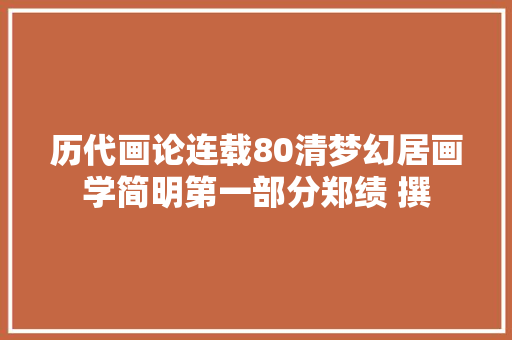
晚年,他隐居广州越秀山南麓自营的别墅,园曰梦喷鼻香, 居曰梦幻楼、梦寄。
遗迹有:新会杜阮叱石岩下石壁上有其擘窠大书“一洗尘凡”四字:双水藏有他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绘的《金钱图》, 图中有寓意深刻的题词。
郑绩著有《论画》2卷、《梦幻居画学简明》、《梦喷鼻香园剩草》等。今新会博物馆藏有他于同治年间画的《山水人物图》、 《晚汀渔竿图》。
◆梦幻居画学简明 (清)郑绩 撰
●梦幻居画学简明卷一
山水总论
夫为学之道,自外而入者,见闻之学,非己有也;自内而出者,心性之学,乃实得也。善学者重其内,以轻其外,务心性而次见闻,庶学得其本,而知其要矣。故凡有所见闻也,必因其然,而求以是然,执其端而扩充之,乃为己有。苟以见闻取捷一时,究之于心,罔然未达,诚非己有也。因思画虽小技,当究用笔用墨,炼形炼意,得气得神,方是学心,岂可专事临摹,苟且自安,而竟诩诩称能哉!
学山水固当体认家法,而形像尤须讲求。今人多忽略于形象,故画焉而不解为何物,岂复成为绘事耶!
盖画必先审夫石与山与树之形,其间阴阳向背、远近高低、气脉连系、宾主朝拱,逐一分清,而后别之以家法皴法,究之于笔,运之于气,由是春融夏翳、秋肃冬严,烟朝月夜、雨雪风云,可随手而生腕下矣。是形象乃为画学入门之规矩也,焉能忽之。
画之形如字之文,写字未知某点某画为某字,又何足与论锺、王、颜、柳、欧、赵、苏、黄之家法、笔法耶!
或云画不求工,意不图形,又贵会写不会写之间,或似不似之际,庶脱画匠。虽然,此是道成后语,从有法归无法,如精楷后作草书耳。学者若执斯论,为入门工夫,则生平贻误,到老无成道之日矣。
述古
王摩诘曰: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模糊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此是诀也,山腰云塞,石壁泉塞,楼台树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两头,树看顶额,水看风脚,此是法也。凡画山水,平夷顶尖者巅,峭峻相连者岭,有穴者岫,绝壁者崖,悬石者岩,形圆者峦,路通者川。两山夹道,名为壑也;两山夹水,名为涧也。似岭而高者名为陵,纵目而平者名为坂,此则山水之仿佛也。不雅观者先不雅观气候,从辨清浊,定宾主之朝揖,列群峰之气候,多则乱,少则慢。不多不少,要分远近,远山不得连近山,远水不得连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断岸坂堤,小桥可置。有路处则林木,岸绝处则古渡,水断处则烟树,水阔处则征帆,林密处则居舍。临崖古木,根断而缠藤;临流石岸,欹奇而水痕。凡画林木,远者疏平,近者高密,有叶者枝嫩柔,无叶者枝硬劲。松皮如鳞,柏皮缠身,生土上者,根长而茎直;生石上者,拳曲而伶仃。古木节多而半去世,寒林伏雏而萧岑。有雨不分天地、不辨东西;有风无雨,只看树枝。有雨无风,树头低压,行人伞笠,渔父蓑衣。雨霁则云收天碧,薄雾霏微,山添翠润,日近斜晖。早景则千山欲晓,雾霭微微,朦胧残月,气色晕厥;晚景则山衔红日,帆卷江渚,路行人急,半掩柴扉。春景则雾锁烟笼,长烟引素,水如蓝染,山色渐青;夏景则古木蔽天,绿水无波,穿云瀑布,近水幽亭;秋天景色则水如天色,族族幽林,鸿雁秋水,芦鸟沙汀;冬景则借地为雪,樵者负薪,渔舟倚岸,水浅沙平。凡画山水,须按四季,或谓烟笼雾锁,或谓楚岫云归,或谓秋日晓霁,或谓古冢断碑,或谓洞庭春色,或谓路荒人迷。如此之类,谓之画题。山头不得一样,树头不得一样平常,山藉树而为衣,树藉山而为骨。树不可繁,要见山之奇丽;山不可乱,须显树之精神。能如此者,可谓名手之画山水也。(苑画)
论形
土水不分,花木时时,屋小人大,人大船小;或人高于树,树高于山;桥脚吊离,远近不能登岸;屋墙斜歪,构造不合丁方,此皆有形之病,浅白易见,可指而言也。气候俱泯,物象乖离,笔墨虽工,支配鄙俗,描摹虽似,品类无神,此无形之病,可以融会,难以言喻也。
山石之形,或先定轮廓后加皴;或连廓带皴,一气浑成;或先皴而后包廓,思某皴某廓,用某家笔法墨法,胸有成见,然后落笔。夫轮廓与皴,原非两端,轮廓者皴中之大凹凸,皴者轮廓中之小凹凸,虽大小不同,而为山石之凹凸则一也。故皴要与轮廓浑融相接,像天生自然纹理,方入化机。若轮廓自轮廓,皴自皴,一味呆叠呆擦,便是匠手。山石交搭,不可层层顺叠,皴法不可笔笔顺落。轮廓起伏,要无定形;皴擦向背,当详细变。
凡山石结顶二笔,乃是等分前后笔也。盖此边见者是前,那边不见者即是后。因此山后有山,须自结顶处想至其后,复从其后计至彼前。应到某处起,方能再叠,故笔要分开,墨须空淡,乃合自然之理。若山后之山,忽自此山结顶等分处连叠而起,则前山之后,与后山之前,两相逼塞,是两山俱得半边,成大笑话,可不察欤!
十六家皴法,即十六样山石之名也。天生如是之山石,然后古人创出如是皴法,如披麻,即有披麻之山石;如斧劈,即有斧劈之山石。譬诸花卉中之芍药、牡丹,梅、兰、竹、菊,翎羽中之鸾凤、孔雀,燕、鹤、鸠、鹂。天生成样子容貌,因物呼名,并非古人率意杜撰、游戏笔墨也。
学写山石,必多游大山,征采生石,按开求法,触目会心,庶识古人立法不苟。更毋拘法失落形,画虎类犬,乃至犬亦不成,不知何物,斯不敷与语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学贵心得。
论忌
饶自然所云十二忌者,皆为形像而言也。一曰支配迫塞,二曰远近不分,三曰山无气脉,四曰水无源流,五曰境无夷险,六曰路无出入,七曰石只一壁,八曰树少四枝,九曰人物伛偻,十曰楼阁错杂,十一曰浓淡失落宜,十二曰点染无法。
支配迫塞者,全幅逼翳,不能推宕。凡布景要明虚实,虚实在乎生变。生变之诀,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八字尽之矣。以一幅而论,如一处聚密,必间一处放疏,以舒其气,此虚实相生法也。至其密处有疏,如山石树屋,凡召盘处,须避疏留眼,毋相逼撞是也。疏处有密,如海阔则藏以波涛舟楫,天空则接以飞鸟云烟是也。此实中虚,虚中实也。明乎此,庶免迫塞之忌。
远近不分者,远与近相连,近与远无异也。夫近须浓,远须澹;浓当详,澹宜略。惟其略也,故远山无纹,远树无枝,远人无目,远水无波;以其详也,故山隙石凹,人物男子,枝叶波纹,瓦鳞几席,井然可数。而由近至远,由远而至至远,则微茫仿佛,难言其妙,宜望真景,以法取之,个中深意在目中,斯在图中矣。
山无气脉者,所谓噜苏乱叠也。凡山皆有气脉相贯,层层而出,即耸高跌低,闪左摆右,皆有余气,连系照料,非多览真山,不能会其意也。若写无气脉之山,不独此山,固为乱砌,即通幅章法,亦是乱布耳。无气脉当为画学第一病。
水无源流者,无源头出处也。夫石底坡脚,有清流激湍,其上要有长泉涓涓而下,方为有源之水,此理易知。然两山之间,夹流飞瀑,上须高山,乃有出处,此理人多失落察。盖必有高山,其下方有积润,水乃山之积润而成也。况本山特耸,泉宜脚出,若泉向高山之顶而来,顶之上又无再高之山,则水之来也,岂非从天而下耶!
孤峰挂瀑,譬诸架上悬巾者,此之谓也。
境无夷队,盖古人布境,有巉岩崒〈山律〉者,有深翳弯曲者,有平远空旷者,有层层重叠者,其境不一。每图中虽极平淡,其间必有一变险阻处,令人意想不到,乃人化境也。
路无出入者,塞断不通也。水隔宜接以桥梁,石遮当留以空淡,或旋环屋畔,或掩映林间,似断非断,不连而连。前有去,后有来,斯之谓有出入。
石只一壁,一壁之石,便成石板矣。又云,分三面者,正一壁,旁边二面也。然此言其概耳,必将皴法交搭多面,以成崚嶒,凹中凸,凸中凹,推三面之法,而作十面八面,亦无不可。且旁边圆转运化,向背阴阳,不露笔画痕迹,如出天然;无寻落笔处,方得石之体貌也。
树少四枝,四枝者,前后旁边四便之枝,非四条树枝之谓也。近必写树,只从旁边出枝,前无掩身,后无护体,纵有千枝万枝,不过两便之枝,是即少四枝矣。必知此忌,而后枝干有交搭处,且四便玲珑,穿插掩护,则虽三枝两枝,亦见不尽之意,奚必定要四枝哉?
人物伛偻者,驼背缩颈,无轩昂高雅气候也。然不但此也,盖山水中安置人物处,为通幅之主脑。山石林屋,皆相顾盼,岂徒人象人,物似物已哉!
古人之清如鹤、飘若仙,以此亦就写人物一端而言。至随处点景,宜俯宜仰,当坐当立,仍须与山林亭宇相照料。庶得山水中人物一定不易之法,当以此忌于伛偻之外也。
楼阁错杂者,间架层叠,安置失落宜也。凡一图之中,楼阁亭宇,乃山水之眉目也,当在开面处安置。盖眉目应在前而安在后,应在右而安在左,则非其类矣。因此画楼阁屋宇,必因通幅形势穿插,斜正高低,或露或掩,审顾停当妥善,与夫间架之周遭曲直,不相拗撞,乃为合式。
浓淡失落宜,不独近浓远淡已也。盖山石必有阴阳,有阴阳则有明晦,有明晦则有浓淡矣。更有渲淡接气,以补意到笔未到之处。故或无或有,如烟如云,生动活泼之机,全向墨中浓淡奇妙而出。浓淡得宜,则通幅生动;浓淡失落宜,则全图去世煞。学者最宜把稳也。
点染无法,夫画成用色,如锦上添花,庖中调味,得其法则粗恶亦艳而甘,不得法虽富丽反成劣坏。故点染合宜,如春宜润,夏宜深,秋宜淡,冬宜黯。又如绿中点衬以红,浓中渲染以淡,非止一端。即此之类,在人灵变,不能指一而概也。
论笔
形像固分宾主,而用笔亦有宾主。特出为主,旁接为宾。宾宜轻,主宜重;主须严谨,宾要悠扬,两相亲睦,勿相拗抗也。
山水形像既熟,能于笔意有会处,则当纵其笔力,赌气魄雄厚,有吞河岳之势,方脱匠习。
用笔贵不动指,以运腕引气。盖指一动则腕松,而弗能引丹田之气矣。因此有轻跳暴躁之弊,可知有力由于有气,有气由于能运腕。欲能运腕,则不动指是为窍门。作书固然,作画亦然也。
用笔以中锋沉著为贵,中锋取其圆也,沉著取其定也。定则不轻浮,圆则无圭角。所谓活泼者,乃静中发动,意到神行之谓耳。岂轻滑暴躁,笔不入纸者哉!
若体认不真,则趋向大错,学者当细参穷究,以归正学。
山水用笔,最忌平匀,如结笔而通幅皆结,放笔而通幅皆放,如是之谓平匀也。盖结必须放,放必要收,故于著眼主脑处构思工致,此是结也。而于四边衬映,不离不即,此是放也。于景外天空海阔处,必用远山关锁全局,此是放而收也。总之有起有收,有实有虚,有分有合,一副之布局固然,一笔之利用亦然。
如初下一笔结实,须放松几笔,以消一笔之余气,然后再叠第二笔。如此,笔气庶免逼匆匆,乃得生动,随意著手,便有虚实矣。不然,则神困气去世,虽有铁铸笔力,叠实不化,从成板煞,何足贵哉!
恐怕涩,熟怕局,漫防滞,急防脱。细忌稚弱,粗忌鄙俗,软避奄奄,劲避恶恶。此用笔之鬼关也,临池不可不醒。
笔动能静,气放而收;笔静能动,气收而放。此笔与气运起伏,自然纤绝不苟,能会此意,即为法家;不知此理,便是匠习。笔繁最忌气匆匆,气匆匆则眼界不舒而情意俗;笔简必求气壮,气壮则神力雄厚而风格高。
写画不可专慕秀致,亦不可专学苍老。秀致之笔易于弱,弱则无气骨,有类乎世上阿谀;苍老之笔每多秃,秃则少文雅,有彷佛人间鄙野。故秀致中须有气骨,苍老中必寓文雅,两者不偏,方为善学。
用笔之道各有家法,须细为分别,方能用之不悖也。一笔中有头重尾轻者,有头轻尾重者,有两头轻而中间重者,有两头重而中间轻者。其轻处则为行,重处则为驻。应驻应行,体而用之,自能纯一不杂。
山水笔法其变体不一,而约言之止有二:曰勾勒、曰皴擦。勾勒用笔腕力提起,从正锋笔嘴跳力。笔笔见骨,其性主刚,故笔多折断,归北派。皴擦用笔腕力沉坠,用惹侧笔身拖力。笔笔有筋,其性主柔,故笔多长韧,归南派。论骨其力大,论筋其气长,十六家之中,有筋有骨;而十六家于每一家中,亦有筋有骨也。
如披麻、云头多主筋,马牙、乳柴多主骨,而披麻、云头亦有主骨者,马牙、乱柴亦有主筋者,余可类推,皆不能固执一定,总由用笔刚柔,随意生变,欲筋则筋,爱骨则骨耳。
论墨
山水用墨层次不能执一,须看某家法与用意深浅厚薄,随类而施。盖有先浅后浓,又加焦擦以取停当妥善者;有先浓后淡,再晕水墨以取湿润者;有浓淡写成,略加醒擦以取明净者;有一气分浓淡墨写成,不复擦染以取简古者;有由淡加浓,或焦或湿,连皴数层而取深厚者;有重叠焦擦,以取秋苍者;有纯用淡墨,而取雅逸者。古人云:能于墨中想法,于法亦思过半矣。
白苎桑翁谓作画尚湿笔,晚世用渴笔,几成骷髅。似此难免不免偏论,盖古人云: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又何莫造孽耶!
未可执一端之论,故薄今人何也。彼尚湿笔者,视渴笔成骷髅;其爱焦笔者,岂不议润笔为臃肿耶!
好咸恶辛,喜甘嫌辣,终日诤诤,究谁定论。不知物之甘苦,各有千秋,画之温按温应为湿。干,各自为法。善学者取长舍短,效法补偏,各臻其妙,方脱手眼。毋执一篇之论,而局守序言也。
凡加墨最忌板,不加墨最忌薄,二者能去其病,则进乎道矣。
山水墨法,淡则浓托,浓则淡消,乃得生气。不然,竟作去世灰,不可救药。
作山石如法皴完,再加焦墨醒笔,复用水墨渍染,向山石阴处落笔,逼凸托阳,或半边染墨,或顶黑脚白,或高下俱黑,而托中间,随眼活取之,不拘锁碎皴纹,俱从轮廓大意,染出待干,则宜赭宜绿,逐一设起。趁色尚湿时,又向阴处再渗水墨,层层接贴,此法极润泽明朗,又不失落笔意也。此予闲试墨法,悟而得之,因并记之。
用墨之法有误笔成趣,法变意外者,如初欲作湿润,而落笔反焦,即当用焦写成;欲作干焦,而落笔湿,宜即用湿写去,不可有一毫勉强拘滞。故写各礼各皴亦然,此乃临时变法也。
论景
凡布景起处宜平淡,至中幅乃开局势,末幅则接气悠扬,淡收余韵,如此自有天然位置,而无浅薄逼塞之患矣。故予常谓作画布景,犹作文立局,开讲从浅淡起,挈股虚提,中段乃大发议论,末笔不过足其题后之意耳,不必敷衍多辞也。以是画要通文,有书卷气,方不入匠派,即此之谓也。
布景欲深,不在乎委曲茂密、层层多叠也,其要在于由前面望到后面,从高处想落低处。能会其意,则山虽一阜,其间环抱无穷,树虽一林,此中掩映不尽,令人玩赏,游目骋怀,必如是方得深景真意。
作山石野景,其树石宜大气磅礴,其屋宇只是茅檐竹壁,或临江渚,或倚长松,其间不过一二隐士来往,绝无车马之迹。或岩边柳下,独钓渔矶;或桥畔虚亭,数声啼鸟,令不雅观者有世外之想,庶不失落为山林风味。
作富贵台阁景,则写琼楼玉宇,红树翠岩,时有衣冠车马,宫女奴隶;其间或净几明窗,回廓雕榭;即道路桥梁,亦多巧砌,豆棚莲沼,亦见工致。
景欲疏旷,树宜高,山宜平,三两长松,必须情趣交搭,远山几笔,不可散漫分开。山与树相连,树与山相映,疏处不见其缺,旷处不觉其空,方得疏旷窍门。
景欲浓秘,则树阴层层,峰峦叠叠,人皆知之。然照此去写,每见逼塞成堆,殊无意见意义者,何也?盖意泥浓密,未明虚实相生之故。不知浓处消必以淡,密处必间以疏,如写一浓点树,则写双钩夹叶间之,然后再用点叶;如写一浓墨石,则写一淡赭山以间之,然后再叠黑石。或树外间水,山脚间云,所谓虚实实虚,虚实相生,相生不尽。如此作法,虽千山万树,全幅写满,岂有见其逼塞者耶!
雨景多用米点,亦不拘泥。如写别皴,无不可以写雨者,但笔须湿润,墨须浑化,而皴法不可太分明,要隐现即离之间,以意为之,决不宜工细显著也。盖山石树林,既有雨水淋漓,雨云遮蔽,岂尚见山纹树叶,纤细玲珑耶!
雪景山石,皴法宜简不宜繁。然有大雪、微雪、欲雪、晴雪之分,大雪则山石上俱作雪堆,一片空缺,应无纹理可见,但于山石之外,以水墨入胶,随山形石势渍染成雪,而山脚石底雪不到处,不妨见些皴纹,树身上边留白,下边少皴,枯枝上亦渍白挂雪,凡亭屋瓦面,桥梁舟篷,皆有雪意,关津道路,当无行人矣。若写微雪,则山石中疏皴淡描,于轮廓外渍黑逼白而已。欲雪则天云惨淡,晴雪则白气仍存。至用粉为雪,加粉点苔,亦是一法,宜用于绢绫、金笺之中,于生纸不甚合适也。
月景阴处染黑,阳处留光,山石外轮以墨蓝洗出月色,如写雪法。但渍雪纯用水墨,以见雪天黯淡,而衬月则于水墨中少加蓝靛,以见月来日诰日朗,不失落彼苍也。树法皴法,咸宜湿润,皓皓明月,必有湛湛露滋之意。其点景,或弹琴弄笛、饮酒赋诗,庶不负此月夜佳趣。尝见人写春夜宴桃李园图,于树林中灯笼高挂,大失落题主。作者意为秉烛夜游句发挥,反轻写飞羽觞而醉月,不思太白之意重在醉月,而秉烛不过引古人以起兴耳,非此时之事也。既有月色,何用灯光。所谓多此一举矣!
然于笔砚杯盘之处,近点桌灯一二,未尝不可。高悬桃李树上,与月争光,则断乎不宜!
故曰:学画贵书卷,作画要达理。
风景于树叶偏斜以写风势,人皆知之。然不特树有风也,凡石上点台、水边点草、舟车往来、旌帆顺逆,人物中衣裾帽带,亭楼上屏帐窗帘,俱不离有风飞舞摇之意,方为作手。
夜景与月景大相悬绝,人多不辨,夫独云夜字,则无月可知矣。或问曰:夜既无月,则黑如漆,一物无所见,又从何着笔而成画耶?予答曰:无月光照耀,虽山石凹凸,树木交加,不能分别玲珑,而把稳作景之间,亦有树石影子。故或茅檐旅店剪烛谈心,小阁芸窗青灯照读,火光透映,只见旁边近处,仿佛有是景象而已。余外远影,亦不可见。全幅用水墨,或浓或淡,渲染渺茫,暗黑连天,斯得夜中真景矣。
论意
作画须先立意,若先不能立意,而遽然下笔,则胸无主宰,手心相错,断无足取。夫意者,笔之意也。先立其意而后落笔,所谓意在笔先也。然笔意亦无他焉,在品质取韵而已。品质取韵,则有曰简古,曰奇幻、曰韶秀、曰苍老、曰淋漓、曰雄厚、曰清逸、曰味外味,各类不一,皆所谓先立其意,而后落笔。而墨之浓淡焦润,则随意相配,故图成而法高,自超乎匠习之外矣。意欲简古,笔须少而秃拙,笔笔矫健,笔笔玲珑,不用多皴擦,用墨多浓,复染以水墨,设色不宜艳,墨绿墨赭,乃得古意。
意欲奇幻,则笔率形颠,最忌平匀。支配则从意外立局,疏密纵横,不以规矩准绳较尺寸。若非人间平凡可到之处,庶可拟作奇幻!
意欲韶秀。笔长尖细,用力筋韧,用墨光洁,望之袅娜如迎风杨柳,丰姿如出水芙蓉,斯为得之。
意欲苍老,笔重而劲,笔笔从腕力中折出,故曰有生辣气。墨主焦,景宜大,虽一二分合,如天马行空,任情收止。
意欲淋漓,笔须豁达流利,或重或轻,一气连接,毫无凝滞,墨当浓淡湿化,景宜新雨初晴,所谓元气淋漓障犹湿是也。
意欲雄厚,笔圆气足,层叠皴起,再三加擦,墨宜浓焦,复用水墨衬染。景不须多,最忌噜苏,绝壁乔松,一亭一瀑为高。
意欲清逸,笔简而轻,轻中有力,交搭处明白简洁。景虽少,夸夸其言。墨以淡为主,不可浓密加多。
作甚味外味?笔若无法而有法,形似有形而无形,于僻僻涩涩中,藏活活泼泼地,固脱习派,且无自持,只以融会,难以言传,正谓此也。或谓:画无法耶,画有法耶?予曰:不可有法也,不可无法也,只可无有一定之法。
写石欲超脱画派,要游览真石,胸有真谱,乃有真画。兴到时以奇别之笔,弗计是皴是廓,横推侧出,以肖天生纹理,若非人事所能成者,乃臻奇妙。故用笔之道,须神而明之。
固泥成法谓之板,硁守规习谓之俗。然俗即板,板即俗也。古人云:宁作不通,勿作庸庸。板俗之病,甚于狂诞。
或云:夷画较胜于儒画者,盖未知笔墨之奥耳。写画岂无笔墨哉,然夷画则笔不成笔,墨不见墨,徒取物之形影,像生而已;儒画讲求笔法墨法,或因物写形,而内藏力气,分别体格,如作雄厚者,尺幅而有泰山河岳之势;作澹逸者,片纸而有秋水长天之思。又如马远作关圣帝像,只眉间三五,笔,传其凛烈之气,赫奕千古。论及此,夷画何尝梦见耶。
论皴
古人写山水,皴分十六家:曰披麻、曰云头、曰芝麻、曰乱麻、曰折带、曰马牙、曰斧劈、曰雨点、曰弹涡、曰骷髅、曰矾头、日荷叶、曰牛毛、曰解索、曰鬼皮、曰乱柴。此十六家皴法,即十六样山石名目,并非杜撰。至每家皴法中,又有湿笔、焦墨,或繁或简,或皱或擦之分,不可固执成法,必定如是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披麻皴,如麻披散也。有大披麻、小披麻。大披麻笔大而长,写法连廓兼皴,浓淡墨一气浑成,淋漓活泼,无一笔滞气。此法始自董北苑,用笔稍纵,笔从左起,转过右收,起笔重著,行笔稍轻,悠扬辗转,收笔复重,笔笔圆运,无扁无方,石形多如象鼻。后清湘、八大隐士、徐文长喜为之。至巨然、米元章、吴仲圭、董玄宰、王石谷辈,俱是小披麻耳。小披麻笔小而短,写法先起轮廓,然后加皴。由淡至浓,层层皴出,阴阳向背,或焦或湿,随意加擦,较大披麻为稍易。北苑亦多作此,子弟皆宗之,晚世更喜学之。
云头皴,如云旋头髻也。用笔宜干,运腕宜圆,力贯笔尖,松秀长韧,笔笔有筋,细而有力,如鹤嘴画沙,团旋中又须背面分明。写云头皴每多开面而少转背,若不转背,则此山此石,与喷鼻香蜡饼无异矣。转背之法,如运线球,由后搭前,从左搭右。能会转背之意,方是云头正法。
芝麻皴,如芝麻小粒,聚点成皴也。其用意与雨点大同小异,先起轮廓,从轮廓中阴处,细细点出阴阳向背,正是天地间沙泥结成。大石光中有粒,凹中有凸之状,故用湿笔干笔俱宜,染淡墨青绿亦可。惟点须参差变动,最忌呆点,呆点则笔滞,笔滞则板,板则匠而不化矣。
乱麻皴,如小姑滚乱麻篮,麻乱成团也。麻丝即乱,何以成为画法耶?不知山石形像,无所不有,天生纹理,逼肖自然。盖乱麻石法,是石中裂纹,古人因其裂纹幼细如麻丝,其丝纹紊乱无头绪可寻,故名曰乱麻也。作此法不能维持原状,拘泥成法,必须多游名山,把稳生石,胸中先有会趣,庶免临池窒笔。
折带皴,如腰带折转也。用笔要侧,结形要方,层层连叠,左闪右按,用笔起伏,或重或轻,与大披麻同。但披麻石形尖耸,折带石形方平。即写崇山峻岭,其结顶处,亦方平折转,直落山脚,故迁移转变处多起圭棱,乃合斯法。倪云林最爱画之,此由北苑大披麻之变法也。
马牙皴,如拔马之牙,筋脚俱露也。马牙之皴,侧笔重按,横踢而成,落笔按驻,秃平处像牙头;行笔踢破,崩断处如牙脚。轮廓与皴交搭浑化,随廓随皴,方得其妙。若先廓后皴,必成去世板矣。此法马远、黄子久多作之。
斧劈皴,如铁斧劈木,劈出斧痕也。斧劈亦是侧笔,亦有大小之分。大斧劈类似马牙,侧按踢跳。头重尾轻,轮廓随皴交搭,一气呵成,此与马牙同。惟马牙笔短,一起即收;斧劈笔长,踢拖直消,此与马牙异耳。山脊无皴,以光顶之字接连气脉,俗人呼为烂头山者。即所谓斧劈山矣。罗浮有之,澳门、喷鼻香港,咸海、砂龙,更多此体。小斧劈皴用笔尖勾跳,可以先起轮廓,而后加皴,与小披麻仿佛赞许。李成、范宽、郭忠恕多画之,至小李将军则变小斧劈而为大斧劈也。大斧劈用笔身力,小斧劈用笔嘴力,当分别之。
雨点皴,全用点法,宜於雨景也。雨景之法始於米元章,故人皆称为米点。元章天性活泼,不入纤小,随意点缀,便成树林山石。或浓或淡,乍密乍疏,模糊处笔墨之迹交融,明净处点渲之形俱化,一幅淋漓,不必楼台殿阁,若有若无,自有雨中春树万人家道象也。米家发源北苑,写山亦有轮廓,写树亦有夹叶,盖变革苑之披麻,专取北苑之雨点,自成一家。今人不味米中奥旨,辄曰米画易学,特为可惜!
友仁画仍用雨点,但用笔稍细致,变大米而成小米。所谓雨点法,即米家父子法也,高房山善学之。
弹涡皴,如流涡滚也。长江水底,巨石阻流,撞激水势,从下滚上,水面回澜,旋转中如浪如泡,或高或低,其山石之形状似之,故名弹涡。石即今之咸海之滨所结水泡石是也。用笔微侧,旋转运动不泥,皴廓多作石眼,如水泡然。石眼之旁,随气接衬几笔。笔宜简,不宜繁,一气写成,然后用墨染出背面,兼衬贴余气,斯为得法。
骷髅皴,如头颅尸骨也。人头枯骨,画法何必以此扬名?不知山石形象多似佛头,若名佛头,只见光秃,未得眶齿玲珑、枯瘦嶙峋之状,古人盖有深间其间,李思训每画之。纯用钩勒,风雅谨严,丝毫不苟,细中有力,密处有疏,或像龙头,或如佛首,正侧旁边,眼鼻毕呈,短参差,形影俱在。宜作小幅,当用白描,更须以细树夹叶、曲槛回廊衬之。
矾头皴,如矾石之头也。矾头石多棱角,形多结方,每开一壁,周围逼凸,直廓横皴。每起工字细纹,高峙倒插,如叠矾堆。用笔中锋,用墨可焦可湿。焦可加擦,湿则加染,刘松年多作此。
荷叶皴,如摘荷覆叶,叶筋下垂也。用笔悠扬,长秀筋韧,山顶尖处,如叶茎蒂,筋由此起。自上而下,从重而轻,笔笔不合,四面散放;至山脚开处,如叶边唇,轻淡接气,以取微茫,此荷叶之法尽矣。当用蟹爪枯树配之,秋柳亦可。
牛毛皴,如牛之毛也。牛毛法与小披麻无异,惟小披麻用笔稍纵,牛毛必用正锋,小披麻粗幼兼用。牛毛有幼无粗,如发如毛,故写牛毛法墨不宜浓,笔不宜湿。笔湿墨浓则融成一片,毛不成毛矣。必要渴笔淡墨,细周详皴,再加焦墨疏疏醒之,浓里有淡,淡上见浓,毫丝显然,层次不混,乃是牛毛嫡派。
解索皴,如终结绳索也。解索与长披麻之法同类,然麻经结为绳索,复将绳索解拆散开,则麻虽非绳索比,而绳索攀卷之性犹存也。故长披麻不过悠悠扬扬而已,解索竟自挛挛曲曲矣。王叔明喜画之。
鬼皮皴,如鬼之皮也。鬼皮之纹皴,山石之纹亦皴,故立此名。用笔写法,略钩轮廓,皴要颤笔,笔笔叠连留眼。每皴一笔,如两点相连,连叠相交。最忌相撞,相撞则叠乱,乱则无眼,无眼则成板实光平,不见其为皴矣。鬼皮法颇与短披麻同,但披麻直皴,意在光滑;鬼皮颤皴,意在绉涩。此中用意,不可不阐发也。
乱柴皴,如柴枝乱叠也。乱柴法与乱麻、荷叶同为一类,但乱麻笔幼而软,有长丝团卷之意。乱柴笔壮而劲,有枯枝折断之意。荷叶笔气悠扬,如荷翻夜雨;乱柴笔势率直,如柴经秋霜。石之阴处,皴密而粗,彷佛重堆柴头。石之阳处,皴疏而细,俨然斜插柴枝。直笔中参以折笔,笔笔用力,即笔笔是骨。骨法用笔,此之谓也。乱柴石即今之寿山石,石多裂纹。有志画学者,当会此意,勿因名离实也,树宜秋林,用鹿角枝配之。
论树
古人有云:山有家法,树无家法。凡写山水必先写树,树成之后,诸家山石俱可任意配搭。此论似是而实非,盖作画贵意在笔先。意欲照某家皴山,必先仿某家皴树,方得如法一律。若专求山石,不讲究树,岂一幅中独取山石为画,而树非画耶!
推之屋宇、桥梁、人物、舟楫,皆分家法,与山石同,丝毫不苟,方是高明。勿因古人一言之错,自错生平也。
山水中树体不一,如松杉竹柏、梅柳梧槐之外,各体杂树均无定名,但以点法分类,如尖头点、平头点、菊花点、介字点、个字点、胡椒点、攒聚点、夹叶双勾,如三角、圆圈、垂尖、俱用笔像形,因以为名,非树果有此名也。若泥其点画,而求树之名,则凿矣!
或问树法与山法相合营,理固然矣,但山皴多而树皴少,恐分之甚难,不知树之配山,不徒以皴合,贵用笔同。如荷叶皴山,而写蟹爪树;胡椒点树,而配芝麻山;乱柴石而衬鹿角枝,凡此犹以貌取而已,总要在树秀则山秀,树古则山古。凡焦苍淋漓,笔长笔秃,与夫筋韧骨劲,用如是之笔写树,即用如是之笔写山,一幅毋出两格,斯言尽之矣。世有写树用笔固与山法不同,更有落笔之山与收笔之山各别,皆非就范者也。
树头要放,株头要敛。树头者,树根下头,故宜放开,俚语所谓撒脚也,必散脚方得盘根错节,担当枝叶,气势端庄。株头者,大枝小枝不合处,故宜收敛。若株头不敛,则枝软无力,加叶重赘,更有屈折之势,殊失落生气。至分前后旁边四枝之法,已详十二忌中,当参不雅观之。
凡作树多在山石之前,用墨宜浓,庶不与山混。若树后之山墨浓,山前之树墨淡,固有树为山压之病,即树山同墨,亦见平板,远近不分也。
一树中前后枝叶自分浓淡,一林中前后掩映亦各分浓淡以别之,其法在於交搭处不相撞,每树必须通气,奕家所谓留眼也。树叶固当玲珑,树头不宜逼塞,参差不紊,俯仰有情,或聚或散,或斜或正,不失落生气,斯道进矣。
晴树平正,雨树下垂,风树偏斜,雪树空缺。春则奇丽,夏则浓郁,秋则萧疏,冬则枯寂。密林多高标而直干,峭壁每枝垂而根露。作者多游真山,博览真树,方能会此真意。
写某皴山,要配某树,此以笔法言,非以树名论也。如写松,其松针落笔处尾尖,而结蒂心处大者,此宜用披麻、云头、牛毛等山。若落笔处尾重大,而聚蒂处反尖小,此宜配斧劈、马牙等石。别的竹、柳、梧、槐,与夫无名杂树,即此类推。其树皴纹繁简,看山石之皴笔疏密,此一定之法,千古不易也。众人每以此论为执拘,从而鄙笑之,专以乱点乱皴为高尚,不知此乃画意,非画法也。画意者,草率不羁,如长沮桀溺之流,只可自适其意,不可以为后世训。画法者,法律谨严,如孔子设教。君臣父子,五伦定分,一丝不紊也。
远山须用远树。远山无皴,有皴亦当从略;远树无枝,有枝亦宜从简。故写远树,但一干直上,多加横点。以成树影,不分枝叶,此宜于远,不宜于近也。众人每于近树下,每用远树法参补个中,作者以为大树脚之小树,不作远树看,不思大树之根株枝叶,纤毫可数,岂树脚之小树,独见直干,而枝柯杳然耶!
孟子所谓足以察秋毫,而不见与薪矣。奈习多不察,以讹传讹,是画学一大憾事。
写枯树最难鹿角枝,其难处在于多而不乱,乱中有条,千枝万枝,笔不相撞;其法在于枝交女字,密处留眼。《梅谱》云先把梅干分女字,《兰谱》所谓交凤眼,即不相撞之窍门耳。写山水、枯树亦然,学者宜寻思之。
论泉
石为山之骨,泉为山之血,无骨则柔不能立,无血则枯不得生。故古人画泉,甚为审顾,或高垂高叠数层,或云锁中断,或谷口分流,随山形石势,即难隐现之间,俱有深意。五日一水,非虚语也。
飞瀑千寻,必出于绝壁万丈。如土山夹涧,惟有弯曲平流,决无百尺高悬之理。凡画两峰,层层对峙,山顶虽高,而山脚交罅,积润成泉,亦是蜿蜒平出,岂可往后层山脚作高处,将前面山脚作低处,奔流直下耶。
写泉有两叠、三叠、四叠不一,而层层石体,叠叠要变,左旋右转,或短或长,连断参差,高下照料。
画水用笔,必须盛行,回润激浪,乃是活泉,而非去世水。
凡水中见石,是石从水底生,上露半浸半,故清流激湍之际,点写大小黑石,其石脚皴笔,要与水纹起伏相逼贴,方为水掩石。若石底下一笔,反收廓向上,则石已露脚,石浮水面矣。
论界尺
文人之画,笔墨形景之外,须明界尺者,乃画法界线尺度,非匠习所用间格方直之木间尺也。夫山石有山石之界尺,树木有树木之界尺,人物有人物之界尺。如山石在前,其山脚石脚应到某处,而在后之山石,其脚应在某处;如树在石之前,则树头应在石前,而石脚应在树后;如人坐石上,脚踏平坡,则人脚应与石脚齐;人坐亭宇门帘,可容出入,近人如此大,远人应如此小。推之楼阁船车,几筵器皿皆然,所谓界尺者此也。至云丈山尺树,寸马分人,亦界尺法。但非写一丈高山、一尺高树、一寸大马、一分大人也,盖山高盈丈,树宜数尺,不宜盈丈;马大成寸,人可几分,不可成寸云尔。故读古人书,要揣情度理,勿以词害意,方善取法。此文人作画界尺,即前后远近大小之法度也。
论设色
山水用色,变法不一,要知山石阴阳、天时明晦,参不雅观笔法墨法如何,应赭应绿,应水墨,应白描,随时眼力灵变,乃为生色。执板不易,便是去世色矣。如春景则阳处淡赭,阴处草绿;夏景则纯绿纯墨咸宜,或绿中入墨,亦见翠润;秋天景色赭中入墨设山面,绿中入赭设山背;冬景则以赭墨托阴阳,留出白光,以胶墨逼白为雪。此四季平凡设色之法也。至随机应变,或因皴新别,或因景离奇,又不可以平凡之色设之。
赭色设面,草绿设背,山石常用之法,但个中以是然处,人多不解。其为何用赭、为何用绿。如春景阳处淡赭,像山面新草初生,而日光映照,仍见土色,土色即赭色也,故写春景用淡赭,必微加绿,以取土上有草之意。阴处用绿,则这天光不到,不见土色,纯见草色,草色即绿色也。如秋天景色阳处纯赭,赭中入墨,以见秋苍,阴处虽有疏草,亦经霜黄,故绿中入赭,草色将枯也。胸中必明此意,作画方有生趣。
大披麻皴与小披麻皴,多是面赭背绿,惟赭与绿交搭之处,每现两色,殊失落自然。必由深赭而至淡赭,由淡赭而至淡绿,由淡绿而至深绿,两色浑化,不见痕迹为妙。其法当用湿饱赭笔,先旭日中之阳处重笔按下,其笔将渴,即趁渴笔拖落阴处,留绿地步,然后以湿饱绿笔,从阴中之阴处重笔托上,至笔将渴,亦用渴笔接连赭色,将见前之渴赭,溷入后之渴绿,两色交融,绿中有赭,赭中有绿,且前后渴笔,合而为一,则不渴矣。若以饱笔用于交搭处,则两相逼撞,必不相入,焉能浑化!
此正是精微心法,一笔不苟,勿以设色为余事,竟不讲究。
尝不雅观黄子久真迹写马牙皴,横竖倒插,石壁嶙峋,先用墨水染出背面,后加润色,一石全赭,一石全绿,一石全墨,而蓝、绿、墨、赭之外,又有赭入绿、绿入墨、黑入赭、赭入蓝、蓝入墨、相互兼色,分别相间,通幅嶙峋中层次显然,或坚或插,片块不紊,甚觉苍古。
王叔明画云头皴,用赭墨笔,依墨笔加皴,勾出背面俟干,然后以赭黄连面兼背,一笔染过。其赭黄之笔,虽不分背面,而赭墨先有阴阳,便不见板,此法明净苍秀可爱。况墨皴与赭皴,笔笔玲珑,不为色掩,子岂目睹叔明用色用笔而知耶?但见叔明多是此体。予初时临摹屡不知法,至今年近五十,乃穷究深悟中,试而得之,故笔之于书,以待来学。
曹云西写牛毛皴,多用水墨白描,不加颜色。盖牛毛皴干尖细幼,笔笔松秀,若加重色渲染,则掩其笔意,不如不设色为高也。有时或用赭墨尖笔,如山皴纹,层层加皴,不复渲染,作秋苍景;或用墨绿加皴,作春晴景。如此皴法,玲珑不为色掩,亦觉精雅,所谓法从心生,学毋执泥。若依常赭绿之法染之,则皴之松秀,变成板实矣。
文衡山画小披麻,夹小斧劈皴,多用赭墨染山背,用草绿染山顶,上绿下赭,随山石分间处顺笔染之,又不是板执。背面逐层分间,亦是一体。
凡画大青绿,用于生纸最难。每见旧画,其青绿化如油痕,殊失落画意,皆因石青、石绿粗则艳,幼则淡,人多喜其艳而忘其粗。况阳处石绿,阴处草绿,其草绿原是靛入藤黄相和成色。藤黄味酸,石绿质铜,铜见酸则腻,石相则易脱,久而绿脱,徒留腻痕。故生纸作大青绿,必须研极细幼,方无此弊。
论点苔
山水画成设色后,则点苔之法最要讲究。古人有云:点苔原为盖掩皴法之漫乱,既无漫乱,又何须挖肉作疮,此以点苔为不宜矣。又有云:山石点苔,如美女插花。女虽美,而无花衬艳,终为失落色,此以点苔为必须矣。两说皆是,亦皆不是,此各执一偏之见,不可以概论成法也。夫画山水,遵法固严,变法须活,要胸罗万象,浑函天地造化之机。故或简或繁,或浓或淡,得心应手,随法活气。时作笔简墨淡,山石明净,布景疏旷,虽欲多皴一笔,尚且不可,而况点苔乎。如美女之淡妆素服,自见幽娴,岂可以无花失落色而论之哉!
时作笔繁墨厚,布景幽深,山石重叠,必于论廓分间处,层层加点苔缀,庶不混乱。而山脊接连处,亦须点出气脉,一起一伏,势若游龙,虽千点万点,不嫌为多,岂可以盖掩皴法漫乱而论之哉!
苔固有宜点,有不宜点者。还有应点在未著色之先。有应点在先;若著色后,则纸为色水胶结,墨不能入,而前之皴与后之点,格不相食矣。如写子久马牙法,刚劲老苍,著色后乃加浓墨点苔,以取醒凸。若点于未著色之先,则墨渗纸背,反见平匀,殊不克不及干。其馀斧劈、乱柴、荷叶,凡苍劲要醒凸者,点苔宜著色之后。如雨点、芝麻、鬼皮、牛毛、折带、云头、解索,凡秀润要浑化者,点苔宜未著色之先。然此特为写生纸而言,至写矾纸绢,又不在此论。点苔之法,其意或作石上藓苔,或作坡间蔓草,或作树中薜萝,或作山顶小树。概其名曰点苔,不必泥为何物。故其圆点横点、尖点秃点、焦点湿点、浓点淡点、攒聚点、跳踢点,皆从山石中皴法生来,又从树叶中点法化出。是幅应点之苔,不能混用于别幅,夫如是,庶几臻乎道矣!
论远山
凡画皴山之外,应有远山。远山无皴,或墨或蓝或赭,用色洗染;或于凸凹处闪露半面,或于山脚外突出全体,其尖峰圆峦,照料皴山,形势远近,皆同一脉。若水上远山,要见山脚与水分,间一笔浓后化淡,以接顶气。而山顶一笔更浓亦化淡,落照料山脚,个中央必空淡,以留云影,方得灵动。
如一幅皴山,形势宜层叠,远山以收远景者,则用水墨、墨赭、墨蓝、层层分。然月朔层略浓,末了一层更淡,淡愈远愈杳,天地自然一定不易之理。予少年读《芥子园画传》云,远山愈远者,得云气愈深,故色愈重。此一重字,于心不能无憾。后游山不雅观海,历览远景,每把稳分别远山,为真画谱,所见皆是愈远愈杳,从未见山远而色反重也。盖近山无云遮蔽,故皴纹毕露,而见绿色,绿色乃山草本色也。云气色白,白色愈深,则山色愈浅,故近山深绿,由深绿至于浅绿,而远山则白云色深,绿为白掩,故绿变蓝,由深蓝而至浅蓝,由浅蓝而至不见蓝,岂不是愈远愈杳乎。重字改作淡字方妥。
凡画成加远山,众人每每忽略,以为末外功夫,多不经意,不知最关紧要。常见山水画成,通幅皆妥,惟远山失落宜,反为马脚,即不入赏,岂可慢不讲究哉!
夫皴山之后加远山,谁人不晓,莫失落位置。即远山之后,有皴山矣。如一幅布局,这一边写崇山峻岭,层叠而上,那一边空旷跌低,作平淡景,二高一低,甚为合法。其峻岭上加远山,无所不宜。但平远低处,要向这边峻岭上后层岭脚,应在低下某处,计度岭脚后一位,乃加远山,方合画中界尺也。若不明此界尺,则那边远山,实在这边岭脚之前;这边峻岭,皆在那边远山之后,树石虽佳,亦无可救药。众人犯此不少,学者尤宜穷究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