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清秋,白露微凉,在江南,已有三分秋色,而渔浦,秋意更浓几分。在萧山义桥,站在古渡口刻有“渔浦”二字的巨石前,秋日的气息,从江面上、桂花树上、庄稼地里,悄无声息地汇聚而来。江边望远,远山变得空旷,而天色显得明净,白云苍狗,世事悠悠。一千多年前的唐朝,那些浪漫豪迈的墨客便是从这里出发,开始了“壮游吴越”的人生之旅。他们饮酒品鲜,往来唱和,在渔浦的日落和霞光中吟咏,大笔一挥,写就浙东唐诗之路的开篇之作。
渔浦是三江交汇处,有江水的地方,必定风光秀美,何况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在此汇流。春天时,江面起了雾,如一幅水墨画,同行的墨客叶延滨形容道,江上的雾气,彷佛春天的秧苗一样,在水面上一棵一棵长出来的。
不止烟云,渔浦的落日,亦十分出名,“钱塘看潮涌,渔浦不雅观落日”,在钱塘枕水听潮,在渔浦醉不雅观落日,皆是人生快事。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一年四季,渔浦自有不同的风骚,江流、落日、湿地、野舟、旷野、烟云,落在眼里的,是景;写在纸上的,是诗;画在宣纸上的,是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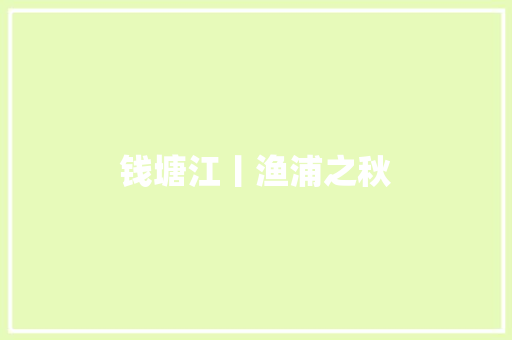
渔浦有沙洲,有湿地,舟过处,惊起水鸟无数。渔浦的江鱼既多又鲜,一叶扁舟,一把渔网,捞上来的,都是鲜活的美味。冬天雪后,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雪后的江鳗,肥美无比,若能钓上,来一盘梅干菜蒸鳗鱼,再加三杯两盏黄酒,那是人间至味。
渔浦的江鲜自古出名,渔浦之名,最早见于晋人顾夷《吴郡志》,“富春东三十里有渔浦”,因有渔市而得名。食客们从大老远凌驾来尝鲜,江鳗、步鱼、刀鱼、鲥鱼、昂刺鱼、江鲈、江虾、江蟹等,都是无双美味,这些江鲜长在咸淡冲的水里,经由富春江、浦阳江、钱塘江三江之水的滋养,岂有不肥美之理。
河鲜的鲜不同于咸鲜,也不同于海鲜的鲜,它的鲜,是清淡的,如白露时节的秋。刚捞上来的江鲜,肉质细腻,光是清蒸,就让人鲜掉眉毛。某年秋风起时,苏州人张翰由于思念故乡的鲈鱼和莼菜,辞官归田,为了唇齿之间的莼鲈之味,他任性了一把。而三江交汇之处的鱼,比张翰舌尖上的鲈鱼更加美味。渔浦是萧山的四大古镇之一,四大古镇中的西兴是浙东唐诗之路的源头,渔浦亦是,渔浦还是钱塘江诗路的交汇口,是幼年离家的贺知章的原乡。墨客们踏歌而来,一半是由于这里的风光,还有一半,或许是冲着江鲜来的。“西兴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欹”,是东坡居士的诗。苏东坡是官人,是墨客,任杭州知州时建筑了苏堤;他是生活家,独创过东坡肉;他的人生,一半是诗意,一半是烟火。不管得意与失落意,他都能找到人生的清欢。渔浦吸引他的,岂止是弄潮儿、朝霞与夕阳,江鲜是断然少不了的。陆游也为渔浦题过诗,“渔浦江山天下稀”,实在,“江山”改成“江鲜”,也甚是停当妥善。同行的墨客黄亚洲说,浙东唐诗之路的入口,是被鱼咬破的。这句话,真是有趣得紧。
千年渔浦,是古渡口,也是热闹的商埠,这里曾经舟船如梭,商贾如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这里也是墨客至浙东游赏的必经之地,从渔浦上船,可南上,可北下,可西进,可东出。墨客们既可从渔浦沿富春江到建德,直至“无梦到徽州”,又可以从渔浦至钱塘,再行山阴道,渡剡溪,走向我的故乡——李白心心念念的“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晒台去”的晒台山。哪怕漫无目标,任意漂流,无问西东,也清闲快活得很。可以舟行,好风送我上青云;可以陆行,一日看不尽江南花。八面来风,四处皆景。这一起,山似青罗带,水似眼波媚,数百里江山,风光无限好,墨客们的游兴与诗兴皆大发。于是,从南北朝的谢灵运、江淹、沈约,到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宋代的苏轼、陆游……都与渔浦结缘。风骚俊朗的孟浩然写道:“卧闻渔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候分,始知江湖阔。”这一年,孟浩然已过不惑,进士落榜,消磨了他人生的斗志,他索性快意江湖诗酒烹茶,自洛阳东游吴越,渔浦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驿站。这里烟波浩淼,鹭鸟翻飞,江面开阔。东风十里,吹动孟役夫心中的诗意,浇落了贰心中的块垒。他一起向东,过镜湖,入剡溪,直达晒台山的石梁飞瀑——“高高翠微里,遥见石梁横”。他在浙东唐诗之路的青山绿水间行吟,从萧山渔浦到晒台石梁,路有多长,诗就有多长。
而踏歌而来的唐代才子钱起,在九九重阳之时,题诗道:“渔浦浪花摇素壁,西陵树色入秋窗。”秋日的太阳照在江面上,波光映射在白壁上,而西陵无边的树色,同样映入秋窗。人生如歌,光影如梦。他的千古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在这里,怕是要一吟再吟。
千年之前,义桥渔浦是诗路;千年之后,这里依然是浙江的“诗词之乡”,诗词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花间的旧影,蒹葭的苍茫,江中的落日,舟来与舟往,人来与人往,山水无意,吟者有情。从唐朝起的那份诗意,在渔浦、在义桥,绵延千年,依然未有尽头。